1993年,97岁的薛岳被推上法庭受审。法官发问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后说道“我杀了十万日本人”,这句话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1993年的台北法庭里,97岁的薛岳被人搀扶着坐上被告席时,法袍领口的褶皱里还沾着室外的凉意,他枯瘦的手搭在扶手上,指节凸起像老树枝,浑浊的眼睛扫过全场,没在任何人脸上停留。 这场官司来得猝不及防,彼时这位老人早已淡出公众视野,日子过得紧巴巴,谁也没想到他会因交不起房租以被告身份出现在这里,原告方的陈述声在法庭里飘着,字句都绕着房产纠葛,书记员的打字声敲得人心烦。 法官终于开口发问,问题落在了纠纷的关键节点上,话音落下的瞬间,薛岳没立刻回应,他微微垂着眼,仿佛没听见那句问话。整个法庭的喧闹忽然就淡了,只剩下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声,时间一秒秒滑过,旁听席有人忍不住动了动身子,椅子腿蹭着地板发出轻响。 没人知道这几十秒里他想到了什么,或许是1939年那个秋天,新墙河两岸的稻田里藏着的杀机,当时他刚接手第九战区,日军十万兵力压境,岳阳失守后长沙已成孤城。他踩着泥泞勘察地形,把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串成三道防线,在幕阜山里布下伏兵,硬是想出了“天炉战法”这个死局。 又或许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寒夜,日军仗着装备优势猛扑长沙城,他在指挥部里盯着地图,几天几夜没合眼。最终国军以近三万伤亡的代价,换来了日军五万六千多人的死伤,连大队长级别的军官都死了十个。那场胜利让美国人立刻递来五亿美元贷款,连不平等条约都废了几条。 “我杀了十万日本人。”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像一块石头砸进静水,薛岳的声音带着老年人的沙哑,却字字清晰。刚刚还在低声议论的旁听席瞬间没了声响,打字机的声音也戛然而止。法官握着法槌的手顿在半空,一时忘了落下。 这话不是虚言,三次长沙会战打下来,日军被歼灭的兵力足有十一万之多,第一次会战里,他指挥二十四万大军跟日军死磕,硬生生把冈村宁次逼得全线撤退,蒋介石专门发来电报嘉奖,还给参战部队批了十五万赏金。就算是打得最惨烈的第二次会战,虽然国军损失近七万兵力,但也没让日军占到真正的便宜。 法庭里的人突然都沉默了,那些为房产纠纷而来的目光,此刻落在老人身上,多了些复杂的情绪。有人想起小时候听长辈讲过的战报,那些在收音机里振奋人心的消息,源头竟然就是眼前这个连站都站不稳的老人。 薛岳没再多说一个字,他重新垂下眼,手依旧搭在扶手上,只是指尖似乎比刚才稳了些,当年在战场上,他敢跟日军硬拼四十七天,敢在新墙河防线被突破后立刻组织反攻,可如今面对法庭上的争执,他只剩这句跨越半世纪的陈述。 后来有人说,那场官司最终没让这位老人太过难堪,毕竟没人能对着一个杀过十万日军的老兵太过强硬。想想也是,当年他在湘北战场拖着日军主力,为后方争取了多少喘息时间。那些在会战中牺牲的九万四千名国军将士,若泉下有知,恐怕也不愿看到老长官在晚年卷入这样的纷争。 庭审结束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薛岳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有人上前想扶他,他摆了摆手,自己慢慢站起身,走廊里的风掀起他的衣角,恍惚间竟让人想起当年他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的模样。 那句“我杀了十万日本人”,终究成了法庭上最沉重的回答,它没直接解决眼前的纠纷,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记忆里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在那些山河破碎的日子里,正是这样的人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才让后来的太平日子有了根基。 这或许就是全场沉默的真正原因,比起眼前的纠葛,那段历史太重,重到没人能轻易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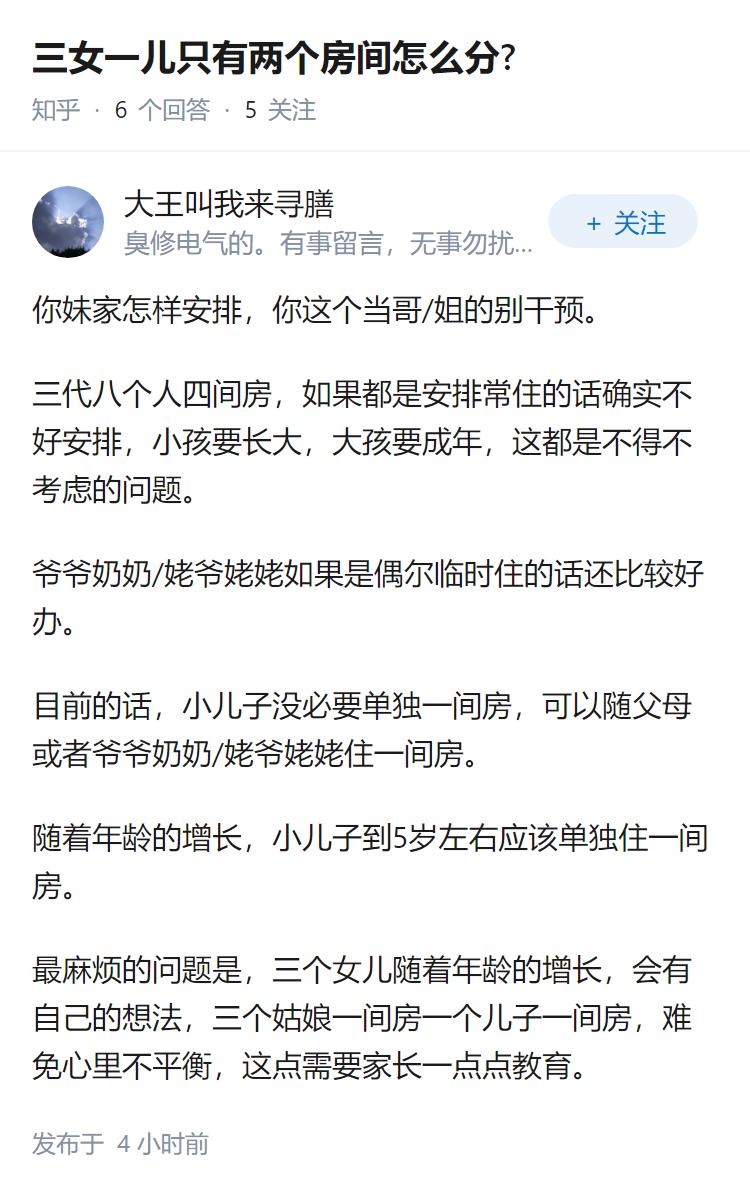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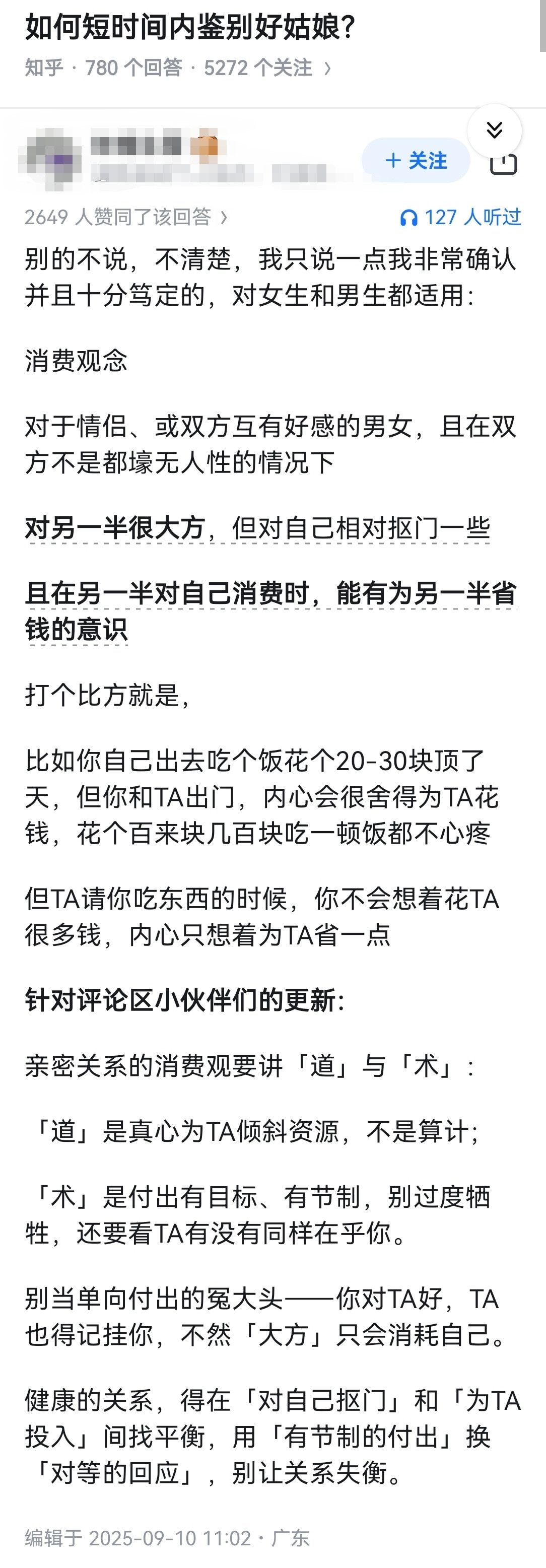
![不得不说,现实中就是这样子的![捂脸哭][捂脸哭][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077707832274358744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