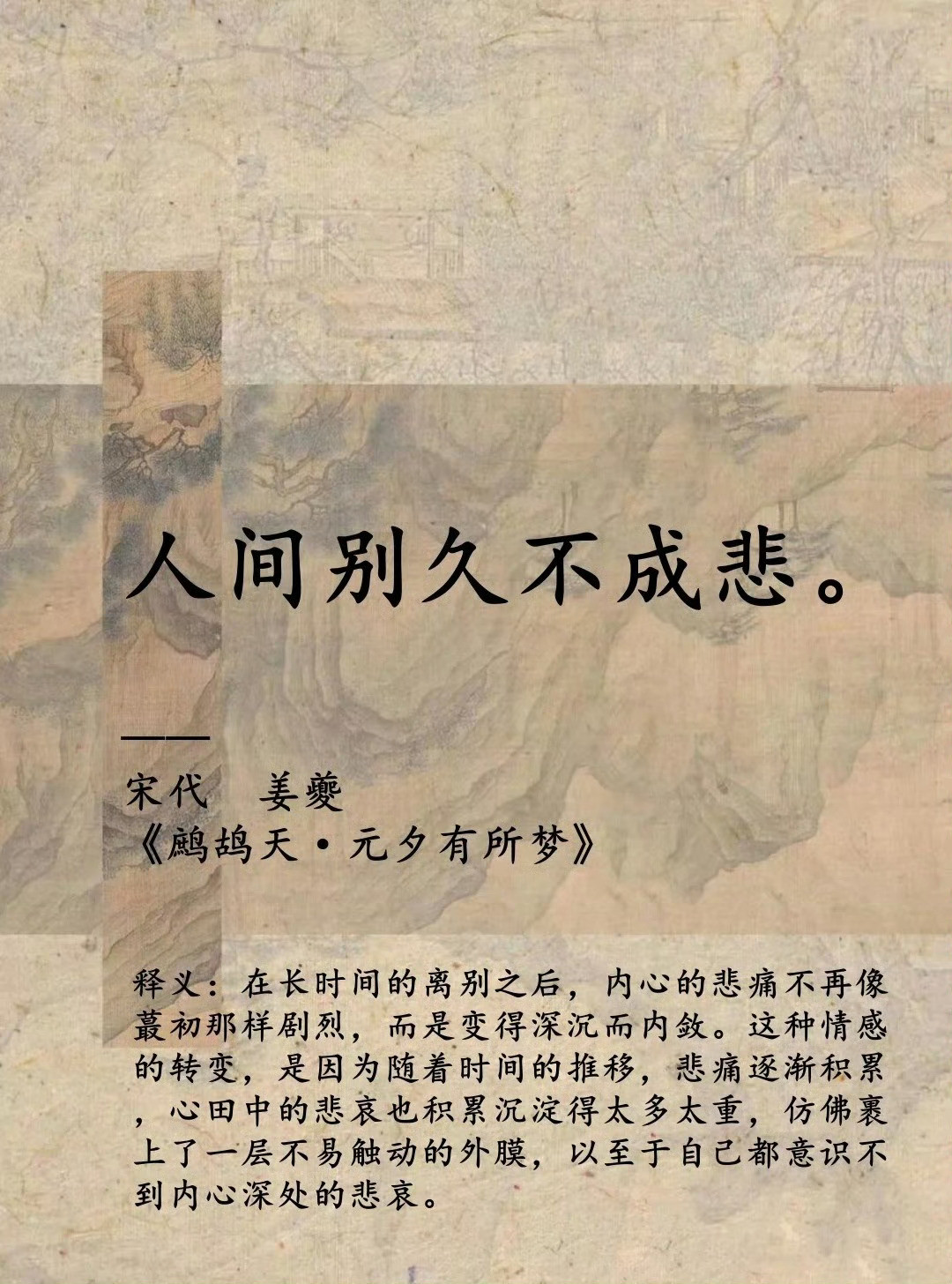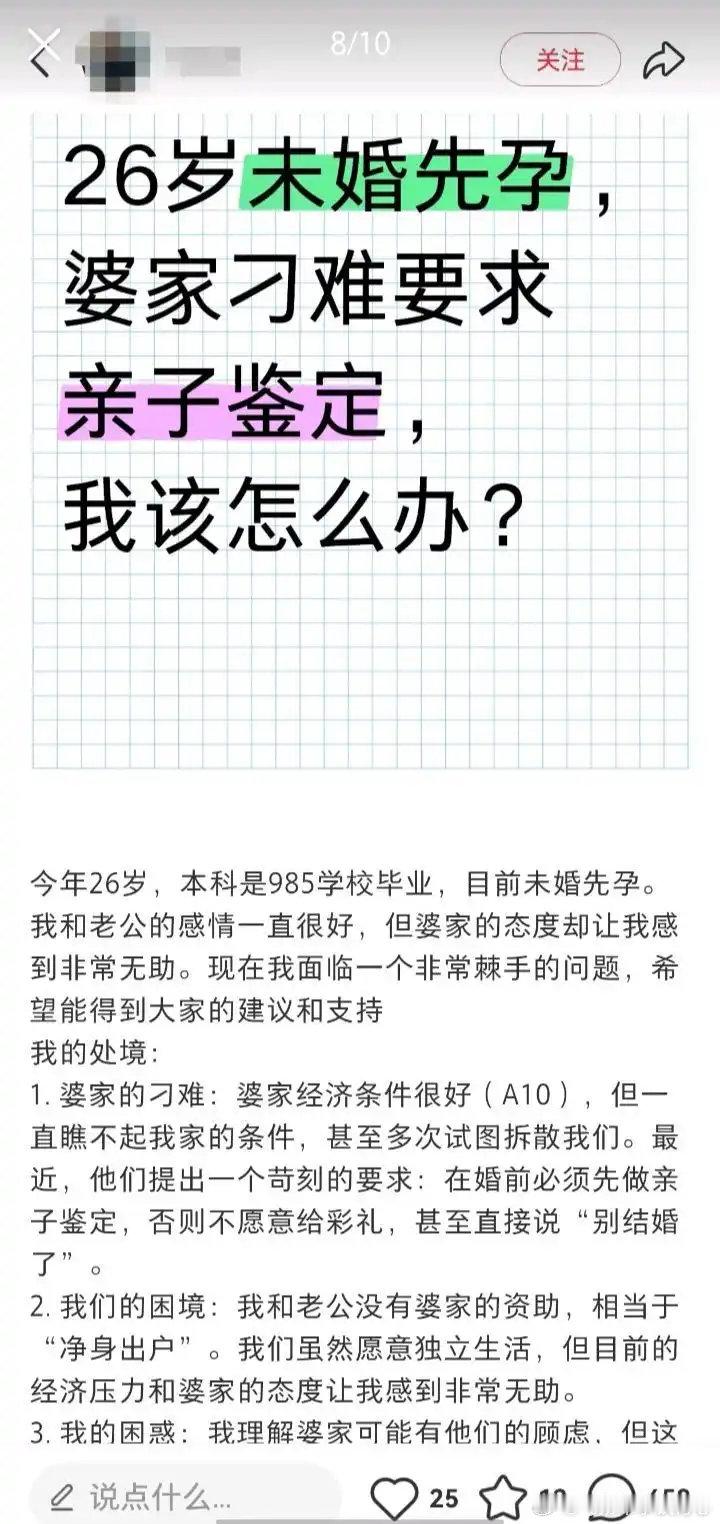我对此“不止喜欢”,我听见了石阶与脚步的千年回响。岳麓书院的门槛上,朱熹的辩难声还未散尽;爱晚亭的飞檐下,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词句仍在霜叶上闪光;抗战时期的炮火曾灼烧过这里的夜空,将军们布防时踩落的碎石,如今长满了青苔。历史在这里不是陈列馆的标本,而是活着的气息——每一阵秋风过处,都是不同时代的呼吸在交织缠绕。 最重的那里有来自“先父踏过的足迹”。巍峨山脉间,忽然裂开一条只属于我一人的小径。父亲的脚步或许曾停在哪级石阶上歇息,或许曾在某棵古树下回望。那些他走过的路,如今被你重新走成一条温暖的脐带,连接着血脉与土地。当伟人的足迹化为碑文,文人的墨迹刻入崖壁,唯有亲人平凡的足迹,会在每年落叶覆地时,从泥土深处传来真实的温度。 所以这不是观赏,而是认领。我在满山红透中认领了历史长河里属于你的那一瓢——那里既有大江大海的壮阔,也有屋檐下茶杯余温的私密。秋阳穿过枝叶,把所有人的故事斑斑点点洒在新铺的落叶上,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封大地写给岁月的信。而我是那个恰好读懂其中几个句子的人,在沙沙的脚步声里,把信小心地折进了心房最深处的位置。 这大概便是中国人最深沉的山水情结——我们从不单纯地看山看水,而是在山水间认领自己的来处,拼接时间的碎片,最后在某个秋日忽然明白:所有的路,都是同一条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