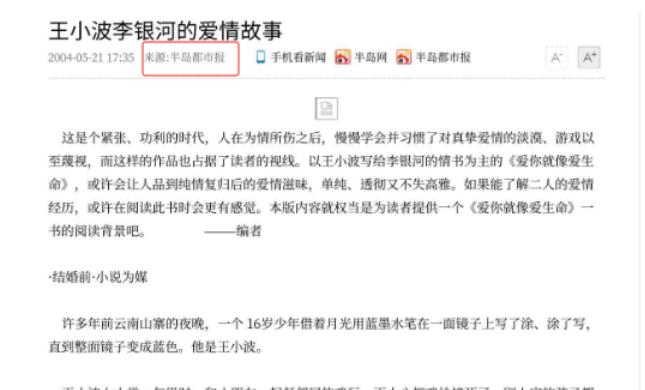“性学家”李银河和王小波交往后,有人问她:“你和王小波交往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李银河回答:“就是王小波长得太丑了。” 这句直白的吐槽,让1977年的北京编辑部炸开了锅。 那时李银河是《光明日报》的年轻编辑,而王小波还是个在街道工厂打磨零件的“黑脸大汉”,手里攥着一沓《绿毛水怪》的手稿。 谁也没想到,这场始于“颜值吐槽”的相遇,会成为后来人嘴里“灵魂伴侣”的代名词。 李银河第一次读《绿毛水怪》是在朋友桌上,油墨印的稿纸边缘卷着毛边。 开头写两个孩子在海边找水怪,她本来觉得“荒诞不经”,可读到“人活着总要有个主题”那句,突然抬头对朋友说:“这作者得见一面。” 后来她才知道,写这故事的王小波,白天在工厂镗床前站八个小时,晚上就着15瓦灯泡写小说,手指上还留着机油印。 见面那天王小波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1米84的个子杵在编辑部门口,脸晒得黝黑。 李银河后来笑他“丑得有特点”,他立马回嘴“你戴眼镜显老气”,俩人拌着嘴在胡同里走了三站地。 旁人都觉得他俩“不搭”,一个是大学生编辑,一个是工人,可李银河心里清楚,这是她见过最懂“自由”的人,就像《绿毛水怪》里的孩子,宁愿变成水怪,也不向规矩低头。 1980年1月,王小波揣着学生证去民政局,那时中国人民大学还不准在校生结婚。 他和李银河只请了双方父母,在胡同小饭馆摆了桌家常菜,连红囍字都没贴。 李银河把结婚证夹在《婚姻法》里,扉页写着“咱俩的事,不用旁人掺和”。 婚后住10平米的筒子楼,冬天没暖气,王小波就把搪瓷缸灌满热水裹进棉被,俩人缩在被窝里读诗,他读聂鲁达,她念费孝通,蒸汽从缸沿冒出来,在墙上熏出一小片白雾。 1984年李银河去美国读书,王小波辞了工作跟着去。 在匹兹堡的小公寓里,家具是跳蚤市场淘的旧沙发,冰箱里总只有牛奶和面包。 李银河上课,他就在家写《黄金时代》,写到“王二和陈清扬”的章节,会突然跑到图书馆找她,趴在社会学书堆里说:“这句性描写得改,你看是不是太直白?”李银河翻着他的手稿,铅笔在“破鞋”两个字旁边画圈:“不是直白,是把假正经撕了个口子。” 1997年春天,李银河从英国讲学回来,推开家门看见王小波趴在书桌上,手里还攥着笔,《黑铁时代》的手稿散了一地。 后来她在威海买了套能看见海的房子,书架第三层永远摆着那本磨破角的《绿毛水怪》,扉页有王小波用红笔写的“送给银河:咱们的水怪找到了”。 去年冬天她发微博,说整理旧物翻出当年的结婚证,照片上俩人笑得牙都露出来,“好像昨天刚在胡同里拌完嘴”。 如今那本《绿毛水怪》还躺在威海的书架上,夹着1980年的结婚证复印件。 李银河说过,她和王小波就像两个守着果酱罐的孩子,不用管外面的世界多吵,只顾着一勺一勺尝里面的甜。 或许爱情本来就该这样,不是看脸,不是看身份,是你读我的句子时,眼里闪的光,和我懂你没说出口的话时,手里攥紧的稿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