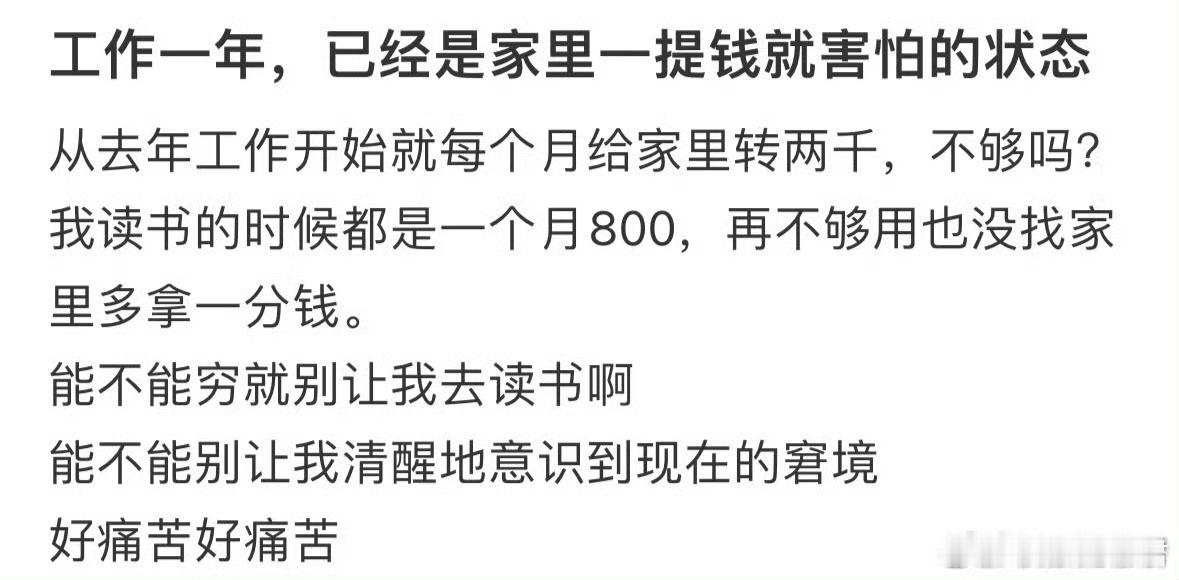昨晚和公公通视频,公公不好意思的对我说这个手头上的活最多只能干个半年了,别人就会嫌弃我年纪大了,如果实在干不了我到时候就不干了。屏幕里的他正坐在工地的板房里,安全帽挂在身后的铁架床上,帽檐的油漆掉了块,露出里面的铁色。 昨晚视频接通时,公公正坐在工地板房的铁架床边。身后的安全帽挂在床栏上,帽檐掉了块漆,露出星星点点的铁色,像他鬓角新添的白霜。我这边刚洗完碗,手机屏幕映着厨房暖黄的灯,他那边的日光灯管却嗡嗡响着,把影子拉得老长。 “爸,今天活儿累不累?”我举着手机往客厅走,想让信号好些。他却忽然避开镜头,手指在膝盖上摩挲着工装裤的褶皱——那是他年轻时在国营厂上班,我妈连夜给他缝的补丁,现在磨得发亮。“其实吧……”他清了清嗓子,“这工地上的活儿,我顶多再干半年。”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去年他腰椎间盘突出住院,医生反复叮嘱不能再干重活,可他偷偷瞒着我们,出院第三天就回了工地。屏幕里的他忽然抬头,眼里的红血丝混着灰尘,像揉皱的旧报纸:“人家包工头不说,我自己心里有数。你看这手。”他把右手凑到镜头前,指关节肿得像发面馒头,虎口处的老茧裂开细缝,“握不住钢筋了,打膨胀螺丝都使不上劲儿——到时候真干不动了,我就不干了。” 这话他说得轻描淡写,尾音却微微发颤。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总把我架在脖子上逛庙会,粗糙的手掌牢牢托着我的腿,那时我觉得这双手能举起整个世界。现在这双手蜷在屏幕角落,像只泄了气的气球。 “爸,您本来就该歇歇了。”我把手机架在茶几上,镜头里能看见他身后堆着的蛇皮袋,装着换洗衣物和降压药。“明年开春我带您去南方走走,听说桂林的水特别清——” “瞎花钱干啥。”他打断我,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我还攒着钱给小宝买学区房呢。”屏幕猛地晃了晃,他大概起身去够什么,背景里传来铁盆倒地的哐当声。我看着他佝偻着背扶着床沿站起来,忽然发现他的肩膀比去年更斜了,像被什么东西压得直不起来。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茶几上的橘子放了三天,表皮起了皱,像极了公公那双开裂的手。窗外的霓虹灯透过纱帘照进来,在墙上投下模糊的光斑,可我总觉得,没有工地板房那盏惨白的日光灯管亮——至少那灯光下,有个老人正用尽全力,想给家人撑出一片天。 我们总说等赚够了钱就好好孝敬父母,可他们的时间,哪里等得起我们的“以后”?或许他说“不干了”的时候,心里也藏着一丝期待吧——期待我们说一句“爸,回家吧,我们养您”。 tonight I should给公公发个微信,问问他工地的被子够不够厚。明天得去药店买几支护手霜,听说凡士林的最管用。对了,还要告诉小宝,爷爷快回家了,到时候要给爷爷捶捶背。 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模糊的影子。忽然想起公公说“握不住钢筋”时,那只悬在半空的手——原来无所不能的超人,也会有害怕的时候。
一场病撕开遮羞布:女儿和儿媳的区别,真的戳到了心窝里人生一次病就知道女儿与
【5评论】【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