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后,一个阔太太乘坐吉普车来到35军军部,对门口的守卫说:“我是陈修良,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一下。” 1949年4月的南京,长江边的硝烟还裹着水汽飘在街巷,穿军装的身影和挑着担子的小贩在马路上交错。哨兵握紧枪托,这个名字像颗石子投进平静的军部——没人知道,眼前这位旗袍领口别着珍珠胸针的女士,藏着整座城市的秘密。 何克希三步并作两步跨出门,握住她的手时,才发现这双“阔太太”的手,指节有层薄茧——那是三年来握着钢笔写情报、捏着针线缝密信磨出来的。三天前解放军渡江时,正是这双手拟的信,让电厂工人老周带着二十个工友守在锅炉边,愣是把国民党工兵的炸药包“拖”到了天亮。 时间拨回1946年春天,上海局的同志把南京地图摊在她面前,特务机关的红圈像毒瘤爬满街巷。“去重建组织。”领导说这话时,她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皮箱里还装着没拆封的马列著作。没人知道,这个曾在抗日根据地带着学生唱救亡歌的女同志,要变成“丈夫病故、从上海来投靠亲戚的张太太”。 住进城南那栋带天井的小楼后,她的日子像本泛黄的账册。每天去菜场买两根黄瓜,和小贩讨价还价时,袖口悄悄滑下的纸条藏着党员联络点;傍晚去夫子庙听戏,戏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唱到第三遍,邻座递来的折扇里夹着最新的军运情报。有人劝她少出门,她却笑:“越像寻常人,才越安全——就像菜篮里的葱,混在青菜里才不扎眼。” 转折点出现在1948年深冬。那天她刚把俞渤的起义计划封进空心竹竿,窗外就传来特务查房的皮鞋声。她把竹竿插进米缸,转身端出刚熬好的粥:“长官辛苦了,天冷喝碗热的暖暖身子。”特务掀开米缸盖时,她指甲掐进掌心——那竹竿就立在米堆里,像根普通的晾衣杆。三天后,B-24轰炸机的轰鸣震碎南京上空,俞渤投下的炸弹落在保密局附近,随即掉头飞向解放区。 1949年春节刚过,她在秘密会议上把油印的《护城公约》分下去。“敌人要炸水厂,我们就组织工人三班倒;要烧火车站,学生们就去‘义务劳动’盯着。”纱厂女工小李记得,陈修良教她们把标语写在布上,藏进棉袄夹层,“她说,南京是大家的家,咱们不拿枪,也要让它完完整整地交给解放军。” 有人说,隐蔽战线的人没打过一场硬仗,算不得英雄。可当解放军进城时,看到电厂烟囱照冒黑烟、火车站信号灯照常闪烁,才明白那些藏在账本、戏票、菜篮里的坚持,比枪炮更能守护一座城。她提供的《国民党军长江布防图》,让渡江战役的炮火避开了平民区;她策反的二十多个保长,在溃逃时偷偷收起了破坏工具。 南京军管会成立那天,她换上灰布干部服,站在挂牌的市政府门前。阳光照在她脸上,三年来第一次不用低头走路。何克希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陈修良同志推门进来时,我看见她旗袍领口的珍珠胸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枚小小的党徽——那才是她真正的样子。” 如今再看南京城,秦淮河的水还在流,总统府的墙根处长着青草。很少有人知道,七十四年前列在护厂队名单上的那些名字,和“张太太”这个假身份一样,都藏着一个共同的信仰:要让这片土地,再也没有秘密,只有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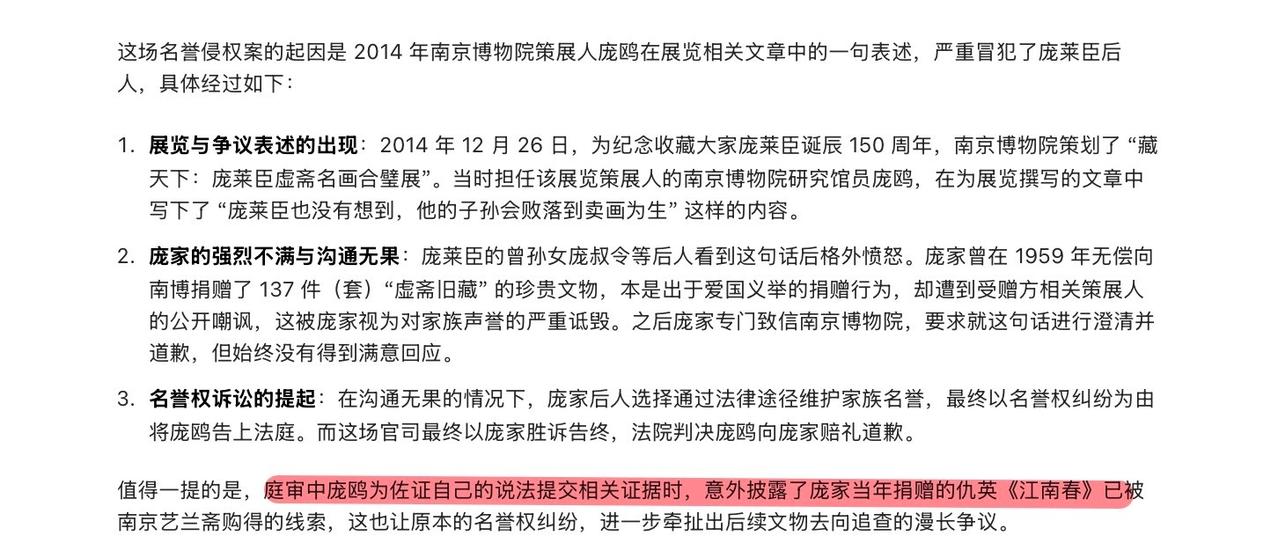







llg1996210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