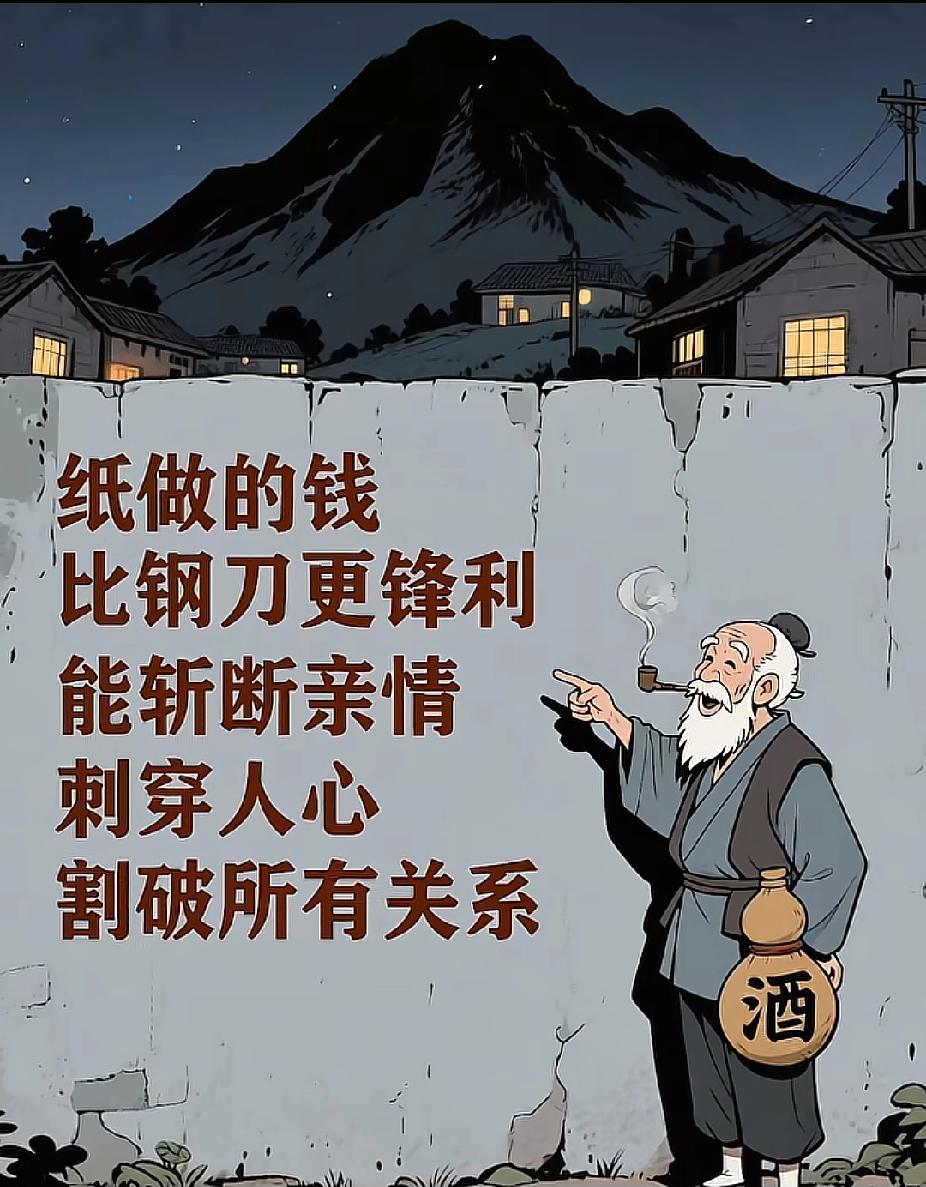1976年,北京知青抛下妻儿返城。 窑洞炕上的孩子还在哭,他塞给妻子一沓粮票,说“等我站稳脚就来接你们”,转身走进了县城的汽车站。 车扬起的尘土落在高丽彤的蓝布头巾上,她抱着孩子站在土坡上,看着那抹灰蓝色越来越小。 1971年陈建平下乡时,黄土高原的风把他的衬衫吹得贴在身上。 高书记拍着他的肩膀说“城里娃得接地气”,后来常叫他去家里吃饭。 高丽彤端来的小米粥总是热乎的,碗边还沾着几粒没擦净的米。 1972年冬天,两人在土窑洞里结了婚,红布剪的喜字贴在墙上,比城里的霓虹灯还亮。 转年孩子出生,陈建平用钢笔在红纸上写“陈念军”,说“念着部队,也念着这土窑”。 1976年政策松动的消息像长了翅膀,知青点的人都在传“能回城了”。 陈建平收到北京家里的信,说父亲托关系给他找了工厂的活儿。 他连夜收拾行李,粮票和布票塞进帆布包,离婚申请压在枕头下。 高丽彤第二天清晨发现时,墨水已经洇透了纸背,“日期”那栏空着,像没说完的话。 接下来的日子,高丽彤背着孩子在地里挣工分。 手上的茧子比锄头把还硬,冬天裂得渗血,就抹点猪油接着干。 孩子半夜发烧,她背着往公社卫生院跑,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有知青回城路过,说陈建平在西单摆地摊卖袜子,娶了个售货员,住的胡同窄得转不开身。 高丽彤听完没说话,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土坯墙的缝隙里漏进风,她用身体挡住了。 2006年春天,陈建平开着小轿车停在村口。 头发白了大半,西装袖口磨得起了毛。 他从后备箱拎出水果篮,递给高丽彤一张银行卡:“拆迁款200万,咱复婚吧,城里的房子写你名。”高丽彤正在给孙子缝衣服,线头在嘴里抿了抿,没抬头。 “当年你走的时候,念军抱着门框哭,你没回头。”她把缝好的衣服递给跑过来的孙子,“现在他每月给我寄生活费,棉袄比城里的羽绒服还暖。” 院子里的老槐树抽出了新枝,阳光透过叶缝落在高丽彤的白发上,像撒了一层碎银。 陈建平捏着银行卡的手出了汗,卡面的数字在阳光下晃眼。 他想起1973年孩子满月时,高丽彤笑着说“等娃长大了,教他写你的名字”。 如今那双手已经布满皱纹,却稳稳地牵着孙子的手,针脚在衣角歪歪扭扭,和当年给孩子缝的襁褓一样,扎实,也再不需要等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