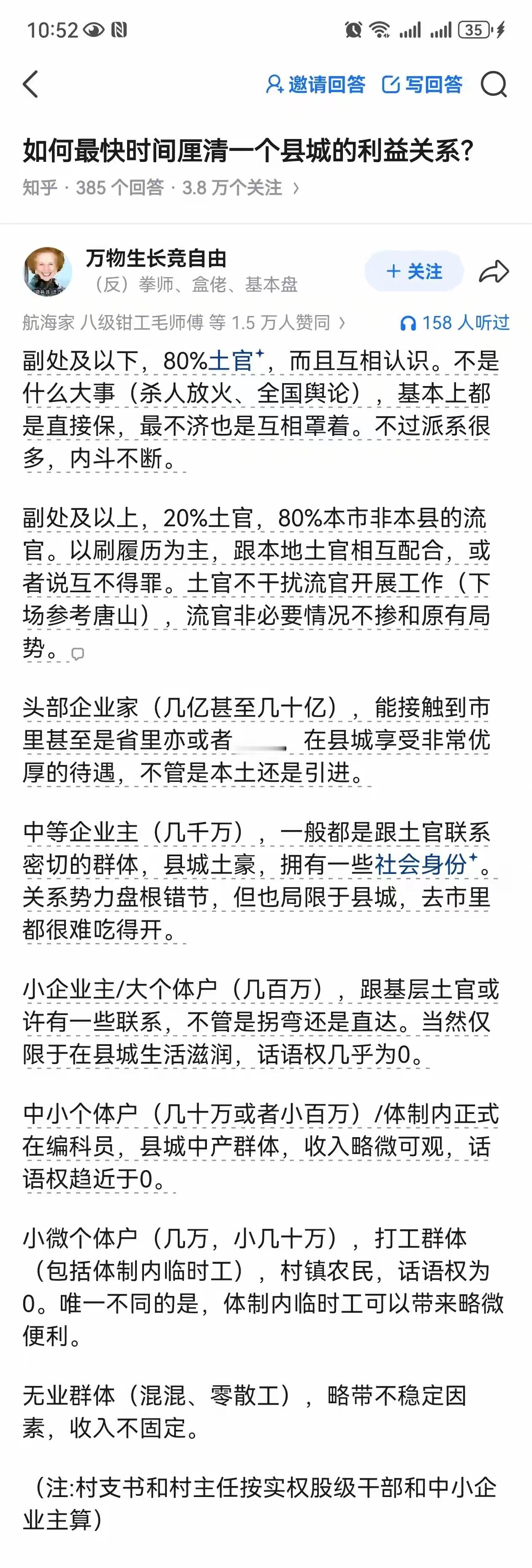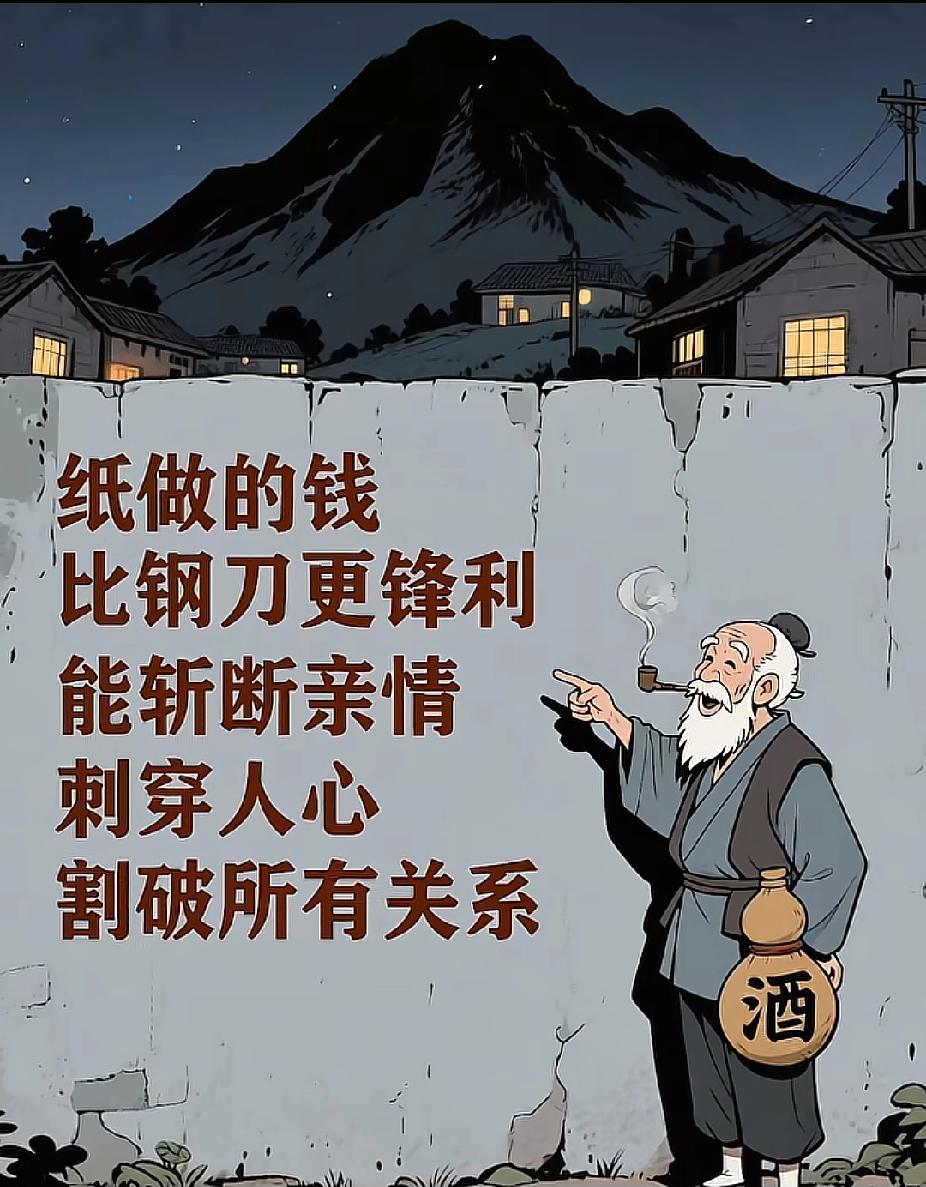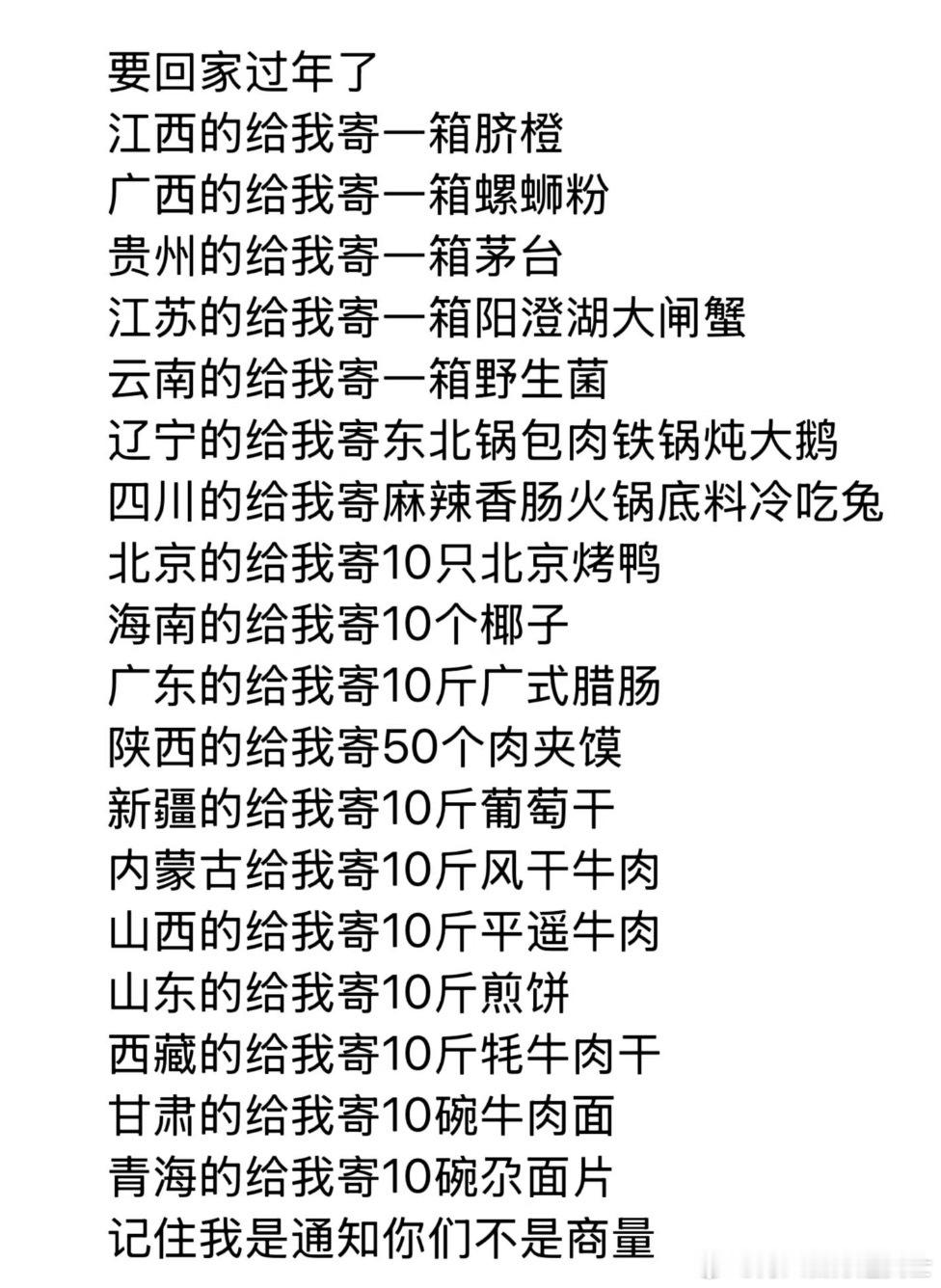一九七零年由于我家生活的六盘山区自然灾害频发,生产的粮食不够吃,父母亲便带着我们一家七口人边讨饭边走,走到了陇东一个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名叫细沟子。 1970年的风,刮过六盘山时总带着土腥味,地里的麦子刚抽穗就蔫了,穗子小得像没吃饱的雀儿——那是我记事起,家里粮缸第三次见了底。 父亲蹲在灶台边抽烟,烟袋锅明明灭灭,母亲把最后一把玉米面筛了又筛,筛出半碗碎碴子,七个弟妹挤在炕角,眼睛亮得像要把那碗碴子盯出花来。 “走吧,”父亲掐灭烟,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讨饭去,总能给娃们讨口活命的。” 我们一家七口,背着补丁摞补丁的包袱,沿着黄土坡走,脚底板磨出的血泡沾了土,硬得像鞋底的石子。 走了二十多天,日头偏西时,远远看见一片窑洞,窑洞顶上飘着几缕炊烟,那就是陇东的细沟子村——村口老槐树下,坐着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婆婆,手里捏着根拐棍,正眯着眼看我们。 母亲拉着我的手往前挪了两步,我能听见她后颈的汗珠子滴在地上的声音,“大娘,俺们是从六盘山来的,家里没粮了,想……想讨口吃的。” 老婆婆没说话,只是把拐棍往地上顿了顿,顿出一声闷响,然后转身往窑洞里走,我心一下子沉到了底——她会不会喊人赶我们走? 可没等我多想,她端着个粗瓷碗出来了,碗里是黄澄澄的玉米面馍,还冒着热气。 那天傍晚,村里的人陆陆续续来了,张婶端来半瓢洋芋,李叔扛着捆干柴,连隔壁窑洞的娃娃都攥着颗煮鸡蛋,塞到我最小的妹妹手里。 父亲红着眼圈给大家作揖,母亲抹着泪把馍掰成小块,分给每个娃——我原以为讨饭的日子,只有冷脸和闭门羹,可细沟子村的土窑洞,却把七月的日头都焐得暖烘烘的。 后来才知道,那年细沟子村的收成也不好,家家粮缸都紧巴,可他们说“都是受苦人,拉一把就过去了”——不是所有苦难都会让人把心关起来,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善良有时候比粮食更经得住饿。 六盘山的灾害让我们没了粮;没粮逼着我们踏上讨饭路;讨饭路上遇到的细沟子村人,用半块馍、一把柴、一句热乎话,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底气——那不是简单的施舍,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分出来一半的勇气,这种勇气,后来成了我这辈子揣在兜里的暖。 我们在细沟子村住了下来,父亲帮村里人犁地,母亲给谁家缝补衣裳,弟妹们跟着村里的娃上山挖野菜。 很多年后,我带着孩子回细沟子,老槐树下的老婆婆早就不在了,可那棵树还在,枝桠上挂着的红布条,都是后来人感恩的念想。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最珍贵的,我会说,是在最难的时候,有人愿意为你停一停脚步,问一句“饿不饿”。 如今再闻土腥味,不是讨饭路上的尘土,是细沟子村窑洞前,母亲烧火做饭时,柴火混着洋芋的香——那香里,藏着我们一家七口,从绝望里走出来的,一条活路。
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结局,已经悄悄来了。我的一位同事,今年38岁,未婚。她的父母
【2评论】【6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