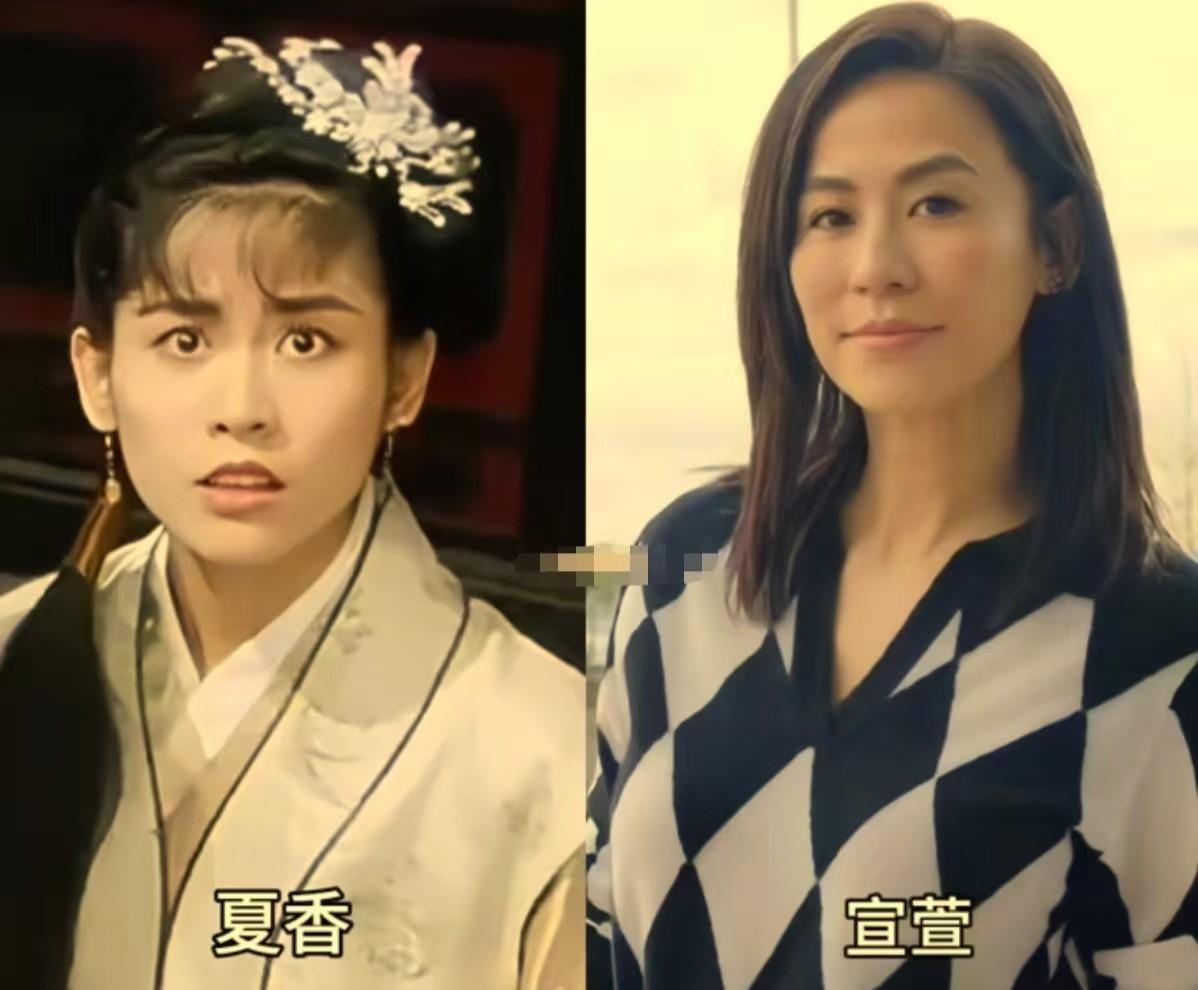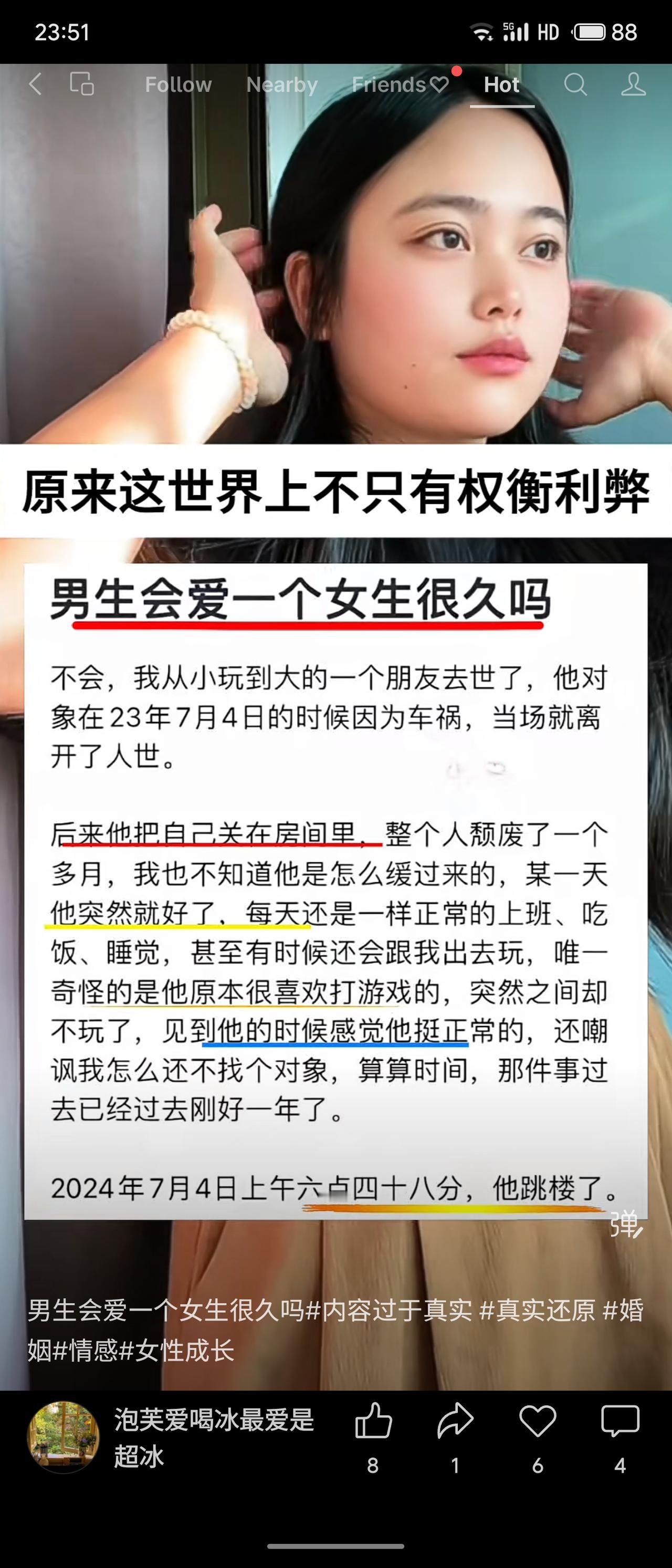三十年后,我们才在4K高清里,看清那只印在一个男人脊椎骨上的凤凰。 1993年,片场。 陈百祥脱掉上衣,趴下。 导演要求一只凤凰的剪影。 没有特效,他用赤裸的背,蘸满墨,在宣纸上一次次滚动。 那组镜头,最终在电影里只有2秒。 他滚了十几遍。 当时的灯滚烫。 墨是凉的。 宣纸粗糙的纤维,刮过皮肤。 他用的是第七节颈椎到第三节胸椎,那段最凸出的骨骼。 压出凤凰最核心的那片羽毛。 三十年后,4K修复版上线。 每一道骨节压痕,在荧幕上纤毫毕现。 观众终于看清,那羽毛的纹理,不是画的。 是一个人的骨头,一寸寸碾出来的。 今年,陈百祥拿了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周星驰在为《少林女足》全球海选。 一个时代在授勋,一个时代在寻找新的面孔。 我们总在谈论电影技术。 但真正击中人心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 是技术匮乏时,那种豁出去的、近乎笨拙的全身心投入。 那2秒的凤凰,是他用一整片背部的皮肤和骨骼,押上去的赌注。 如今,我们有8K,有虚拟制片。 一个镜头可以拆分给十个部门。 但那种“用肉身丈量艺术”的孤注一掷,似乎也和那个胶片时代一起,慢慢封存了。 所谓“笨”精神,本质是一种敬畏。 对观众的敬畏,对作品的敬畏。 如果今天再拍一只凤凰,你会选择用CG渲染72小时。 还是,把背交给一张粗糙的宣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