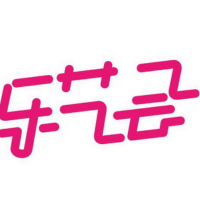怀 师 忆 友
无百川则无大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韩天衡先生通过文字记录了许多艺术前辈的逸事趣闻,让我们仰之弥高,回味无穷。在艺术世界里,他们用一生向着艺术的理想境界攀登,从不懈怠。韩天衡先生以其对细节的强大记忆,再现了文化荒漠时代和微光初露时刻,一个年轻而痴迷的艺术爱好者,和一群老艺术家交往的动人情境。这些情境,淡如水,浓如血。在那个时代,属于绝对边缘、毫无轰动效应的私人叙事。四五十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经过时间的发酵,具有了传奇的色彩。活在作者心中的谢稚柳、唐云、程十发、朱屺瞻、钱瘦铁、陆维钊、沙孟海、方介堪、李可染、启功、黄胄、郑竹友……都是照耀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熠熠巨星。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将持续推出韩天衡先生所著怀师忆友系列文章,本期推出《方介堪师的几件逸事》。
方介堪师的几件逸事文 | 韩天衡
方介堪先生已经仙逝八个年头,我曾先后写过几篇文章,这里我仅谈谈他的几件逸事。
介堪先生自幼对篆刻有着特具的禀赋,少时家贫寒,十三四岁就在温州街头鬻印以养家。其时他的印风是多取法于吴让之、徐三庚,也涉及赵次闲辈,路数颇杂却饶有气质。少儿捉刀卖篆,不免令人刮目相看。时学者张宗祥先生(后任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游瓯海,观其治印,有板有眼,视为可选之才,加以资助扶植,并辅以学业,从而使方介堪先生摆脱窘境,走上了一条艺学并进的康庄正途。

方介堪先生(左)与韩天衡先生(右)
二十岁后,介堪先生来上海,他的印艺得到了黄宾虹、赵叔孺、张大千诸家的佳评,由友人引荐入赵叔孺室为弟子。刘海粟诚聘其任上海美专教授,讲授篆刻之学,先生操一口瓯语,非沪人能消化,故上课必先发教材,教材皆自撰,论古道今,条分缕析,图文结合,言之有物。在当时纯属是具有创意结构的表达,有学生孔某,做有心人,对方先生散发的讲义勤加汇辑,又请益先生为其提供秦汉乃至明清印家之印蜕。先生视孔氏为好学,热心无私指授,直至孔氏以己名出版《篆刻入门》一书,先生方知被蒙被欺,然也不加追究。由此可见先生老实豁达之胸襟。
先生治印,此时已脱出清人及时人窠臼,直攀上古,醉心于汉人切玉法,故名玉篆楼,所治玉印足以置于古谱而乱真。先生对周秦小玺也悉心研求,他研求的方法是用心地摹写所有小玺文字,辨其差别,晓其规律,成竹于胸,演为新声。对古印他博览强记,万数以上的古印出自何家何谱,及其来龙去脉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这恐怕也是常人所不可及的。他的仿小玺印,精严浑穆,自成一格。记得他的启蒙老师谢光(磊明)先生在刻小玺印时也特意署款称“介堪在沪上卖篆,作小玺有此一格”。由此可见影响的一斑。先生在编纂《古玉印汇》一书时,对周秦两汉的花体篆字——鸟虫篆,发生了浓郁的兴趣,探幽索微,畦径别开,从此篆刻鸟虫印也就成了先生开拓性的强项。先生尝有诗曰:“戈头矛角殳书体,柳叶游丝鸟篆文。我欲探微通画理,恍如腕底起风云。”谢稚柳师告我,其时先生治鸟虫篆,尚不擅繁加纹饰,谢师以画人之识见,参与意见,遂使先生之鸟虫印,更具丰赡玄奥的美感,成为这一领域里承前启后的枢纽人物。先生治印用推刀,故线条的表达稳练、精确,用刀如笔,不事修饰,是其过人处。先生素来浸淫传统,胸中自有古印万钮,故先生治印,往往不起墨稿,视印面为纸楮,任意挥运,自在轻松而水准上乘。时先生印名大隆,求印者不绝,一天治印五十方是寻常事。诚然,过多的应酬,加之先生的推刀技法,难免有压抑豪气、抵消激情的作用。因此,他部分的印作,似有四平八稳的倾向。先生治印至晚岁均不借手于人,且勤勉如中壮。我曾估计,先生一生治印在三万钮以上。这个数字,或许不是同时代的任何印人所能企及的。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家近青田,所刻印多取青田石,古来印材多不取长,故乏品相,青田印材之拔长可观,这全是先生提倡所致。


现代·方介堪 平戎阁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藏
20世纪30年代,先生在勤于治石之际,即明智地勤于治学,他曾对许多彼时不能识别的古文字做了合理的解读。又曾与夫人王舜英手摹旧谱印章数万方。豪发不爽的手摹,决不同于今日的照相与复印的简捷轻松,是考验学力、眼力、毅力的艰辛工程。先生积十余年之功,成《玺印文综》十四卷。皇皇巨著耗费了先生半生的心力,欲谋出版,恰逢抗战,携稿避乱,又痛失第十四卷一册,直至先生下世,门人张如元、林剑丹和我等多方努力,补遗失之一册,增新见之文字,终究于1989年使此书出版问世,让先生的一大印学成果嘉惠印林、流布天下。
新中国成立初,作为大篆刻家的先生由沪渎老返温州,颇为政府重用,委以文管会主任、博物馆馆长重任。先生一心效劳新中国的文博事业,年迈六十犹跋涉荒野,有时一天步行六十里考察、征集文物,不以为苦。在如今温州博物馆的收藏中,足以看出先生三十余年如一日的付出的辛劳汗水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的生活同样是清苦的,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营养不良而得了肝肿大。那时,我在温州海军服役,常去古籍书店买书读书,一位年迈体弱的老职工就跟我谈起过,先生把朋友送他的黄鱼肚干硬是赠送给他这个普通人补充营养,说到感动处,老职工都眼含泪水,这泪水至今还晶亮晶亮地时常在我的心田里浮现出来。

现代•方介堪 小篆杜甫堂成诗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藏
1962年,先生患黄胆肝炎住院,我请假去探视,先生硬是不让我与他见面。他叫护士传话给我,说:“你是时刻要保卫海防的解放军战士,我得的是传染病,如果见了面传染给了你,怎么得了。”这事虽小,却让我感受到先生纯正的高尚德行。
比我们长整整一辈的师长们,他们的苦难和境遇,往往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所不能体会的。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坎坷,以使他们的艺术得不到应有的宣传,也使我们在今天不能科学地、平等地了解他们,而以“今是而昨非”轻率地否定他们,这种非历史、非客观的品评倾向,应有必要注意和纠正的。十年前,我在为先生编选的《方介堪印选》跋里,曾这样说过:“方介堪先生矢志于篆刻艺术的20世纪初叶,正是吴昌硕、黄牧甫两位巨擘以各自强劲的雄风左右和统帅印坛的时期。如果说,天上耀眼的巨星会使贴近于它的四周的星辰减色。那么彼时这两位巨星的升腾,也确实遮盖了一些人的光芒。少年的方介堪,许是天公作美,许是自身的早慧,他在学印伊始却没有去追随这两位印坛大师,而是避近求远、避同求异,迈步于秦玺汉印的广袤世界里,从而使他得以放射出自我的光亮,成为一位有其自身特色的重要的印学家、篆刻家。”至今,我认为当时对他的评价依旧是公正而切实的。

文章来源:韩天衡《砚边艺絮》,文汇出版社2024年版。(本文选段有删减)
- 版权声明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微信号: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发布的图文均为版权作品,仅供订阅用户阅读参考。其它网站、客户端、微信公号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并请勿对文章内容擅自修改。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