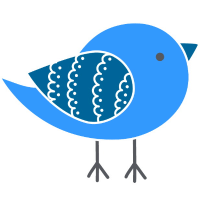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深圳微评
杨华标《病中吟》(五首)解读诗/杨华标 评/于爱成

今天没有一个好消息
永不停歇的战争
地震、海啸
干旱、洪水
医院匆匆忙忙为火葬场运送着一具具“燃料”
电视画面里
台上西装革履的乌鸦叫声
台下五颜六色的鹦鹉不停地迎和
这人云亦云的和奏
却让正辛勤觅食的麻雀听不见超级台风来临的声音
它们的危险无人关心
今天没有一个好消息
除了此时此刻时钟将过深夜二十四时
从大写到小。天体宇宙,各种各样各个物种各个层面的战争,永远在发生,没有止息。包括这地震、海啸、干旱、洪水等种种的自然灾害(人类认为的灾害,其实也仍是天体、宇宙、自然、地球运动的一部分),包括这人类的医院中运送到火葬场的一具具尸体,实则也不过是一具具燃料。彼时彼地、此时此地、亘古如此,天道自然,无非如此。
从远写到近。写到了地球、人间或形同畜生道的人世间或形同人间的畜生道。天天出现于电视上的、出镜的、冠冕堂皇的,是台上的乌鸦,他们着正装,西装革履,呕哑嘲哳说个不停;台下坐着的是鹦鹉群众,是乌鸦的听众、他们的仆役,打扮得花枝招展,五颜六色,点头哈腰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这鹦鹉学舌的合奏实在太过响亮,甚至掩盖住了超级台风来临时的声响,辛勤觅食的可怜的麻雀众生大难临头,而他们竟然毫无察觉,而且他们的生死,又有谁来关心?
从众生写到自己。今天没有一个好消息,除了此时此刻即将迈过今夜进入明天。今天过去了,今夜过去了,明天即将到来,这是唯一的好消息。时光的流逝不是正常的转换吗?在诗人笔下,也许他想说的是,好在时光还在流逝,明天还能来临,生命还在延续,这就是最坏之中的好消息了。
从而,这个作品,既是写自况,此时此刻的黯淡的心境,也是写众生,写社会人生,写宇宙大千,乃至法界虚空界,写终极意义上生命的悲剧。
从而,有态度,有立场,有愤怒,有悲悯,有忧伤,就是一首普遍意义上的诗作。

门诊部
菜市场是忙碌的
现在的医院是繁忙的
市场的熙熙攘攘是自发而开心的
你能轻易闻到人间烟火
医院的所有电梯、楼道都挤满了焦虑的人
这里人们只想活着,但没有时间思考生命的意义
他们用愁苦、揪心、害怕甚至愤怒
构筑了医院的一片繁荣景象
夜幕降临
医院走廊的灯光昏暗而悲伤
暂时的安静却会令人紧张到窒息
不知何时远处传来的嚎啕大哭
莫名的恐惧 挥之不去
全篇采取对比法,菜市场与医院,人间烟火与人间炼狱。菜市场与医院,都人山人海、人头涌动,都是一片忙碌、繁忙的景观。置身于菜市场与受困于医院,心情却是冰火两重天。在菜市场,你有你的轻松惬意,人们汇聚于此,熙熙攘攘,正是自发地形成与追求,这样的开心也是由衷的,寄寓了对生活的投入以及更好生活的热望;而在医院,作为病人的人们,真实的处境和心境却只有焦虑、愁苦、揪心、害怕甚至愤怒,他们的“愁苦、揪心、害怕甚至愤怒/构筑了医院的一片繁忙景象”——因何愁苦,因何揪心,因何害怕,因何愤怒?这种种恐惧与不甘、恋世与愤怒(对不幸降临己身的愤怒),构筑成为医院密集人群之外的另一个气场、宇宙、环境。
可以看出,除了采取对比法,诗人还采取了以物写人的间离法。聚焦点,诗人不忍心直接面向一个个具体的病人,而是宕开一笔,从环境写起,从容纳、包容、体贴着人的物(包括空间)写起。他写市场忙碌,医院繁忙,市场熙攘,电梯楼道爆满,他写种种的情绪盈满、挤满了市场和医院的空间。他有他的不忍,他的不愿,他的悯怜。
再看这第二节,“夜幕降临/医院走廊的灯光昏暗而悲伤/暂时的安静却会令人紧张到窒息”,同样是写物和空间,物和空间中的情绪和情感。入夜了,一切仿佛安静下来,看病的病人和家人少下来,住院的病人们进入各自的病房,此时只有医院走廊的灯光兀自亮着,“昏暗而悲伤”,她不忍更亮,昏暗才好遮掩她的悲伤;此时的“安静”也让置身其中者感到一种不真实、不踏实、没有安全感,似乎这样的安静太过奢侈,也过于虚幻;似乎这样的安静其实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危险,如同宵禁之夜的战场,无法让人紧绷的弦片刻放松。/不知何时远处传来的嚎啕大哭/莫名的恐惧 挥之不去”,这其实正是这如同战场的片刻安静可能的真相——生离死别于此夜间更尖锐裸露出其残酷的一面,在此夜间,也才一遍遍一次次地追问每一个在此的病人,这生与死的考验,生与死的直面,生与死的追问,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在这样的恐惧中,让人陷入更深的暗夜。
应该说这也是一首天成之诗。对于生命的喟叹,对于生与死的思考,对于生命真相的触摸与直视,他不激烈,甚至很冷静,只做旁观,但却通过这样白描的方式得以呈现。

手术室
护士天使般的温柔
在迷宫一样的手术室楼层内穿梭
就如牧师的临终关怀
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只模糊看见翕动的嘴唇和美丽安详的脸庞
躺在手术床上
头顶上的灯光像是UFO降临
随时准备将你掳去另一个空间
思想游离了身体
想极力睁开不受控制的眼睛
看看
麻木的身躯,如何
成为医生们解剖课的教具
护士笑容如同天使,医护人员的对话如同牧师的临终关怀,躺在手术车上,感觉车子在迷宫一般的手术室楼层穿梭,这是怎样的一种经验和体验?只有这样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穿行、在恐惧与软弱之中煎熬的即将上手术台的病人才能写出来这样的文字。从而,最绝望之病躯所唯一所可依靠的医护,他们的“翕动的嘴唇和美丽安详的脸庞”就成为手术昏迷之前最深刻的记忆。
诗到第二节,已经躺到手术台上,此时的麻药还没有完全生效,还有部分的觉知。诗人所能看到的,只有头顶上的灯,这灯让他想到了外太空前来的飞行器,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可能离去,这离去不是因为手术过程中的种种不虞,而是可能被外星人掳去进入“另外一个空间”。诗人此时此地,反而表现出他的乐观和幽默,他的死生无惧。但他却非要抓住自己的意识,不让“思想”完全失灵并昏迷。最后的刹那,他看到了“思想”从“身体”的游离,仿佛“思想”漂浮于肉体之上而独立存在。他所能做的,他所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是他想“睁开不受控制的眼睛”,“看看/麻木的身躯,如何/成为医生们解剖课的教具”,这是诗人强大意志力的反应,是轻易不让渡思想力的已经成为强大本能的反应。当然,此时的他其实关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死安危,他还关切更宽泛的事物,人间的事物,比如,他这似是诙谐调侃的“解剖课的教具”之谓,未尝不是又一种深入骨子里的悲心光芒。
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觉自主的主体精神,一个顽强、坚强的个人。这样的诗歌,表面和明白的一面是写一种经验,一种记忆,是一种疾病叙事或者治疗叙事,暗里仍有诗人作为现代主体、现代启蒙一代和思想者的坚强的理性。
麻醉
最先醒来的是耳朵
然后是局部的肌肉
思想,准确地说是大脑壳
还停留在醉醺醺的状态
呼吸需借助于氧气机
眼睛还不能自由控制闭合
更多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合上
耳朵里听见的全是远远的切割声
装修房屋时 切割瓷片的声音
很想让呼吸频率跟上切割瓷片的节奏
可是 总会慢了半拍
躺在周遭都是白色的床上
半醉半醒之间
做着一半幻想一半清醒的白色的梦
为什么最早醒来的是耳朵?因为因为听到了声响而从昏迷中苏醒,是耳朵唤醒了自己的灵魂。为什么是然后是肌肉?因为肌肉最早感知到了疼痛;此时,“我”最关心的是“思想”——哦,不,谈不上思想,是脑壳,脑壳仍然停留在昏昏沉沉“醉醺醺的状态”。第一段写苏醒之后的感知,最初最浅层面的感知。
哦,终于留意到了,原来自己的呼吸是靠氧气机;一呼一吸,都仍然艰难。感觉到了,眼睛,“我”的眼睛一开一合还不能“自由控制”,“更多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合上”,如此难!如此难!听到了,“耳朵里听见的全是远远的切割声”,这“切割声”如同装修房屋时切割瓷片的声音,那般锐利刺耳,让人难以忍受。次写六根六尘更全面的感知。
但能判断出听得见这刺耳的噪音,也一定是好消息,是生命苏醒的征兆和示现。只是,“我”觉知到自己的无能无力无可奈何,但作为生命力的反应应激,“我”“想让呼吸频率跟上切割瓷片的节奏”,这会让“我”好受些,也让“我”跟上这外力的牵引——是的,尽管声音难听,但力图呼应这声音的召唤,尽管“我”上气不接下气,尚无法跟上这喧嚣的节奏。此时,“我”也能意识到自己是“躺在周遭都是白色的床上”,“半醉半醒”,“做着一半幻想一半清醒的白色的梦”——半是幻想半是清醒,忽梦忽醒,如梦如幻。身体残损,无能为力,而“我”的意识正逐渐恢复,思想正逐渐回归,正处于这临界点。此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手术之后从昏迷中醒来最初的感知,见闻觉知慢慢恢复的过程,被诗人如斯描刻。一切的宏大在最本真的身体面前,在痛感面前,其实往往都是第二位的。我们在这里,也许看不到升华,但需要升华吗?我们看不到他者,但需要他者吗?疼痛是美学吗?疼痛是自身的伦理。身体是美学吗?身体是自身的美学。只属于自己,个体。这正是诗人的切肤之感,刻骨之感,也是刻录下来的最真实的生命记忆,身体记忆。
穿刺
病人是否有病
通过X光、CT扫描
甚至高精度的PETCT
看到的影像仍然只是表象
医生还是要通过穿刺、活检
才敢
判断这血淋淋的肉块是良性还是恶性
世人的微笑、哭泣
政客的演讲、政见、作秀
我们常常轻易地误判他人的良莠
真正要探究
还是要穿刺、活检其良心
才能
判断曝光下的灵魂是否真正的干净、纯洁
第一节写穿刺之必要,因为X光、CT扫描、PETCT,看到的都只是“表象”,仍是不可确定的,仍然需要“穿刺、活检”才能判断“肉块”的良性、恶性。写的是医学知识。
第二节跳了开来,取了对比手法,也即比喻和象征的修辞,由医学的穿刺术,联想到识人术,世人有笑有哭,有政客有本色有表演,我们常常容易轻易判别他们的“良莠”,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真与假、对与错、正与邪其实往往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样,而应该需要如同这医学上的“穿刺、活检”,才算“真正”的“探究”,才能“判断”得出一个“灵魂”的干净与否。但这是可能的吗?
诗人写到此处,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不置可否,就做了结束。其实这样写,是一种留白式的写作,一种开放式的写作。他所没充分展开而需要读者填空的逻辑是,一个人的复杂性,正复杂如同一个机体组织。机体的良性恶性难以轻易判断,正如一个人的好坏善恶不能轻易判断。一个机体组织的定性需要动用十八般武艺,一个人的定性自然也需要过五关斩六将。但机体组织的分析判断靠的是仪器,手段是科学,人呢?复杂如精密仪器的人性,该当使用怎样更精密的仪器来穿刺活检辨析呢?由谁来执行穿刺活检判断呢?谁能科学精密过仪器呢?
这样看来,这首诗,就实现了诗性的飞跃和思想的跳跃,成为一首讽喻诗了。我们的诗人,终于彻底苏醒了过来,从肉身的疾病叙事一跃而为社会性批判的疾病叙事。实现了作为肉身和思想的满格复活。
作者简介杨华标,1967年生,广东龙川人,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哲学学士,曾任职于星海音乐学院、深圳某艺术团体等单位,现为企业高级职业经理。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有诗歌等作品发表于《特区文学》等报刊。
于爱成,1970年生,山东高密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博士、研究员,文学创作一级。现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系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出版有《深圳:以小说之名》《新文学与旧传统》《四重变奏》《狂欢季节》《细读:文本内外》《诗与思的对话》等专著7部,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多篇。历获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