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年间,在吉林伊通县城的西门外,有一刘姓人家,以开菜园子为业。
日积月累,家族兴旺,修建了一个大院子,很引人注目,这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并不是一件好事。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伊通县城驻军第三十三团二营的五、八两个连哗变了,他们同当地有名胡匪“赵全胜”绺子同流合污了。不久,甚至传来他们要攻打县城的消息,县城里第三十三团赶紧加强了防守。
到了11月4日拂晓,北山皮的大股胡匪和哗变的士兵汇集在西门外,开始攻城,双方激战1个时辰,胡匪从西壕线攻进了县城。他们进城后围攻县署和三十三团团部,砸电报局,四处抢劫,整个县城陷入一片混乱。
5日上午,一股胡匪闯进了刘家的院子,为首的就是全胜绺子(绺子:一伙一伙的土匪)的“孙傻子”。这群土匪刘家全家老小驱赶到一个屋里,然后到各屋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
在一个箱子里翻出一个匣枪壳子来,这下可惹出是非。既然有壳子,那就肯定有钱,土匪就逼问刘家人。原来这个箱子是一个亲属寄存在此的,刘家人根本交不出枪来。
土匪遂下狠手,把刘家两个孩子,13岁的刘庆祥和他6岁的小侄儿掠走。土匪心里清楚得很,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未成年的男孩,这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所在,只要拿住了两个男孩,就不怕刘家人不乖乖就范。刘家人上前去抢孩子,被土匪一个个踢翻在地。
刘庆祥两人被胡匪天兴源的饭房里,饭房的炕上早已坐满了被绑来的“票儿”,有天兴源掌柜的赵老贵,西门外王家油坊当家的王瘸子,西门外祝大眼珠子,煎饼铺的郭山东子,还有西门外的徐关门。这个徐关门是当地有名的地主,他们家每年能吃三四百石粮,他怕胡匪抢劫和绑票,无论白天黑夜宗室大门紧闭,所以被称为”徐关门”,没承想他也被抓来了。
看守“票儿”的土匪脾气不好,谁在炕上稍微晃动,就劈头盖脸一顿毒打。
此时胡匪早就做了准备。过梁上搭着一条绳子,凳子上放着马鞭子、马缰绳,旁边还准备一堆小灰。几个匪徒袒胸露怀,目射凶光,铁青的脸上还挂着一丝狞笑。他们把我们当中的一个做小买卖的叫到跟前,逼他说出家有什么贵重东西,藏在什么地方,这个做小买卖的哀求道:”老爷们行行好,我是做小买卖的,家里什么也没有。”一个匪徒吼道:“行好?你上庙里找和尚老道去,我们这是卖人肉的,得拿钱来买。”说着就上来两个人,用布把他的眼睛蒙上,扒掉上衣,用扁担把胳膊支起来,再用绳子把他吊到过梁上。两名匪徒站在过梁的两侧,用马鞭子疯狂地鞭挞起来。那一道道鞭痕,一滴滴鲜血,一声声惨叫,使人撕心裂肺,肝胆欲摧,目不忍睹。每当他惨叫时,匪徒就抓把小灰扬在他嘴里。惨叫声消失了,呼吸声没有了。当他缓过气来再叫时,从口腔和鼻腔里就喷出血水来。
他们就是这样用这种最残忍、最凶暴、最野蛮的手段拷打着人票。这些丧失人性的土匪,简直就是衣冠禽兽。
秧子之中只有4人没有挨打,可他们没有捞到多大油水,只是税捐局胡主任说他家有600块现大洋埋藏在北炕洞子里,让他们去取。600大洋不是小数目,他这么一说就停止拷打。该轮到刘庆祥,刘庆祥见胡主任说他家有大洋就不打了,也照说:“当家的别打了,我家有地窖,啥东西我不知道,天亮我领你们去起。”这一招真灵,果然免受了皮肉之苦。剩下还有3个,他们也照葫芦画瓢,有的说家有枪支的,有的说家有金银首饰的,也有的说家有地窖的,都答应领他们去取。
第二天下午,来了一个50多岁的胡匪,他是全胜绺子秧房掌柜的“老头好”,叫张焕臣,这些“秧子”都得归他管。听老头好这么一说,大家就下地换农服。地下堆满了胡匪抢来的,上好的衣服都被他选走,不值钱的就扔在这里。大家七手八脚地换上了几件衣服,而刘庆祥只拿了 3个狗皮套袖。
天黑时老头又对大家说,凡是一家有两个绑票的留下一个,放走一个,留大不留小,刘庆祥6岁的小侄被放了。
“老头好”见大家换好了衣服,天也黑下来,就喊了一声“挑”。所有的“票儿”3个人一组被绑成一串,共9串27人,被土匪押着从北门出去后往县城的西北方向走去,再往西走一段路程,又往南走去。到西大岭乱尸岗子时,孙傻子向那两个匪徒吼道:你两个眼睛瞎了,没看这些秧子要蹦吗?"
原来孙傻子以为有人要跑,遂一边下马一边喝着:“滑住!”
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他拉开枪栓,推上顶门子,冲着人群就开一枪。这一枪如同晴天霹雳,把刘庆祥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眼冒金花,刘庆祥定睛一看,顿时魂飞魄散,发现他们这串的另一个票儿被枪打倒了,那人只哼了一声就死了。孙傻子上前用刀挑开了线对我们骂道:“狗XX,看谁敢跑,就叫他去摸阎王鼻子!”“票儿”们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连一步都不敢错,在阴森森的黑夜里向前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行了多少路程,走到什么村落,“票儿”被押到一间黑黝黝的屋子里。这群“票儿”从5日上午被绑到现在滴水未饮,粒米未进,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心想要饮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可是无人敢说,只得忍着。“哐当”一声门开了,有人端来一瓢凉水让大家喝,这才让大家解了渴。
不一会儿,孙傻子走进屋来,用脚连踢带踹喊到:快起来“啃富!"“票儿”中有人愣住了,不知是什么意思,小声问身旁的人,什么是“啃富”,才得知这是黑话,是吃饭。
土匪自有一套黑话,不是所有人都听得懂。
饭是一盆小米饭,一盆猪下水汤,这对饥肠辘辘“票儿”来讲无疑是人间美味,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碗筷,狼吞虎咽地填饱了肚子。
孙傻子又下命令,叫我们到外边“登轮子”,也就是坐车。
6日上午到了靠山镇,靠山镇是胡匪的天下,也是土匪的老巢。从县城撤回来的各路绺子和哗变的士兵都集聚在这里。胡匪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到处是人喊马嘶,闹得鸡犬不宁。
“票儿”被押到侯家店,有7间宽敞明亮的店房,胡匪出出进进,听说他们在这里要"拉片子,也就是分赃。哗变的五连李连长走进了店房,仍然穿着灰军装,背着三八枪,挎着匣子。他坐在南炕沿上,操着上口山东腔对匪徒和士兵们骂街:“俺说不出来,你们非拉出来。打了一次县城每人才分7钱金子,13钱银子,挣饷钱也比这个多。当一次胡子一辈子也扒不掉贼皮。”他骂了一 通,众匪默默无言。
这个时候,胡匪放了几个票儿,他们是通过有靠山的亲友和胡匪通融才脱离虎口的,剩下的19人被押出了侯家店往西沟走去。走了五六里,我们又登上了轮子。突然响了一阵排子枪,说是“洋跳子”(警察)从公主岭来到了太阳岭,胡子们要“硬挑”。
19名“票儿”都心惊胆战,生怕在混战中一个没注意就成了炮灰,大家都坐在车上,有人默默无言,有人短叹长吁。
9日晨,“票儿”到了三道岗子村,被带到一座三合院。这座院很气派,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5间。“票儿”被押到正房西屋的里间,挤在一铺炕上。孙傻子和那两个拿棒子的坐在南炕上看着我们。在外间的南炕上坐着一个老头,身披貉绒皮袄,双臂被反绑着,这个场景谁都明白,这老头是个“大秧子”,是土匪此次获取的大猎物。
但“票儿”们这次搞错了,这个一身福贵的老头其实也是土匪,“票儿”们从土匪们的谈话中得知他叫“西恩厚”。五连哗变的一个班长,现在匪名叫海蚊子,他说西恩厚独吞了大饷,要他把赃物交出来。西恩厚对海蚊子起誓道:“我要吞大饷,对不起炮手,不得好死。”海蚊子见他盟誓,没再追问,就来到里间吩咐孙傻子道:“秧子没过筛子的得赶快过,天冷了,没油水叫他们滚蛋。”孙傻子说一两天就过完。
海蚊子转身刚要走,西门外煎饼铺的郭山东子对他恳求着:“俺是煎饼铺的,西门外谁不认识,把俺放了吧。”海蚊子叫他下地了。郭山东子没等给他松绑,望一眼祝大眼珠子又对海蚊子说:“他家是出布床子的,布都给抢没了,用啥抽票子?”海蚊子也叫他下地了。原来这祝大眼珠子是郭山东子的房东,交往甚密,所以才给讲个情。郭山东子被松绑后,指着刘庆祥对海蚊子说:“他是刘家园子的,你要大白菜拉两千斤吧。”海蚊子笑了笑说:“你们仨都快滚蛋。”
刘庆祥听了他这句话,心里像开了两扇天窗,非常高兴。我们刚要走,从大门外又来伙胡匪,闯进来问道:“他们要干啥?”海蚊子说:“他们都是穷光蛋,叫他们回去。”其中一个匪徒说:放了?1000不抽,500能不能抽?500不行,三二百还不能抽吗?"
几个刚要走的“票儿”激动的心顿时被剿灭了。
那个匪徒看几人紧张的样子,就缓和地说:“海蚊子叫放人能不放吗?我是跟你们闹着玩的,我们把你们放了还有小帮呢。你们走路要小心,遇见屯子口有人要绕道走。”几个“票儿”记下了他的话,匆匆地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走了一个时辰,刘庆祥有些跟不上,郭山东子就斥责他。郭山东子解释道:“你不知道,俺家北门灶子里藏有两支匣子,也不知翻出去没有,我很惦念。”一个开煎饼铺的家里藏着枪,刘庆祥感到惊奇。后来才知道,这郭山东子是个有钱人家,光吃租粮就100 多石。“票儿”一路上担惊受怕,过了大孤山的德云堂,一颗心才落了地。
在胡匪绺子里熬过了24个日日夜夜,“票儿”才逃回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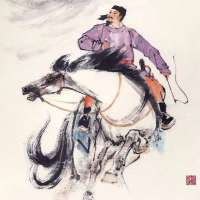
美人绝色原妖物,乱世多财是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