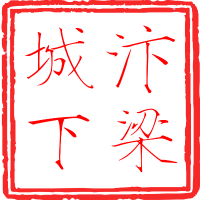以为河南人民痛苦大声疾呼而声震历届参政会的郭仲隗先生,任过民国时期的豫鲁监察使。他是一个老同盟会员(百年老店国民党前身),有直爽的性格及光明磊落的人格与正义感。

宣统元年(一九〇八)正在省立武陟中学读书,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发现而捉了起来,关在卫辉府的监狱里。靠了许多师友的营救,地方官没有把这案子报上去,所以得免一死。但终身监禁是注定了。
他进监狱的时候,就有朋友告诉说:狱卒对于囚犯的勒索敲诈是无止境的,进监的时候必须把门事头打硬,无论怎样折磨,都要咬牙忍受,千万不可说出钱的话,等他知道用什么都不能榨出油水时,就不再发难了,否则什么时候缺钱花就紧紧你的串,那就永远填不满他那无底洞了。
听了朋友的话,在进监的时候,他就决心以最大忍耐来对付狱卒的摆布。无论大串(清末的夹刑具)多么紧,都一声不响,脚磨烂了,浑身臭虫咬得发肿,每天吃的只有一斤红薯,这样过了一个多礼拜,狱卒看到榨不出银子。以后也就不再故意为难,头一关算过去了。这样从春天躺到了秋天。
有一天串房里添了一个新犯人,是汲县北山中的一家大户,捕班想敲他的钱,便诬他为匪而捉了进来,按法律,土匪就该躺串,但这个人花了六百两银子给狱卒,大串便不躺了,只搬了张椅子坐在串房里,于是纠纷开始了。
“这像伙非常讨厌,不躺你就坐在那里吧,但还不知足,坐着还要吸水烟,拿着一根水烟袋咕噜咕噜的吸个不停,还会扑的一声把烟灰吹到别人的身边,烟灰薰得前屋人咳嗽,他仍满不在乎”。郭先生叙述这事时说。
屋裹人不三不四骂着,埋怨着。狱卒来查串了,绕了一周,要出去时我止住了他,“休走”!我有点事要问问你。狱卒看到我不像说好话的样子,便搭讪笑着说:“不要胡扯八溜,有话明天再说”。“不,我得请问:在监里的人是论银子多少呢?还是论犯罪的轻重?你今天得给说个明白。如果论银子多少,老子有银子,说明白了老子也给,如果是论罪的轻重,那么那个吸水烟的家伙为什麽不躺串?”,“是你的串紧了吧?来,我给你松松”。狱卒把话向一边扯。

“不必松!国家把我关在监里是要我反省的,不受罪怎么会反省。我的串越紧越好”。
“没有正经话不要瞎扯”,说着想出门了,他看毫无结果,便又警吿他说:“我问你的事你今天如果不给说个明白 明天我可要告发你”!老监霸听我在吵,便问旁人:他打的什么官司?旁人把我案子告诉了他。老监霸是个很义气的人,听说打的是革命官司,立刻说:不要躺串了,明天跟我般到一块住。老监霸是囚犯中间自然形成的领袖,在监里很有号召力量,管狱员为了避免出事,便也承认他的特殊地位,给他以特殊待遇,交换条件是不准监狱里打架及发生逃脱。
这位老监霸是山东人,练得一身好武艺,很有梁山泊上好汉的风度。因为替人打抱不平,打死了人,从家乡逃出来,干上了绿林工作,后来犯案坐监的,因为他最义气,所以到监里的匪犯,只要是敢作敢当,决不攀扯朋友的汉子,他就特别尊重。如果说谁挨了一顿打,把朋友都攀扯出来了,那来到监里,就休想受到他一口好气。因为他的正直和侠义,无形中在监里造成了一种尊敬刚毅,鄙弃怯懦的风气,郭先生提到他时,总眉飞色舞的谈他那些杀人越货的故事。

民国二十八年,做着河南省政府委员,在他的资历上,省政府委员是他第一个正式官衔。
黄河改道以后,整个豫中有全陆沉之虞,春汛将临的时候,他奉命去鄢陵主持黄河新堤修筑工作。
新堤的修线有二:东线沿着泛区,西线则远在鄢陵城边,计刻是先修东线;如果东线失败,则改修西线,以免泛区过于扩大。但在东西两线之间,是定居着几十万人口,存在着无数村舍田园的。
东线工程完成的期限,省政府是规定了的,他一到鄢陵,便亲自到堤上主持,把四面八方征来的堤工严密组织起来,按照工作的性质分成班。绳索,杠子,箧子,一切工具都严令事先准备充分,以免临时因缺乏工具而是延搁工程进行。
工人都热烈的工作着,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田园,在东西两线间几十个村落中的民众,更自动前来参加作工,他们的生命财产都寄托在这条堤上。如果东线抢修不成,他们的家就要到入泛区,而他们的一切也就完了。
省府限定的日期到了,郭先生在工程处静候着合拢的消息。堤工上的人是紧张到万分,打椿,抛石,推土。每一个人的眼睛,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民的最后一分力气,都贯注在阻遏那最狭的一股黄流上。但是他们失败了。
当失败的消息的报告到时,成千成万的民众也围住了他。民众要求把合拢的工作再展限一周。代表们在说明工程失败的原因及一周后一定可以合拢的道理,说明大家一定努力工作,郭先生虽然明知大汛的危险,明知答应展期责任太大,但在群情乞求之下,他感动得不能不答应,于是他答应一面向省府请求,一面继续抢修东线。
省政府给他的覆文并未正式批准展限,只说大汛将届,泛滥堪虏,要他慎重处理。
第二周有老百姓告诉他,说这次合拢一定可以成功,因为“黄大王”来了,农民的经验是来修堤时有黄大王来,堤一定可以修好,他跟着老百姓到堤上去看,果然有条小花蛇盘在黄裱纸上,男男女女在围着这条蛇烧香祷吿。村庄上在搭起戏台,为黄大王唱戏。

但时限届满时合拢又告失败了,几万男女老少,又都跪倒了在戏台前面,哭号着,乞求着,要求再给他们展限一个礼拜。
他知道再请省府展期是决不会核准的,然而看着人民哀怜的面孔,看着几十里的田园庐墓,他知道他的一个“否”字要决定多少人的生命,他没力量拒绝人民的请求,于是他走到戏台上。
大家要求再展限一个礼拜,这在省政府是决不会准的,不过,我现在提出几个条件来,如果大家愿意照办,我可以私行担保再展期一礼拜拜。“郭委员,你给甚么都可以,我们一定遵办呵,”民众欢呼起来。
“第一,各家无论男女老少,只要又工作能力的人,都动员到堤上来做工。第二,十五里以内的车辆,要完全拉来运料。第三,由近及远,不问谁家的,逢庙拆庙,逢柳砍柳,逢麦秸堆拆麦秸堆,先记账,不付款,一切能用的材料都运到堤上来,等堤修好了再去算账,大家要是同意我就再展一礼拜。”民众感激得流泪了,不要说拆庙砍柳树,就是拆他的房子,只要不把他的地全淹进去,他也干呵。
不止十五里,所有东西二线间村庄上的人力,畜力,材料都动员了起来。
第二天到了,还没合拢的消息,我不得已只好只好偷偷的溜走了,溜到了离堤二十五里的一个村庄上。如果第二天仍不能合拢,就不再和堤上的民众见面,回鄢陵去下令修西线了。因为再要展期,谁保不几县都陆沉下去。郭先生谈到这里时就有一种潸然的味道。
但这一次合拢成功了,第二天中午勤务骑了马找我报告消息,我立刻就原马骑到堤上。工人还正在紧张的荷土,连村庄戏台前面都空无一人,只有台上锣鼓声喧。
“他们在韩四营给我立了个纪念碑。”

三十一年河南大旱,岁尾年首,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人民饿死了三四百万。杀子而食的骇闻,到处传布着。
灾荒的照片在伦敦纽约的报纸。刊布出来。灾荒的新闻使蒋夫人在美国羞的昏厥。
粮食部要去河南办理平籴了,拨了二万万的巨款,组贼了平籴委员会,请等政府主席李培基兼主任委员,当时是参政员,后来因农工银行大舞弊案被揭发布而潜逃无踪的李汉珍为副主任委员,负实际责任。河南的征实征借还在照旧严刑押追。

郭先生是参政员,正在重庆为河南救灾工作而呼吁。他反对李汉珍,因为他知道李汉珍的贪污鄙皁,与无耻。他知道要李来办平籴不过等于向灾民多榨一次油,所以粮食部要聘他作平籴委员时他便谢绝了。
粮食部从李汉珍那里得来一个印象:郭仲隗专门反対粮食部,徐堪部长的印象尤深。
一个下午,郭先生和另外两位参政员去财务部会见孔祥熙部长。路不熟,摸进了粮食部的院子,看表,和孔约定的时间还早,于是决定顺便看看徐堪,问一下河南征实减免的案子。
几个人走选了粮食部部长的会客室,听差的请他们等一下。半点钟过去了,他们等得不耐烦,说要走了,徐堪才从办公室跨出来。
没有什么寒暄,徐堪就把题目拉到平籴委员会上来。“你们就是反对李汉珍,也不愿和平籴委员会拉在一起,平籴委员为什么也不干呢?”徐堪部长很不客气的问郭先生。
“不干平籴委员是因为一时无法分身回豫,何必担此虚名?至于说不干平籴委员是反对李汉珍,这完全是猜词,平籴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李涵础,倘说反对李汉珍,不更是反对李涵础么”?郭先生很客气的解释,不愿在人事问题上去争辩。
“你们河南的事情根本没法管”。徐堪的话带着申斥的气味了。
郭先生其实也并不是好脾气的人,虽然想教训他的人是一位部长老爷,他这时可没想到官的大小,于是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你不管正好,没有你来管,河南饥死不了这几百万人”!“平籴委员名单是你们开的,开来了为什么不干,不是故意和粮食部为难吗”?徐堪更气了。
“哪个开给你的,请把名单拿出来对证一下”!“那算我糊涂!我糊涂!”徐堪气得面红耳赤,咆哮着!两手摆动着站了起来,完全忘掉了他处的境地。“糊涂还当部长?你岂不祸国殃民”!郭先生也吼了起来。
“你们参政员不是皇帝,也没权把我的部长撤职”,“撤职!我要有权撤你的职,还会让你干到今天”!同来的参政员赶紧排解,粮食部的职员勤务莫名其妙的看着这幕剧的演出。
不欢而散的结果,是有人埋怨郭先生了,说他性子太暴,粮食部不肯减免河南粮额,就是因为他和徐部长吵了架。不过他可并未因此而放松呼吁减轻人民负担的努力。
中原事变的时候他和家眷正住郏县。敌人在郑州渡河的消息才传到这偏僻的县域,将军们已经席卷了地方的财政,逃得无影无踪!人民和他们自己的武器一齐委弃给敌人了。
郭先生没有向大后方逃难的经济力量,携眷狼狈逃到嵩县山里友人家中,在敌人的包围下度了三四个月不堪想象的艰难日子。他亲眼看到那些守土将士的“战绩”,及他们怎样对自己的同胞。
秋季参政会开会时他冒着敌人的封锁,攀绝崖,翻峻岭,穿过了八百里伏牛,赶到了重庆。上午从珊瑚坝下机,下午就出现在参政会的会场里,他要以他的亲身经历,向全国至世界控诉将军们的罪行。他的声音震撼了重庆山城。
劝诱,疏通,威胁,压迫,都没有使他改变态度。但人民的声音是没力量的,将军不过调防了事,他失望了!一种沉重的难以言喻的失望。
参政会闭幕后他取道陜南回豫,路过商南时又碰到一次危险,一班查店的武装兵士指名索他,他翻出了后墙,在迷失的稻田里山坡上爬了一夜,跌得满身创伤,幸得免于暗算。

以后豫鲁监察使的命令发表了,他犹豫又犹豫的就了这个“特任官”。
(本文来源)公众号 河朔知事 马琳
供稿:新乡郭仲隗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