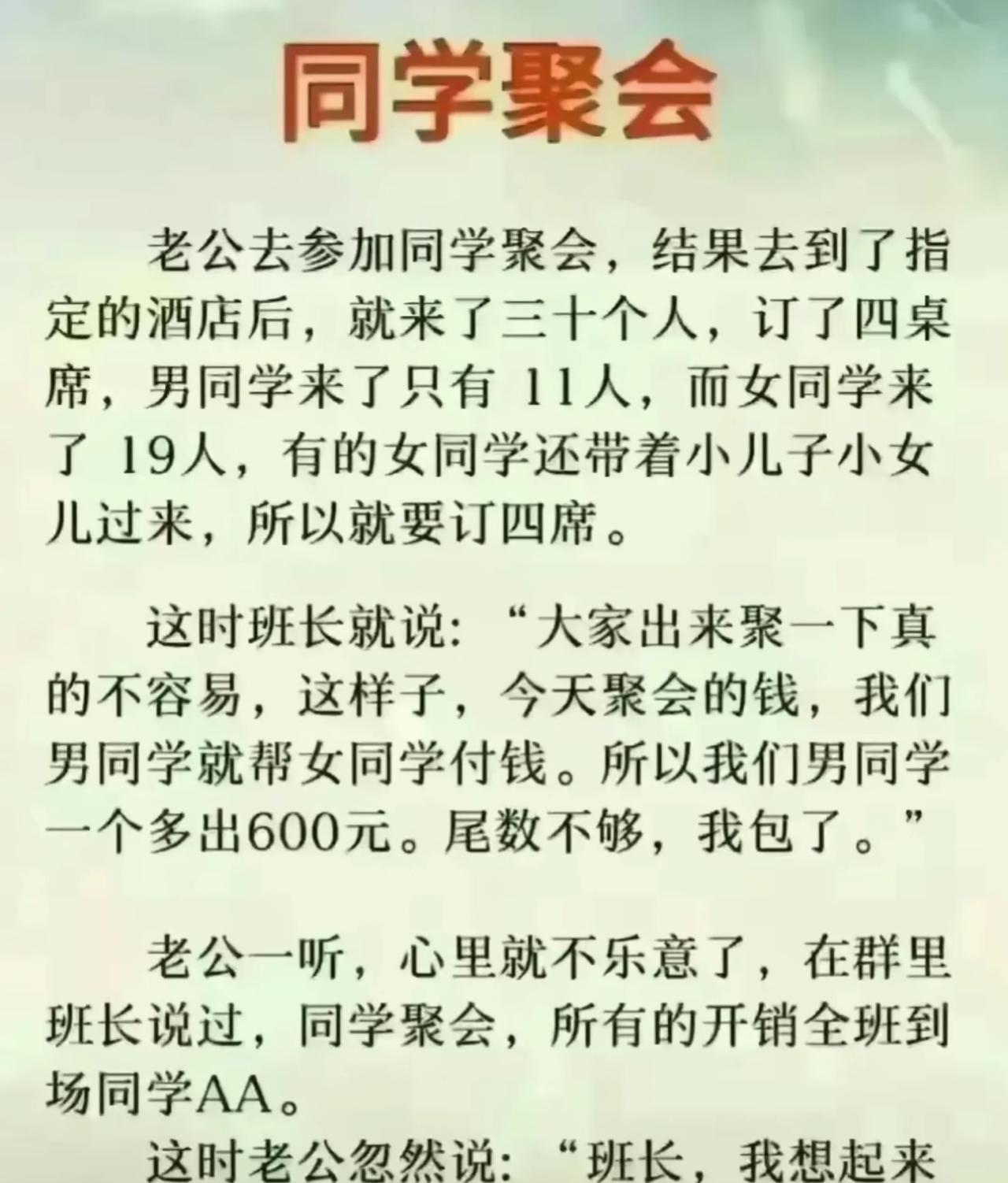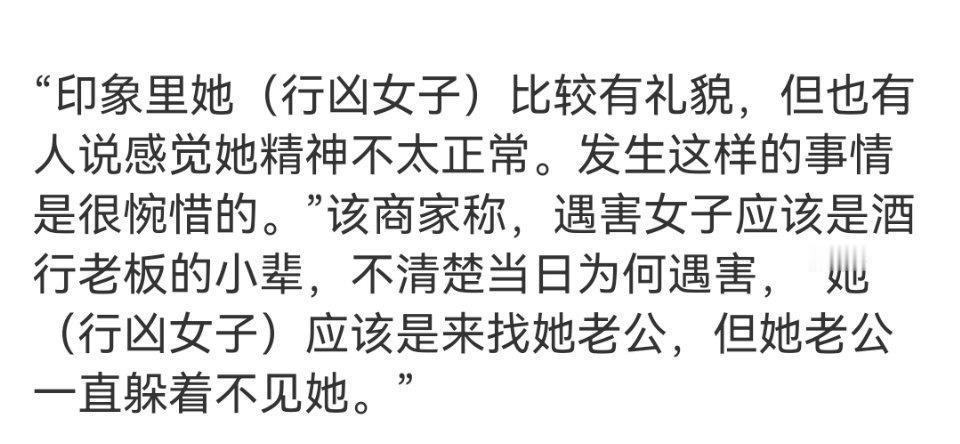恨了四年的“陌生女人”,是我曾拼命想报答的人!推开家门我僵在原地 六月的风裹着毕业季的燥热,吹得行李箱滚轮发烫。站在熟悉的单元楼下,我望着三楼亮灯的窗户,心里像塞了团浸水手帕——这是我四年没踏过的家,也是我发誓“有陌生女人在就绝不回”的地方。 四年前,母亲去世刚满三年,父亲说想再找个人作伴。我正翻着母亲的旧照片,相框“啪”地砸在地上,玻璃碎渣溅到指尖。“我妈才走多久你就忘?你找别人,我再也不回这个家!”喊完这句话,我抱着行李搬到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寒暑假要么打工要么泡图书馆,连春节都躲着不回。父亲偶尔打视频,只要听见电话那头有女人声,我立马挂断——那“陌生女人”在我眼里,就是破坏家庭、忘了母亲的帮凶。 直到辅导员催着清空宿舍,我实在没处去,才咬着牙拎行李回来。钥匙插进锁孔时,手指止不住地抖。推开门的瞬间,一股熟悉的香味钻进鼻腔——是糖醋排骨,母亲生前最擅长做的菜,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偏爱。 我愣在门口,就见穿浅蓝色围裙的身影从厨房走出,手里端着冒热气的砂锅。她听见动静抬头,笑意熟稔得让我心头一震:“薇薇回来啦?算着你今天毕业,特意炖了排骨。” 看清那张脸的刹那,行李箱“砰”地砸在地上,滚轮还在原地转了两圈。怎么会是刘阿姨? 母亲刚走的半年,我像丢了魂,每天躲在房间哭,连饭都不吃。有次在小区长椅坐了一整晚,凌晨时刘阿姨拎着热包子走来,蹲在我面前轻声说:“孩子,再难过也得吃饭,你妈妈看见会心疼的。”后来,她总以“顺路”为由给我带刚烤的面包;我考试失利躲在楼梯间哭,她递来纸巾说“一次没考好不算啥,阿姨信你”;连我第一次来例假慌得手忙脚乱,也是她悄悄塞来卫生巾,手把手教我用。 她是母亲最好的朋友,是我人生至暗时刻唯一拉过我的人。可后来她搬了家,我们就断了联系。我怎么也没想到,四年后,她会以“继母”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家。 “怎么了?是不是累着了?”刘阿姨放下砂锅,快步过来想帮我拎行李,我却下意识往后退。她的手僵在半空,笑意淡了些,却没生气:“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没关系,咱们慢慢来。” 这时我才注意到,客厅茶几上摆着母亲的照片,相框擦得一尘不染,旁边还放着束新鲜白菊——那是母亲最爱的花。阳台晾衣绳上,挂着父亲的旧衬衫,还有我高中穿的连衣裙,洗得发白却叠得整整齐齐。 “你妈妈的照片,我每天都擦一遍,怕落灰。”刘阿姨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声音轻了些,“你这件裙子,想着你说不定还能穿,就没扔,洗干净收在衣柜最上面了。” 喉咙像被堵住,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原来我恨了四年的“陌生人”,一直在替我照顾父亲、守着这个家,连母亲的喜好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突然想起,这四年父亲每次打生活费,总会多打两百,说“买点好吃的”;去年冬天我感冒发烧,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我是刘阿姨,听你爸说你病了,寄了感冒药”——当时我以为是诈骗,直接挂了电话。 “爸呢?”我声音沙哑,盯着地上的行李箱,不敢看刘阿姨的眼睛。 “去超市给你买草莓了,知道你爱吃,特意挑新鲜的。”刘阿姨笑着转身往厨房走,“排骨还得炖十分钟,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温水。” 看着她的背影,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在厨房忙碌,刘阿姨坐在客厅陪我写作业,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暖得让人犯困。原来我一直以为散了的家,从来没垮过;我抗拒的“外人”,其实是想帮我撑起家的人。 我弯腰拎起行李箱,走到沙发边坐下。茶几上放着本相册,翻开第一页,是母亲和刘阿姨的合照,两人笑得灿烂。后面几页多了些陌生照片:父亲在公园打太极,刘阿姨在旁边拍视频;父亲生日那天,刘阿姨订了小蛋糕,上面写着“老周,生日快乐”。 原来这四年,不是父亲忘了母亲,也不是刘阿姨“插足”,而是两个孤单的人互相陪伴,把这个家撑起来,等着我回来。 门口传来钥匙转动声,父亲拎着草莓走进来,看见我眼睛瞬间亮了:“薇薇回来啦!这草莓刚摘的,可甜了!”他把草莓放在茶几上,又朝厨房看了眼,小声跟我说:“你刘阿姨昨天就开始炖排骨,说怕你吃不惯外面的饭。” 我看着父亲眼角的皱纹,看着厨房忙碌的刘阿姨,再看看母亲的照片,鼻子突然一酸。原来这四年的抗拒,全是多余。真正的家,从不是只有血缘,还有藏在细节里的温暖。 刘阿姨端着排骨出来,笑着递过筷子:“快尝尝,跟你妈妈做的是不是一个味。”我夹起一块放进嘴里,熟悉的味道在舌尖散开,眼眶瞬间湿了——是家的味道,是我想念了四年的味道。 原来有些相遇不是打扰,是救赎;有些接纳不是背叛,是成全。我恨了四年的人,其实一直在替我守护最珍视的家。父亲是孩子永远的偶像 社会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