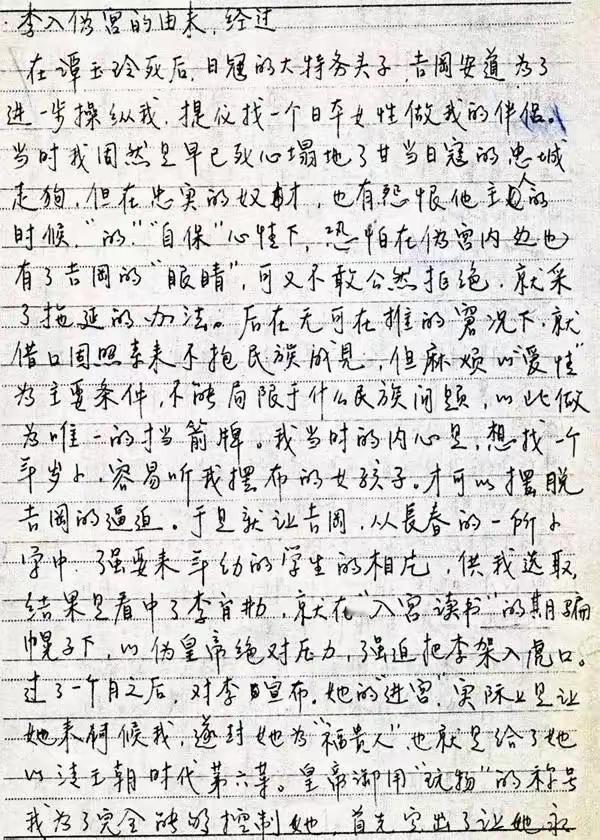1950年,正在接受改造的溥仪听到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突然撕开棉衣,取出一物件说:“这是我从紫禁城偷出来的,现在自愿交给政府。”看守拿过来一看,当下傻眼了….. 那是一件巧夺天工的宝贝,一方由三枚印章用链子连在一起的“三联玺”。 这东西一送到北京,专家们一看,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可不是一般的宝贝,这是乾隆皇帝生前最珍爱的私人印章,田黄三联玺。 这三枚印章,一枚刻着“乾隆宸翰”,代表皇帝的身份;一枚刻着“惟精惟一”,出自《尚书》,是乾隆的治国理念,提醒自己要兢兢业业;中间一枚椭圆的,刻着“乐天”,取自《周易》,又流露出这位帝王希望像个普通人一样乐天知命的愿望。 这东西,是溥仪的命根子。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仓皇之中,什么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大部分都来不及带。但他贴身的棉衣里,却死死地藏着这枚三联玺。为什么?因为在溥仪心里,这不仅仅是值钱的古董,它是大清帝国最后的余晖,是祖宗的象征,也是他日后“复辟”的念想和精神寄托。 从北京到天津,再到东北去当日本人的傀儡皇帝,这枚印章陪着他经历了人生中最屈辱、最颠沛流离的岁月。日本人投降后,他想跑到日本,结果被苏联红军截胡,送到了西伯利亚。在苏联的战俘营里,他几次三番申请加入苏联国籍,甚至想留在苏联,但他从来没想过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当敲门砖。 这枚印章,就像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和那个辉煌的过去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联系。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被他看得比命还重的宝贝,为什么在1950年,他却心甘情愿地交了出来?是为了减刑?为了讨好政府? 有这方面的原因,但绝不是全部。要理解溥仪的这个举动,就得看他当时正在经历的“改造”。 刚被引渡回国时,溥仪怕得要死。他觉得自己犯下的罪,尤其是投靠日本人搞伪满洲国,枪毙一百回都够了。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无尽的羞辱和清算。可没想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受到的不是酷刑,而是“学习”和“劳动”。 管理人员找他谈心,告诉他:“你的错误,很大一部分源于你的出身和历史局限,党和人民愿意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话,溥仪活了半辈子,从没人跟他说过。从小到大,他身边的人不是怕他,就是利用他。第一次有人把他当成一个可以被理解、可以被教育的“人”来看待。 他开始学着自己穿衣服、系鞋带、叠被子。这些对普通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事,对这位前皇帝来说,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他还跟着大家一起去劳动,糊纸盒、打扫卫生。当他靠自己的双手完成一件工作时,那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远比当皇帝更让他踏实。 更重要的是,管理所组织他们参观日本侵华罪证展览。当溥仪亲眼看到那些记录着民族苦难的图片和实物时,他内心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皇帝梦”,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灾难。他的那点个人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渺小得不值一提。 所以,当1950年,他听到国家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保家卫国时,他内心深处沉睡的民族认同感被唤醒了。全国人民都在为国家贡献力量,他,爱新觉罗溥仪,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做点什么? 他想到了那枚三联玺。 他知道这件国宝的价值。在国家最需要钱的时候,它或许能为前线的战士换来几门大炮,几箱药品。更深层次的,捐出这枚印章,是他与自己过去身份的一次彻底决裂。 这枚印章代表的是“家天下”的封建皇权,是他复辟梦的最后寄托。把它交给代表人民的政府,就意味着他从心里承认,“天下”不再是爱新觉罗家的了,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 这是一种真正的“缴械投降”,不是向某个政权低头,而是向一个崭新的时代,向“人民万岁”这个理念低头。这是他从一个旧时代的符号,转变为一个新时代公民的“投名状”。 所以当看守看到这枚国宝时,他傻眼了。他或许无法理解这枚印章背后复杂的历史和情感,但他一定能感受到,眼前这个叫溥仪的犯人,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 后来,政府收下了这件国宝,并且明确告诉溥仪,捐献国宝值得表扬,但这和他需要接受的改造是两码事。功是功,过是过。溥仪对此也完全接受。1959年,因为改造表现良好,他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成了一名真正的新中国公民。 如今,这枚“田黄三联玺”静静地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成了镇馆之宝。它见证了一段传奇,一个皇帝如何从“朕”变成了“我”,一个国家的宝物如何从皇帝的私产,变成了人民的财富。溥仪的一生,让人唏嘘,但他最后亲手为自己的皇帝生涯画上的这个句号,却足够深刻,也足够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