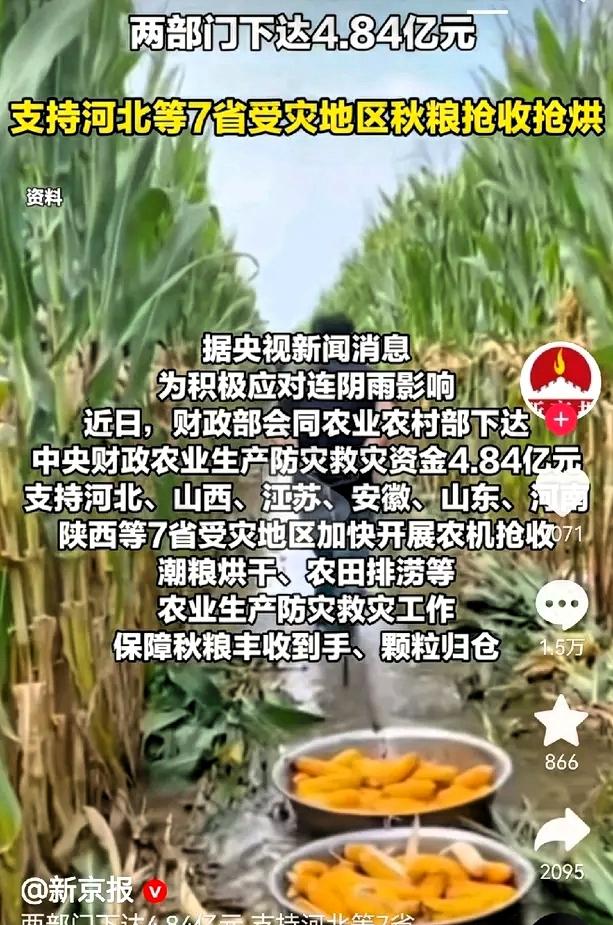我爷爷今年82了,看新闻里说涝灾,他就念叨:"这雨,跟1964年那天杀的一模一样!" 每次一提起那年,他的话就像打开了闸门,满是庄稼人的心酸。 爷爷说,1964年立秋后就没见过太阳,雨连着下了快一个月。地里的积水漫过小腿,站在田埂上能看见小鱼在谷子苗间窜来窜去,那景象看着热闹,心里却凉半截。地窖里存的地瓜全烂了,一掀开窖盖,酸臭味能飘出老远,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挑去倒掉。 更难的是没柴火,灶膛里没了正经木料,只能把没抽穗的高粱杆掰下来烧,火苗弱得煮不熟饭,炒出来的谷子又涩又苦,咽下去都剌喉咙。 那时候全村人都拼了,男人们光着膀子挖河道,手掌磨出血泡也不歇;女人们挎着竹篮运淤泥,裤脚湿透了就拧拧水接着干;就连半大的孩子,都跟着帮忙递铁锹、送凉水。 没日没夜地干,硬是靠手挖肩挑,扛了一个多月才把积水排出去,可地里的庄稼早就烂得差不多了。 现在再遇涝灾,可比当年强太多。手机上提前好几天就有天气预报,红色预警一出来,村里的抽水机就全拉到田里,轰隆隆一响,积水半天就能排下去;种的玉米品种也耐涝,就算泡上两天,及时排水还能保住一部分收成。 可每次看到新闻里倒伏的玉米,爷爷还是会红着眼圈说:“现在有机器帮忙,不用再靠命扛了,可庄稼人看着苗倒了,心里的疼还是一样的啊!” 其实爷爷说的,不只是两代人对抗天灾的差别,更是庄稼人刻在骨子里的土地情结。你们家里的长辈,是不是也讲过过去跟天灾硬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