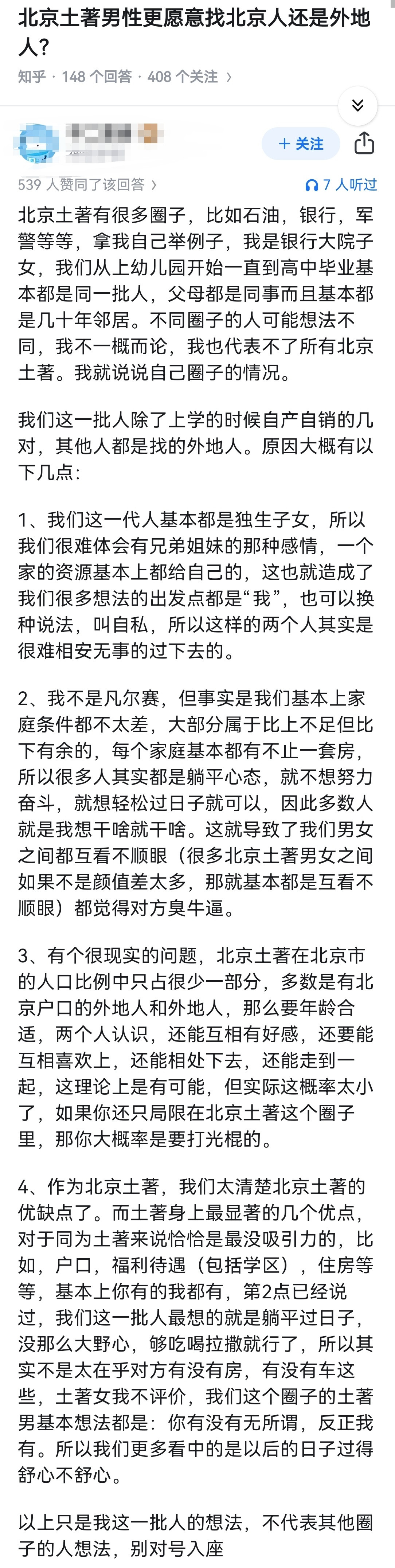1967年的北京,秋风卷着枯叶扫过胡同,茅以升推开老宅木门时,指节还沾着妻子戴传蕙灵前的香灰。 妻子走了刚满百日,快八十的老人突然把六个孩子叫到厅堂,八仙桌上的搪瓷杯沿结着圈茶渍。 他坐在太师椅上,后背比去年更驼了些,开口时喉结动了动:“我想再娶。” 子女们起初没吭声,长子茅于越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袖口的补丁——那是母亲生前缝的。 等他说出“权桂云”三个字,次子手里的茶碗“哐当”磕在桌上,水渍漫过木纹。 没人知道权桂云是谁,直到父亲低声补了句“钱塘江大桥那会儿的事,还有个女儿叫玉麟”,长女突然站起来,椅腿蹭着青砖地刺耳。 1967年的人家,“私生女”三个字比阶级成分更让人抬不起头,子女们盯着父亲花白的头发,突然觉得那个造桥的英雄陌生得像块石头。 可谁又能替一个八旬老人说句话?妻子走了,屋里的灯总暗着一半,冷被窝捂到天亮也暖不热。 戴传蕙跟他过了五十年,从江南水乡陪到北京老宅,临终前还攥着他的手说“孩子们要好好的”。 现在他们觉得母亲的一生像个笑话,那些深夜缝补的灯影、病中熬的汤药,原来都藏着另一个女人的影子。 六个孩子没吵没闹,只是依次起身,长子走到门口时停了停,没回头,说了句“您保重”,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脚步声消失在胡同拐角,茅以升看着空荡荡的厅堂,八仙桌上的茶还冒着热气,只是再也没人喝了。 他还是把权桂云和茅玉麟接进了门,老宅西厢房多了张书桌,玉麟每天给父亲读报。 邻居路过总探头,佣人扫地时故意把簸箕弄得很响,权桂云买菜都绕着胡同口的老槐树走——那儿常聚着说闲话的老街坊。 茅以升写过三十多封信,信封上的地址换了又换,从北京寄到上海,再转到瑞士,最后都堆在抽屉底层,贴着“退回”的红戳。 1972年他去瑞士开会,特意绕到茅于越公寓楼下,雪下了两个小时,楼道灯亮了又灭,始终没人下来。 后来他得了老年痴呆,坐在轮椅上总朝门口望,嘴里念叨“孩子们该放学了”。 玉麟把全家福摆在他面前,他指着戴传蕙的影像笑,再翻到子女那页,手就抖起来,像被烫着似的缩回去。 1989年冬天,雪花拍打着病房窗户,93岁的老人咽气时,手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糖——那是年轻时戴传蕙塞给他的,他总说甜。 茅玉麟给北京的六个哥哥姐姐打电话,听筒里只有忙音,或者一句“打错了”,最后一个号码拨过去,传来“此号已注销”的机械女声。 钱塘江大桥的铜像是后来立的,游人摸着“茅以升”三个字拍照,说这是“中国桥梁之父”。 没人知道桥的设计师晚年常对着空屋子说话,说“当年炸桥时心都碎了,现在这心啊,比炸碎的桥墩还散”。 老宅拆迁时,工人从墙缝里掏出一沓信,信纸都黄脆了,开头全是“吾儿见字如面”,结尾总空着半页,像等着谁来补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