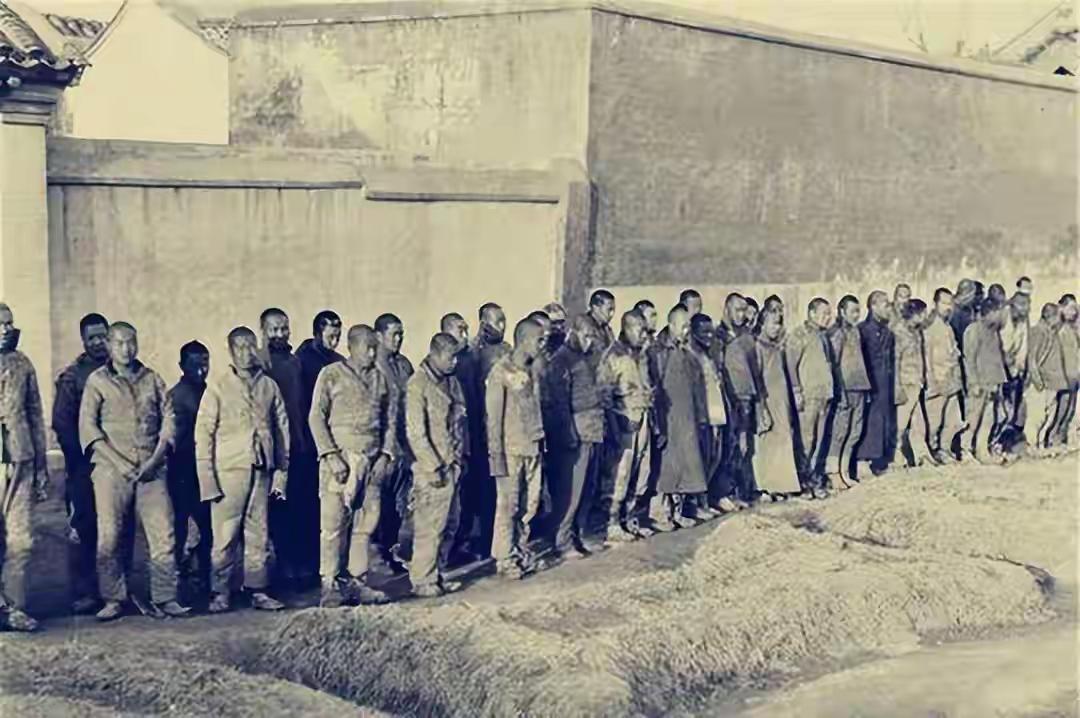七子参军全“阵亡”,58岁母亲哭瞎眼,1949年门外来了熟悉身影 1949年秋天,58岁的邓玉芬坐在破窝棚前,眼睛已经哭瞎了。丈夫没了,七个儿子送出去六个,全死了,她在等什么? 这地方在密云山区穷得很,可邓玉芬一家原本不这么惨。早些年家里有田有房,丈夫任宗武是个勤快人,两口子拉扯着七个儿子,日子虽苦倒也有盼头。鬼子打进来那年,一切都变了。 1933年,日本兵进了密云。邓玉芬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大儿子任永全从外面跑回来,脸都白了:“娘,鬼子见人就杀!”那时候大儿子才十七,最小的老七还在怀里吃奶。邓玉芬和丈夫一商量,带着全家躲进了深山。 1940年,八路军来了。邓玉芬听说这是打鬼子的队伍,二话不说就把大儿子、二儿子送去参军。临出门前,她给儿子们整了整衣裳:“好好打鬼子,娘等你们回来。”两个儿子跪下来磕了头,转身就走了,头都没回。邓玉芬站在门口看了好久,直到人影看不见了,才抹了把眼泪回屋。 第二年,三儿子也去了。邓玉芬心里揪着疼,可嘴上还是那句话:“去吧,多杀几个鬼子。” 仗打得惨啊,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往往都不是好消息。先是丈夫任宗武跟着游击队运粮,被鬼子发现,活活打死了。邓玉芬没哭出声,咬着牙把眼泪咽回肚子里。紧接着,大儿子牺牲的消息来了,二儿子也没了音讯。村里人劝她:“别让老三老四去了,你家总得留个后啊。” 邓玉芬摇摇头:“鬼子还没打完呢。” 老四、老五、老六,一个接一个都送到了部队上。送老六走的时候,邓玉芬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哭得太多了。她摸着小儿子的脸:“六啊,娘可能等不到你回来了,但你得去,咱家不能出孬种。” 老六扑通跪下来:“娘,我肯定回来孝敬您。” 这话说完才三个月,老六就牺牲在战场上。消息是游击队的人送来的,那人站在窝棚外头,半天没敢进门。邓玉芬听见动静,走出来问:“是我家老六吗?”来人点点头,邓玉芬身子晃了晃,扶住门框没倒下。 七个儿子,现在就剩下老七了。老七那年才十五,瘦瘦小小的。邓玉芬把他搂在怀里,整夜整夜不撒手。可老七不干:“娘,哥哥们都去打鬼子了,我也要去。” “不行!”邓玉芬头一回发了狠话,“你再敢说这话,娘死给你看!” 一个月后,老七的阵亡通知书来了。送信的人说,这孩子虚报年龄参了军,第一次上战场就冲在最前面,中弹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枪。 邓玉芬这下真的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哭得眼睛再也看不见光亮。村里人帮她搭了个窝棚,轮流给她送口吃的。她整天就坐在门口,朝着山路的方向,一动不动。 1949年秋天,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了这个小山村。村里敲锣打鼓庆祝,邓玉芬还是坐在窝棚前,好像什么都听不见。 那天下午,脚步声又响起来了。这回不是一阵风,是真真切切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窝棚外头。邓玉芬侧着耳朵,手里的拐棍握紧了。 “娘……”一个颤抖的声音响起来。 邓玉芬浑身一震,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她死了都认得! “娘,是我,老四啊!” 窝棚外头站着个穿着军装的人,三十来岁,脸上有道疤,可眉眼分明就是任家老四任永合。他没死!当年战场上受了重伤,被老乡救下,昏迷了整整一年,伤愈后找不到部队,辗转多年才打听到母亲还活着。 邓玉芬颤巍巍地站起来,伸出双手在空中摸索。任永合扑过来跪在地上,抱住母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腿:“娘,儿子回来了!儿子不孝,让您等了这么久!” 邓玉芬的手摸到儿子的脸,从额头摸到下巴,摸到那道疤,手抖得厉害。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有眼泪从早已失明的眼睛里不停地流。 那天晚上,窝棚里第一次有了火光。邓玉芬坐在炕上,手一直拉着儿子不放开。任永合跟母亲讲这些年的经历,讲他们兄弟几个在战场上的事,讲最后怎么打跑了鬼子,怎么建立了新中国。 “娘,哥哥们没白死。”任永合说,“现在没人敢欺负咱们中国人了。” 邓玉芬点点头,摸索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个小布包,里头是六张泛黄的阵亡通知书,整整齐齐叠在一起。她把布包递给儿子:“收好,这都是你哥哥。” 任永合接过布包,沉甸甸的,像有千斤重。 后来的事村里人都记得,邓玉芬活到1970年,有人说,邓玉芬等的其实不只是儿子,她等的是一个道理,人为什么要牺牲?值不值得?等她终于等回一个儿子,也等来了答案:牺牲从来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是为了让后人不必再牺牲。她的六个儿子躺在了通往新中国的路上,换来了老四能平安回家,换来了千万个母亲不必再送儿子上战场。 这道理太沉重,沉重到一个家庭几乎承受不起。可偏偏就是这样千千万万承受不起的家庭,用他们的破碎,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国家。 窝棚外头的山路上,后来立了块碑,上面没有刻名字,只刻了一行字:“这里住过一位母亲,她叫中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