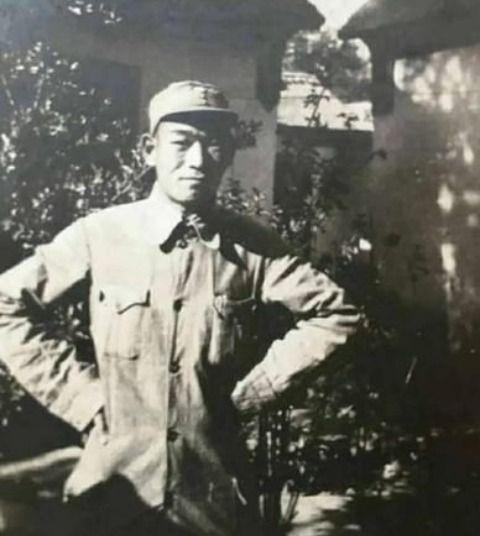"1932年,东北某地的一个居民院落里,日本士兵举起军刀,摆出准备砍杀中国人的架势。站在旁边的小个子鬼子兵,也将长枪的刺刀对准了他。 被刀枪围住的男人叫陈守业,怀里还揣着给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抓的药,粗布药包的边角被指节攥得发皱,草药的苦味混着尘土味往鼻子里钻——那是他昨天走了十几里山路,从镇上唯一没关门的药铺换来的。 院子门槛边,妻子王氏正死死抱着一个鬼子的腿,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哭喊。鬼子抬脚就往她胸口踹去,王氏闷哼一声摔在地上,额角磕到石阶,血珠很快染红了鬓角的碎发,在腊月的冷风中凝成暗红的痂。 举刀的鬼子脸上挂着戏谑的笑,但陈守业没看他。他的眼睛盯着妻子额角的血,想起三天前在镇上看到的景象:鬼子的卡车碾过街边的菜摊,摊主老伯冲上去理论,被一枪托砸倒在地,菜筐里的萝卜滚了一地,沾着泥和血。 “让开!”陈守业突然低吼一声,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小个子鬼子的刺刀往他脖颈又抵近半寸,冰凉的金属压得皮肤生疼。他却想起邻村的张铁匠,就因为不肯给鬼子打造刺刀,被绑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活活烧死,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 里屋传来母亲压抑的咳嗽,一声比一声急,像要把肺咳出来。陈守业的心揪成一团,那药包里的甘草和杏仁,是母亲咳了半个月等来的唯一指望。 举刀的鬼子手腕轻轻晃动,像是在掂量从哪个角度砍下去更“顺手”。陈守业突然挺直了腰杆,原本攥紧的拳头缓缓松开,又猛地攥起,指甲掐进掌心——他不想让母亲最后见到的,是儿子像牲口一样被宰在院里。 他猛地朝举刀的鬼子撞过去,军刀划破肩膀,鲜血瞬间浸透了褂子,温热的血顺着胳膊往下淌。小个子鬼子慌了神,刺刀往前一送,却只划破了陈守业的衣袖。 院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有几句模糊的中文喊话。举刀的鬼子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回头张望。陈守业抓住这个机会,用尽全身力气推开身前的鬼子,转身扑向妻子,将她死死护在身下。 有人说,那个年代的普通人,要么像野草一样被踩死,要么像老鼠一样躲起来。可陈守业不是野草,也不是老鼠。他只是个想守着母亲吃药、看着妻子缝补的庄稼汉,却被侵略者的屠刀,逼成了要用血肉之躯护家的人。 当生存被逼到墙角,普通人的勇气会从骨头缝里渗出来。他们没有军装,没有番号,怀里揣的可能是药,是干粮,是孩子的鞋,却在那一刻成了最硬的铠甲。 那个院子里的血与泪,是1932年东北大地上无数家庭的缩影。没有谁天生是英雄,只是侵略者的铁蹄,把一个个只想安稳度日的普通人,逼成了守护家园的墙。 如今再看那个攥皱的药包,那滴在石阶上的血,突然明白: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糖,是无数陈守业们用脊梁撑住的天。我们现在能安稳地走在阳光下,是因为有人曾在黑暗里,用命护住了那一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