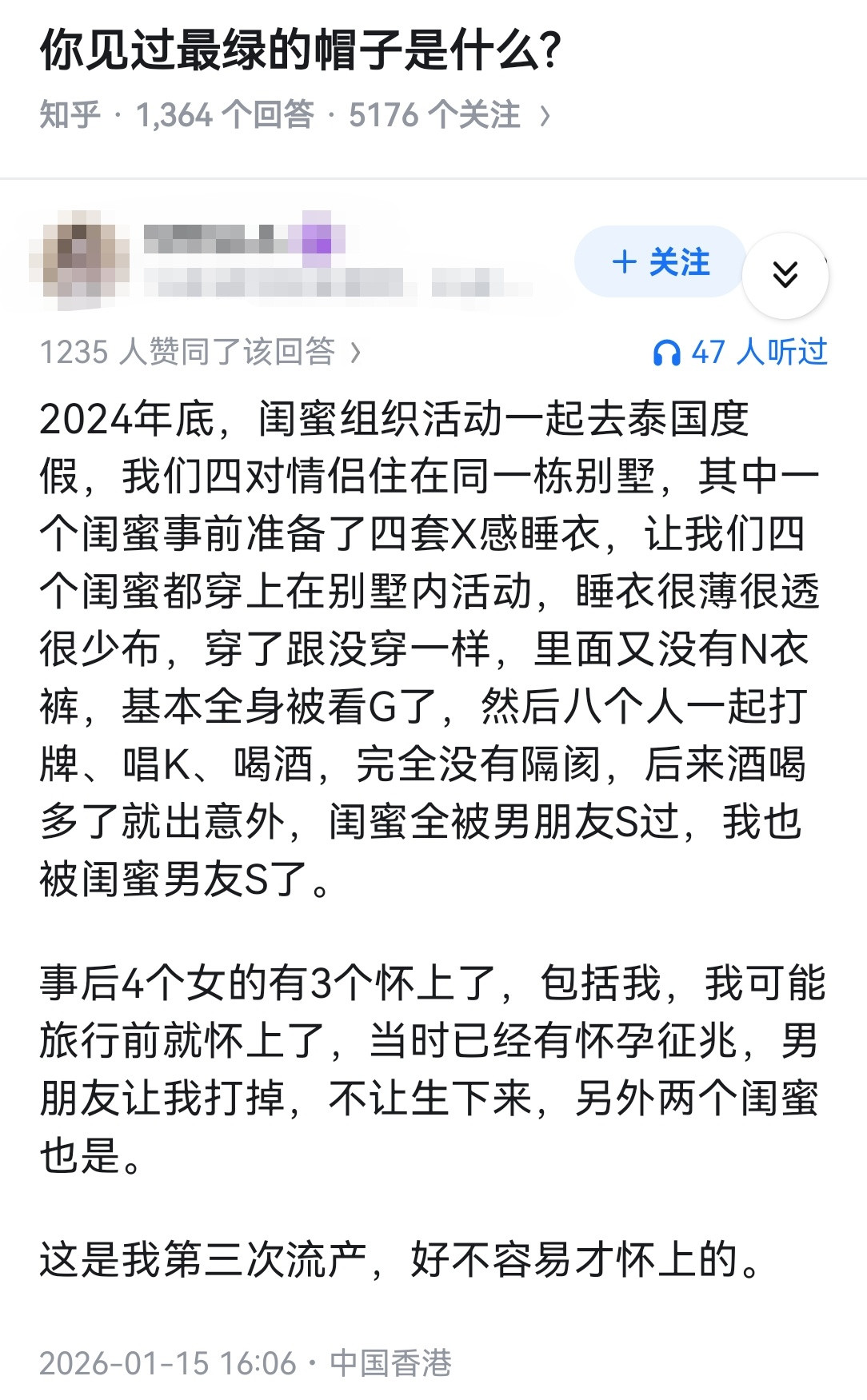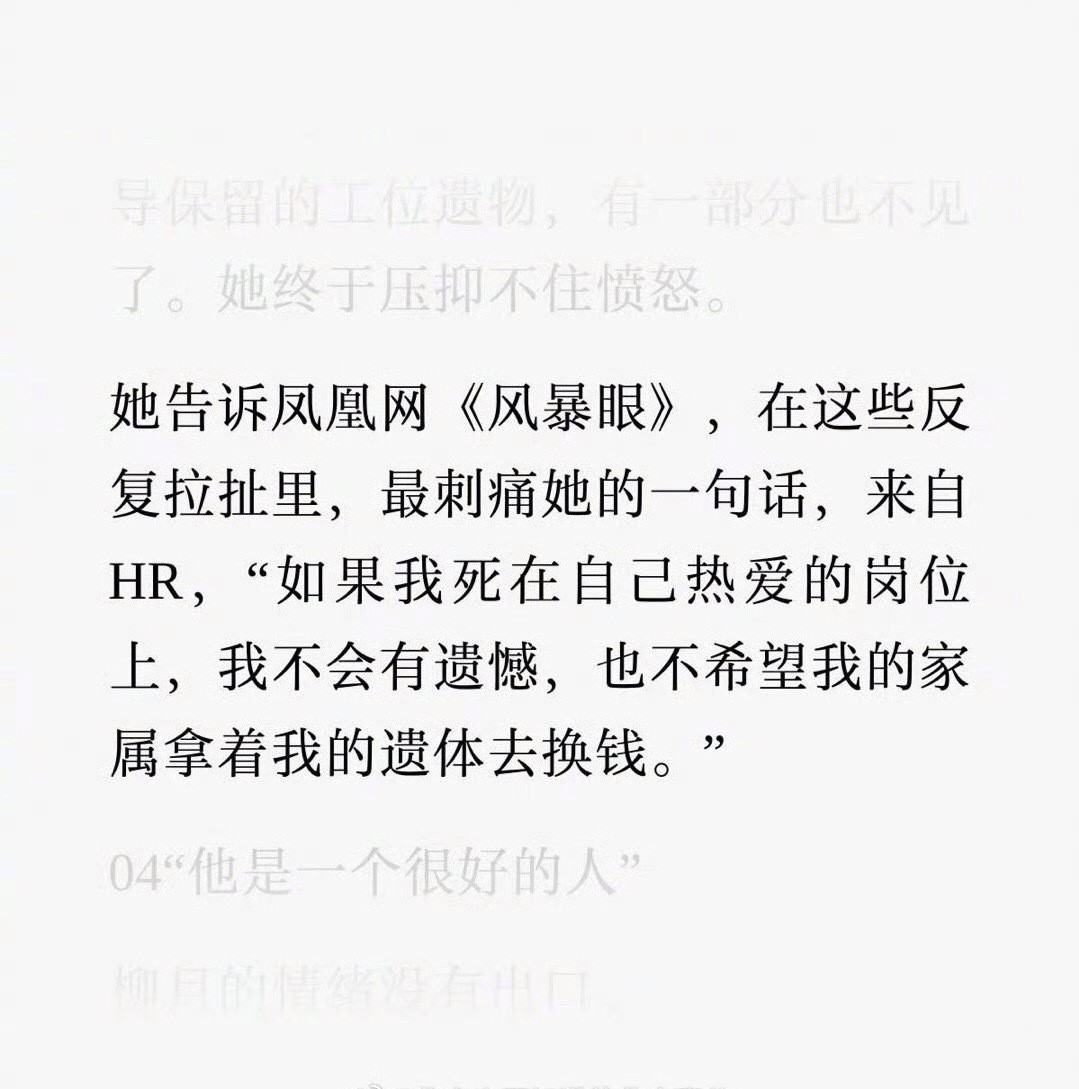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4年,党中央对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来到了若尔盖县,在这里曾生活着很多长征中负伤离队的老红军,后来在县委领导的主持下,政府决定给二十七位老战士颁发荣誉证书,这时负责主持的同志大声说道:“请失散红军上台领证。” 现场忽然有些沉默,没人立刻起身。坐在前排最中间的李茂盛犹豫了一下,慢慢站起来,拄着那根用了几十年的木杖,脚步有点踉跄。李茂盛1935年随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在毛尔盖沼泽地段受伤掉队,被藏族阿珠家族救下。 他昏迷了三天三夜,靠酥油茶吊着命。等伤好些后,他留在班佑村放牧、种青稞,藏语说得比汉话还溜,后来还娶了阿珠家的幺女。 台上那声“失散红军”像颗石子投进他心里。四十九年了,整整四十九个春秋。那年他十九岁,江西兴国县的放牛娃跟着队伍走,过草地时左腿被流弹打穿。醒来躺在黑帐篷里,牦牛粪火塘噼啪作响,藏族老阿妈正用木勺给他喂酥油茶。伤养了三个月,能下地了,部队早不知走到哪里。阿珠家老爷子拍他肩膀:“留下吧,红军娃娃,草原也是家。” 真就留下了。学挤牦牛奶,学打酥油,学在冻土上种青稞。老阿妈把最厚的藏袍给他披上,阿珠家的小女儿卓玛教他唱牧歌。1938年草原最美的季节,他和卓玛在喇嘛主持下成了亲。婚礼那天,他把珍藏的八角帽小心收进木箱,压在箱底最深处。偶尔半夜醒来,摸着那褪色的红布,耳朵里仿佛还能听见湘江边的冲锋号。 可心里那根刺始终没拔出来。掉队——这两个字像烙印烫在灵魂上。有几年他常做同一个梦:战友们在雪山上朝他招手,他想追,受伤的腿却陷在泥沼里。醒来满脸是泪,卓玛不说话,只是把他长满老茧的手握在自己掌心。草原上的风刮了又停,格桑花开了一季又一季。他有了三个孩子,个个都会用藏语唱《北京的金山上》。只是教他们唱“毛主席的光辉”时,声音总忍不住发颤。 这些年不是没打听过。1951年解放军进阿坝,他跑去问有没有红一方面军的老战友。那个小战士翻遍名册,摇摇头。1959年民主改革,工作队的汉族干部听说他的经历,握着他的手直喊“老革命”。可当对方说要给他“落实身份”时,他却摆摆手:“我就是个放牧的,挺好。”怕什么?怕那顶“逃兵”的帽子,怕给救他的藏族家人惹麻烦,最怕的是——自己真配不上“红军”这两个字。 所以1984年春天,县里通知他去开会,他蹲在帐篷外抽了一下午旱烟。卓玛把最体面的藏袍拿出来:“该去的,你本来就是红军。”女儿央金梳着他的白发:“阿爸,你梦里常喊‘指导员等我’。” 会场里坐着二十多个老人。有的缺胳膊,有的瞎了眼,个个脸上刻着草原的风霜。主持的同志念名单,念到“李茂盛”时顿了顿:“原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战士。”他身子一震,木杖“咚”地戳在地上。四周好安静,静得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去不去?去就意味着承认,承认这四十九年的等待,承认每个深夜的煎熬,承认自己虽然掉队但从未背叛。 他站起来了。一步一步,走得特别慢。那条受伤的左腿一瘸一拐,就像当年在草地上拖着走的样子。走到台中央,县委书记双手递来红色证书。他伸出那双又黑又糙的手,手抖得厉害,几乎捧不住那薄薄的本子。翻开,白纸黑字写着:“李茂盛同志,系失散红军,现予以确认。” 眼泪突然就滚下来了,砸在证书上啪啪响。这个在草原上冻掉脚趾没哭过,挨饿时啃皮带没哭过,看着三个孩子饿得哇哇叫没哭过的老人,此刻哭得像个孩子。台下不知谁开始鼓掌,掌声越来越响,像当年过金沙江时的浪涛。其他老人也陆续站起来,一个个走向主席台。有个独臂老人用剩下那只手敬军礼,姿势标准得让人心碎。 那天傍晚,李茂盛抱着证书坐在山坡上。夕阳把草原染成金红色,就像记忆里井冈山的杜鹃。卓玛轻轻坐到他身边,他用生硬的汉语说:“明天,我想去给孩子们讲讲,讲讲湘江,讲讲雪山。”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讲讲那些没走出来的战友。” 晚风拂过草原,经幡哗啦啦地响。远处传来牧歌,是他教给孙儿们的那首:“红旗飘呀飘,红星闪闪亮……” 证书静静地躺在老人膝上。四十九年的重量,终于找到了安放的地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