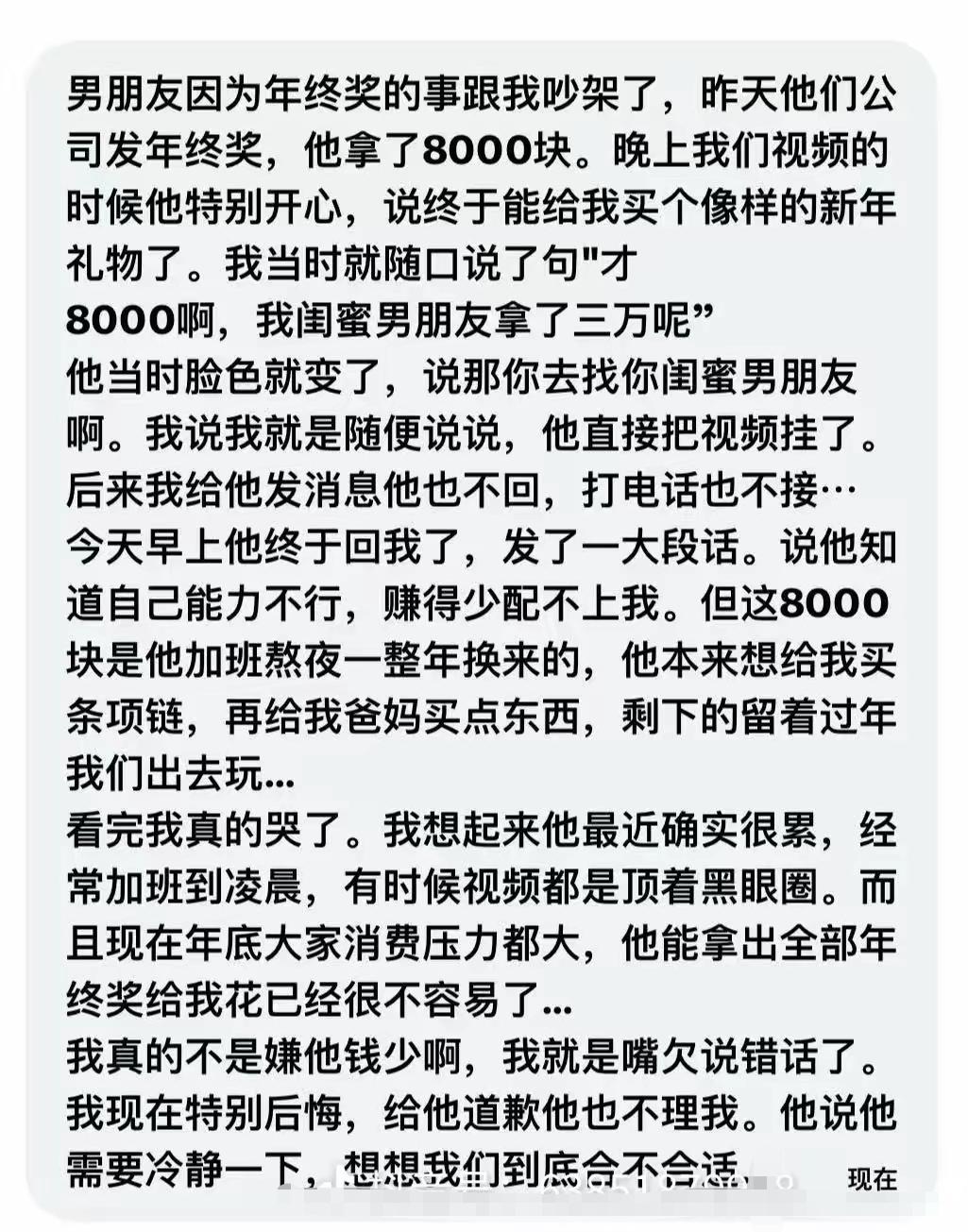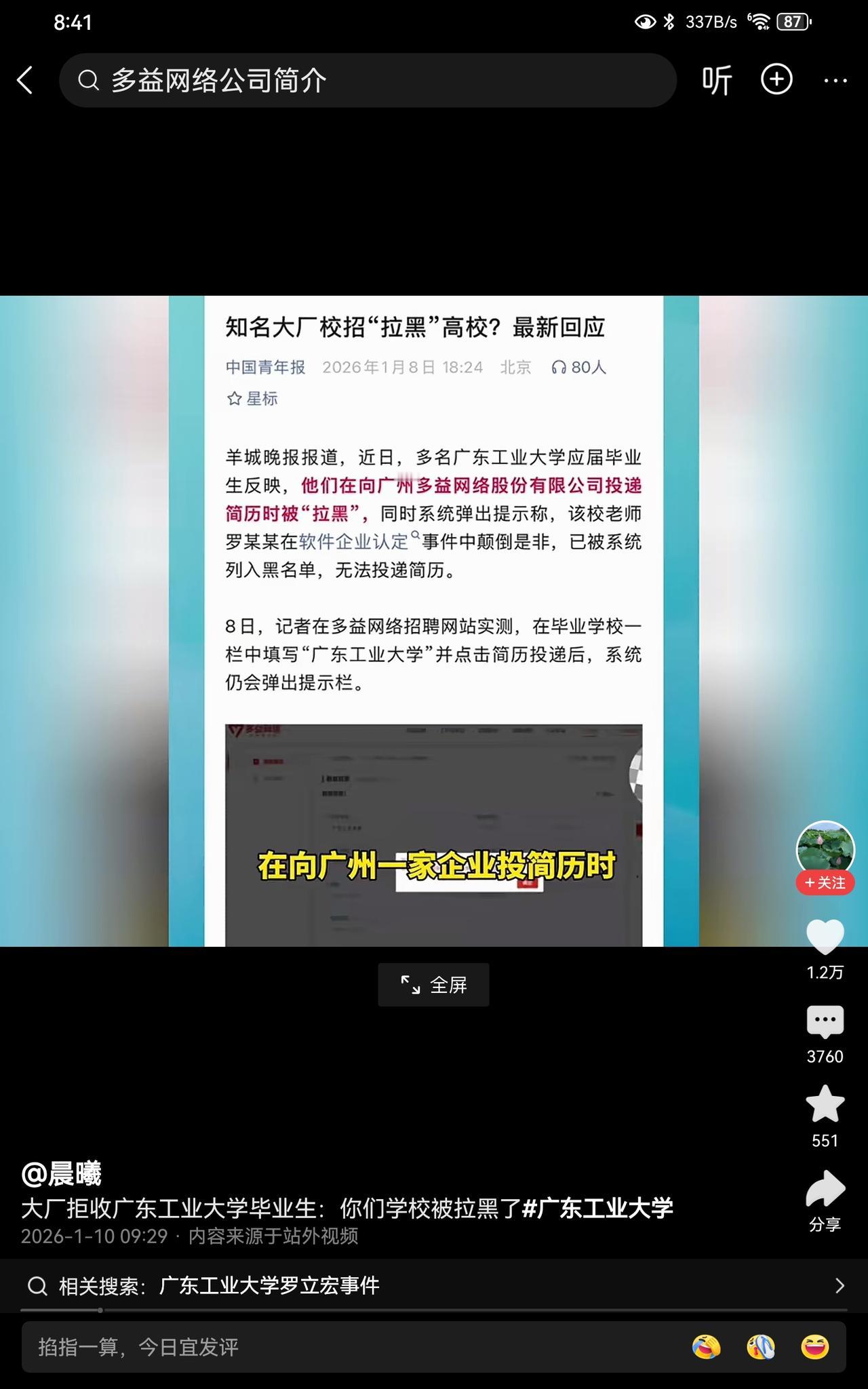《大宅门》二奶奶去世,出殡时,黄春病得走不动,白玉芬提出不要让她去送葬,白景琦却嚷道:“她是二房长媳,不去像话吗?” 白景琦的意思,又不用她走路,可以坐轿,人一定要去。 但当时大热的天,黄春躺在屋里都喘不上气,更何况是在轿子里。 但白景琦不听,只一个劲地嚷:“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还有没有孝心了?” 黄春是白景琦的原配妻子,也是白家二房的长媳。她性格温顺,做事周到,从进白家起就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大家族的体面。二奶奶在世时,她几乎是“完美儿媳”的样板,对上孝顺,对下宽和,对妯娌、姑嫂也尽量周全。正因为这样,白景琦心里默认,二奶奶的葬礼上,黄春必须在场,才算对得起这份情分。 问题在于,黄春那时的身体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多年操劳加上旧病缠身,她几乎常年被药罐子陪着。大热天里,她躺在屋里都要靠人不断打扇、喂药,才能勉强维持呼吸。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硬要她出门,本身就是一种折磨。白玉芬作为大姑姐,最清楚黄春的身体情况,所以才提出“别去送葬”,出发点是心疼弟妹,而不是跟谁赌气。 白景琦却不这么看。在他的价值排序里,家族礼仪、脸面、孝心,永远排在个人感受前面。他觉得黄春是二房长媳,二奶奶又是白家真正的“主心骨”,长媳不出现在出殡队伍里,就是“不像话”。他并不否认黄春病得厉害,只是坚持“坐轿去,不用走”,在他看来,这已经是给足了体谅。这种逻辑,本质上是把黄春当作家族结构中的一个“位置”,而不是一个有极限、有痛苦的活人。 这一幕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传统大家族里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一种是以白景琦为代表的“家族本位”,强调规矩、名分、体面;另一种是以白玉芬为代表的“人情本位”,更看重亲人的身体和感受。白景琦并非冷血,他对二奶奶有深厚感情,对黄春也并非没有心疼,只是在“孝心”和“规矩”面前,他习惯牺牲的是个体的舒适度,甚至是健康。 从人物性格看,白景琦的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逻辑。他从小被二奶奶宠大,又被教养成“有担当、有血性”的白家传人,对家族荣誉有着近乎偏执的维护。他敢闯、敢拼、敢和整个世道对着干,但在家族内部,他又是传统伦理最坚定的执行者。他可以为了生意跟洋人硬刚,却不会为了妻子的身体去“破例”。这种矛盾,让他既显得有骨气,又显得有些冷酷。 黄春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她始终处在这种价值冲突的夹缝中。她明知道自己撑不住,却也明白白景琦那句话的分量:“还有没有孝心了?”在那个环境里,“不孝”是一顶能压垮人的帽子。她若坚持不去,很可能被说成“不懂事”“不给老太太面子”,甚至被贴上“不贤惠”的标签。为了不给丈夫难堪,也为了保住自己在家族中的位置,她最终还是选择了顺从。 从故事走向看,黄春在送葬途中病情急剧恶化,最终没能熬过去。她的死,表面上是旧病复发、劳累过度,深层原因却是长期被家族角色绑架的结果。她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做孝顺儿媳,做贤惠妻子,做温柔母亲,唯独很少有人真正问过她累不累、痛不痛。她的死,是整个大宅门对女性的某种“制度性忽视”的集中爆发。 白景琦在黄春死后,悲痛欲绝,但他的悲痛更多停留在“失去亲人”的层面,很少真正反思自己的行为。他可能会后悔那天逼得太紧,却未必会否定“长媳必须送葬”的原则。这正是传统家长式男性的典型局限:他们重情,却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去“安排”别人的命运,很少真正把女性当作平等的个体来尊重。 从剧作角度看,这场戏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制造了一个“坏人”,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家庭结构:在“孝心”“规矩”“体面”这些看似正当的名义下,无数个体的痛苦被合理化,甚至被要求“自愿承受”。黄春不是被某一个人害死的,而是被一整套话语和结构慢慢耗尽的。 这段情节也提醒观众,传统伦理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它里面也有残酷的一面。所谓“孝道”“长媳”“名分”,如果不与对人的尊重结合起来,很容易变成一种压迫工具。白景琦的爱,是真的;他的心疼,也是真的,但他的观念,让他最终亲手把黄春推向了绝路。 从更大的社会背景看,《大宅门》写的虽是清末民初的家族故事,反映的却是一个延续很久的问题:在以父权和家族为中心的结构里,女性往往被要求为“整体”牺牲“个体”。她们被赞美为“贤惠”“懂事”“识大体”,却很少有人问一句:“你自己想要什么?”黄春的死,是对这种结构最沉痛的控诉之一。 黄春的故事,放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很多家庭里,类似的逻辑仍在以不同形式上演:打着“为你好”“为了这个家”的旗号,要求某一个人牺牲健康、时间、尊严。我们在感叹黄春命苦的同时,也不妨多问一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是不是也在用“规矩”和“面子”,压着某个最亲近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