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徐悲鸿被迫娶村姑为妻。 急信从宜兴老家送到上海时,徐悲鸿正对着石膏像画素描。 信封上母亲的字迹歪歪扭扭,只有一句话:“父病危,速归。”他攥着信纸往码头跑,心里清楚,父亲这病拖了半年,怕是等不及他这个独子尽孝了。 回到家时,堂屋里已经摆上了香案。 叔叔把他拉到一边,说村里老人都看过了,要想救徐达章,得靠“冲喜”。 徐悲鸿盯着父亲蜡黄的脸,想说这都是迷信,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沉默。 他读过新学堂,知道生老病死自有规律,但看着母亲哭红的眼睛,终究还是点了头。 新娘是邻村的蒋家姑娘,那天她穿着红袄,头埋得很低。 徐悲鸿后来才知道她叫蒋棠珍,根本不是什么村姑,父亲是宜兴有名的富商。 婚礼办得仓促,唢呐声里,他听见有人议论“徐家小子捡了便宜”,心里像塞了团乱麻。 新婚夜他坐在床沿没动。 蒋棠珍先开了口,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知道你不情愿。”徐悲鸿猛地抬头,看见她眼里的光,突然觉得有些愧疚。 “为了我父亲,”他低声说,“委屈你了。” 说也奇怪,婚后第三天,徐达章居然能坐起来喝粥了。 母亲拉着蒋棠珍的手直夸“福星”,徐悲鸿却偷偷找了西医。 医生说病人是心病,家里热闹了,精神头自然好起来。 这个答案让他更难受,好像这场婚姻从根上就是个骗局。 回到上海的画室,徐悲鸿把自己埋进画布。 他给蒋棠珍写过一封信,本来想说说巴黎的画展,写了又撕,最后只寄了些钱。 直到收到那封加急电报,他盯着“妻孕”两个字,半天没缓过神。 “把孩子打掉。”他在回信里写得干脆。 没过多久,母亲寄来一张照片,蒋棠珍抱着个婴儿,照片背面是三个字:“劫生”。 徐悲鸿把照片塞进抽屉最底层,再没打开过。 后来听老家说,那孩子一岁多就没了,蒋棠珍抱着空襁褓坐了三天三夜。 1927年签离婚协议时,蒋棠珍没要额外的赡养费,只带走了那本写满批注的《悲鸿画集》。 徐悲鸿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起新婚夜她那句“我知道你不情愿”。 他后来在法国遇到过很多红颜知己,却再没听过那样平静又带着委屈的声音。 去年在宜兴档案馆查资料,看到蒋碧薇(她后来改的名字)的回忆录手稿。 其中一页写着:“劫生若在,该会画父亲那样的马吧。”墨迹晕开了一小块,像滴在纸上的泪。 那个被当作“冲喜”工具的婚姻,最终用一个孩子的名字,刻下了两败俱伤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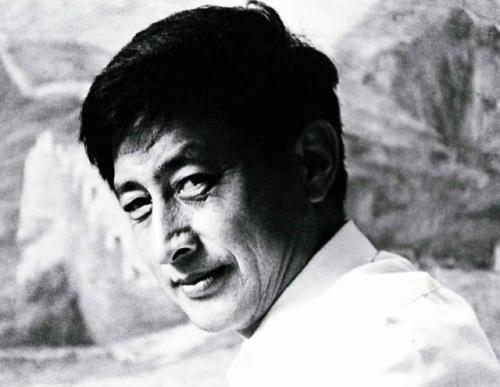







![真的要被魏桥的领导和团队暖到湿了眼睛[哭哭]超有温度的一支队伍!颁奖结束后尹老](http://image.uczzd.cn/9659559788906336046.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