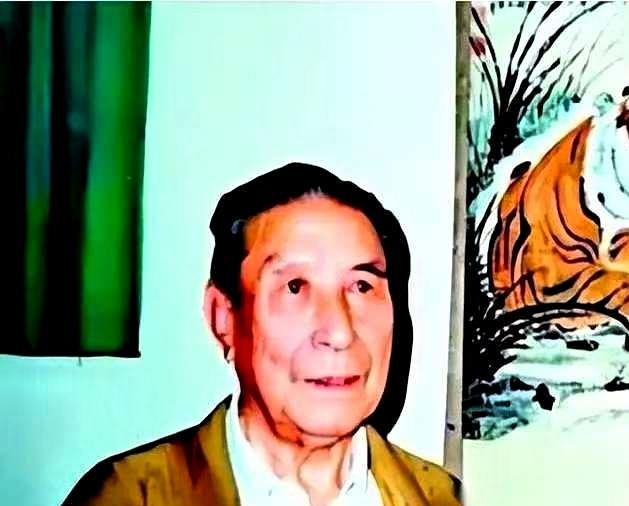抗战中,八路军王金英因为肺病严重,被悄悄地送到老乡家中休养,不料邻居跑去告密,日军当即派出重兵。等王金英发觉,日军已经包围了院子,情况十分紧急。 1941年的鲁南,麦子刚抽穗,夜里的风还带着凉意。王金英蜷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咳嗽声像破风箱似的停不下来。她把八路军军服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枕下,身上盖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被——这是房东张大娘特意给她晒过的,带着点阳光和麦秸的味道。 三天前,她被两名战士背到六天务村。部队要转移打游击,她的肺病拖得整个人只剩一把骨头,团长红着眼圈说:“金英,先养好身子,队伍还等着你归队。”她知道这是托词,当时的医疗条件,拖着这样的病,能不能活到队伍回来都说不准。 张大娘守在炕边,给她端来熬得稠稠的小米粥:“闺女,趁热喝,发点汗就舒坦了。”王金英刚要接碗,院墙外突然传来狗吠,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像雨点砸在院子的石板地上。 “不好!”张大娘的儿子二柱从门缝往外看,脸瞬间白了,“是鬼子!还有伪军!” 王金英的心猛地一沉。她挣扎着想爬起来找枪,可刚直起身子就一阵头晕,咳嗽得更凶了。张大娘赶紧按住她:“别动!我去应付!”话音未落,院门上的木栓“哐当”被踹断,十几个端着枪的日伪军涌了进来,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冷光。 “女八路在哪?”翻译官尖着嗓子喊,眼睛在屋里扫来扫去。王金英躲在门后,手紧紧攥着炕席的边缘,指甲几乎嵌进木头里。 就在这时,西厢房的门“吱呀”开了。一个穿着黑布褂子的汉子走出来,手里把玩着两颗铁核桃,正是刚在这隐蔽养伤的连长刘锡琨。他前几天带小队伏击鬼子运输队,腿被流弹擦伤,正好和王金英前后脚藏进张家。 “找八路?”刘锡琨的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子寒气,“我就是。” 日伪军都愣住了。领头的小队长翻出告密者提供的画像,上面明明是个瘦弱的女同志,怎么冒出个虎背熊腰的汉子?他扭头看向缩在后面的告密者——正是村东头的懒汉李四,前两天偷摸去炮楼领赏,说看到个病恹恹的女八路藏在张家。 “八嘎!”小队长扬手就给了李四一巴掌,打得他嘴角淌血,“你的情报,大大的错误!” 李四捂着脸哆嗦:“太君……我、我真看见个女的……” “啪啪!”两声枪响打断了他的话。刘锡琨不知何时摸出了藏在炕洞里的匣子枪,子弹擦着小队长的耳朵飞过,钉在院门上,溅起一串木屑。“想抓八路?先问问我手里的枪!” 日伪军慌了神,举枪就射。刘锡琨拽着王金英往八仙桌底下躲,子弹“嗖嗖”地穿透窗户纸,在墙上打出道道弹痕。张大娘和二柱早从后窗翻出去报信了——村里藏着十几个伤员,这动静准能惊动他们。 “你带着病,别乱动!”刘锡琨把王金英护在身后,匣子枪“砰砰”响个不停,每一枪都撂倒一个敌人。王金英看着他腿上的绷带渗出血来,咬着牙摸到墙角的柴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拖累他。 院墙外突然传来喊杀声,是村里的民兵和其他伤员赶来了!他们拿着锄头、扁担,甚至还有几杆土造的猎枪,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日伪军腹背受敌,顿时乱了阵脚。 小队长见势不妙,喊着“撤退”就要往外冲。刘锡琨瞅准机会,一枪打中他的手腕,指挥刀“当啷”掉在地上。“想跑?晚了!” 战斗没持续多久。日伪军被打得屁滚尿流,丢下几具尸体和枪,狼狈地逃回了炮楼。李四想趁乱溜走,被二柱一扁担打翻在地,捆了个结实。 月光重新照进院子,刘锡琨扶着墙喘粗气,腿上的血把黑布褂子浸得发黑。王金英挣扎着爬起来,掏出自己带的急救包给他包扎,手指触到他伤口时,忍不住打颤。 “哭啥?”刘锡琨咧嘴笑,露出两排白牙,“这点伤算啥?当年在平型关,比这凶险十倍的仗都打过。”他看了眼王金英苍白的脸,“倒是你,得赶紧转移,这村子不能待了。” 王金英点点头,眼泪却掉了下来。她想起自己当年放弃优渥的生活参加八路军,家人都说她疯了,可此刻看着眼前的热血和生死相托的信任,突然觉得一切都值了——这世上,总有些东西,比安稳日子更重要。 后来,王金英跟着大部队转移到了后方,肺病渐渐好转。她总跟战友说起六天务村的那个夜晚,说起刘锡琨挡在她身前的背影,说那时候她就知道,这场仗,他们一定能赢。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像刘锡琨、像张大娘这样的人,用热血和骨气,筑起了比炮楼更坚固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