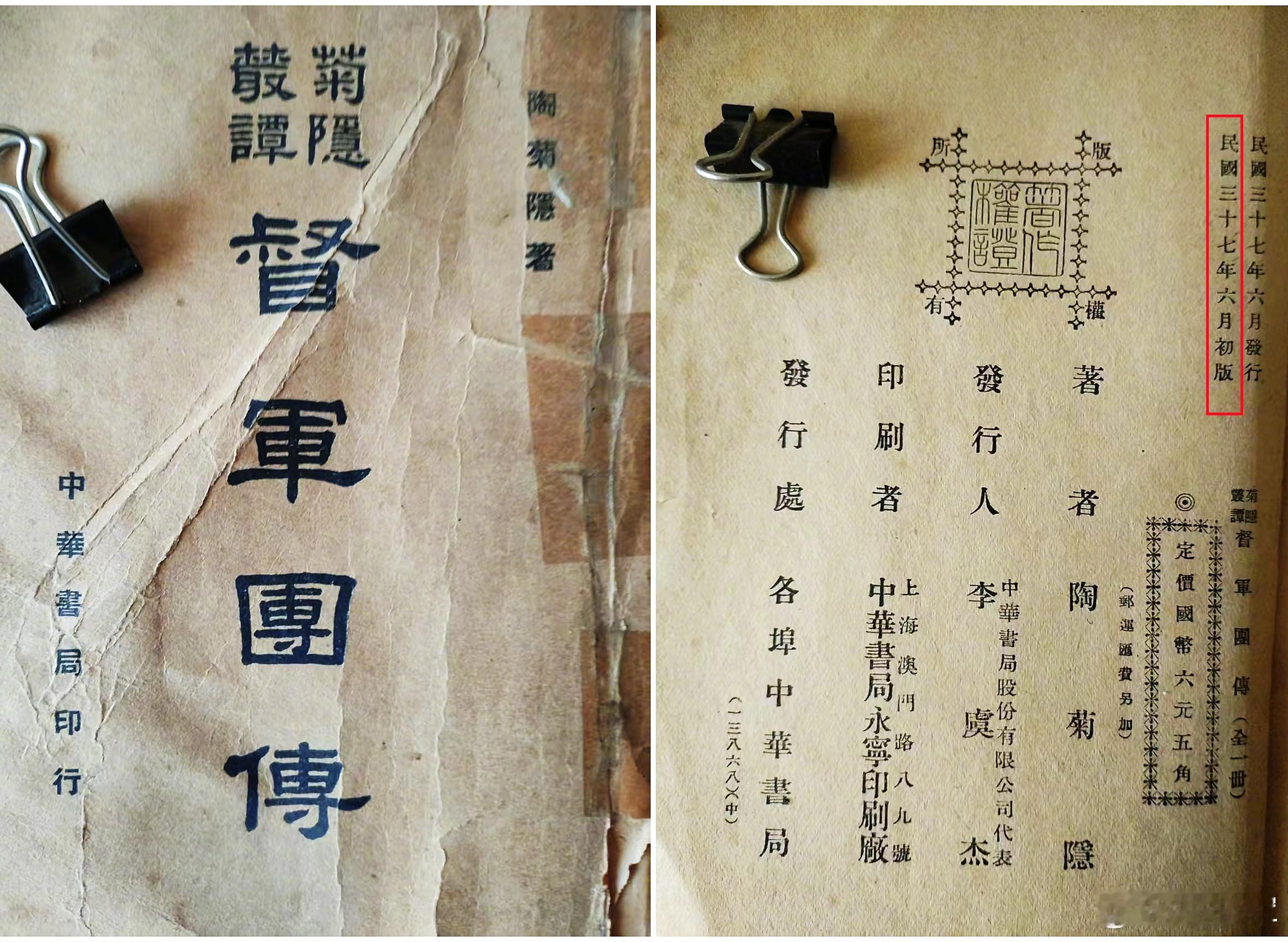1964年至1967年三年间,三名曾氏与俞氏家族成员相继去世,而中国却失去了三位顶级人才。 1966年8月的北京,北大燕南园的紫藤萝还没谢,英语教授俞大絪把自己反锁在书房。 三天后,人们在书桌上发现半杯没喝完的茶水,和摊开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 这位60岁的学者,曾带着牛津大学文艺复兴文学硕士的学识回到刚诞生的新中国,主编的《英语》教材让百万学子第一次触摸到标准的伦敦音。 可此刻,书里夹着的全家福照片被红笔打了叉,照片上站在她身边的丈夫曾昭抡,正远在武汉的“牛棚”里扫厕所。 曾昭抡的人生轨迹曾比他的化学实验更精准。 27岁拿下麻省理工博士学位时,导师断言他能拿诺贝尔奖。 这位中央研究院最年轻的院士,抗战时在西南联大用土陶管做实验,硬是建起中国第一个有机氟化学实验室。 1949年在香港,国民党派专机接他去台湾主持核计划,他却把机票塞进壁炉,转头对俞大絪说“科学家的实验室应该在祖国的土地上。”只是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十年后会被自己亲手培养的学生指着鼻子骂“反动学术权威”。 南京博物院的石阶上,曾昭燏最后一次整理考古笔记是在1964年12月。 这位55岁的女院长踩着碎雪走到大殿前,手里攥着南唐二陵发掘报告的手稿。 1950年她带着团队用洛阳铲唤醒沉睡千年的南唐后主陵寝时,郭沫若曾握着她沾满泥土的手说“你让五代史有了温度。”可现在,展厅里她修复的青瓷瓶被贴上“四旧”标签,那些标注着“龙纹演变考”的笔记,成了“资产阶级治学”的罪证。 她给远在北京的堂兄曾昭抡写了最后一封信,信封上没贴邮票,只用铅笔写着“烦交”。 曾国藩的血脉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成了沉重的枷锁。 俞大絪的母亲是曾国藩孙女,曾昭抡是曾国潢的曾孙,曾昭燏的父亲官至晚清两江总督。 这种显赫家世在1960年代成了“原罪”,俞大絪的兄长俞大维在台湾任“国防部长”的消息传来,红卫兵闯进她家时,把牛津大学的博士证书撕成了碎片。 曾昭燏在批斗会上被按着头下跪,有人举着她穿旗袍考察遗址的照片质问“考古队是让你当大小姐的?” 曾家兄妹最后一次见面是1962年的春节。 曾昭燏从南京带来一包雨花石,曾昭抡把麻省理工的博士戒指偷偷塞给她“戴着防身。”俞大絪在厨房煮了锅腊肉,三个人围着煤炉没说几句话,窗外就传来邻居的咳嗽声。 后来这包雨花石被抄家时搜走,展览在“阶级教育馆”,标签写着“剥削阶级的玩物”。 曾昭抡1967年肺癌晚期躺在病床上,弥留之际还在念叨“把我那本《元素有机化学》找出来,第三章还有个公式没验算。” 俞大絪批注的《莎士比亚全集》现在还放在北大图书馆的特藏部,书眉上的铅笔字迹已经褪色,第37页《哈姆雷特》的台词旁写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南京博物院的仓库里,曾昭燏手绘的南唐二陵平面图边角微微卷起,标注着“待考”的符号旁边,有滴风干的水渍。 这些未完成的批注和标注,或许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留给这个时代最安静的回答。 去年冬天我去南京博物院,讲解员指着展柜里的青瓷瓶说这是“南唐文物”,却没人提起那个在雪地里整理发掘报告的女学者。 倒是在北大英语系的走廊里,老教授们还会说起俞大絪上课的样子“她讲莎士比亚时,眼睛亮得像有星星。”这些散落的记忆碎片拼起来,才看清那些年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三个名字,更是一个民族本该拥有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