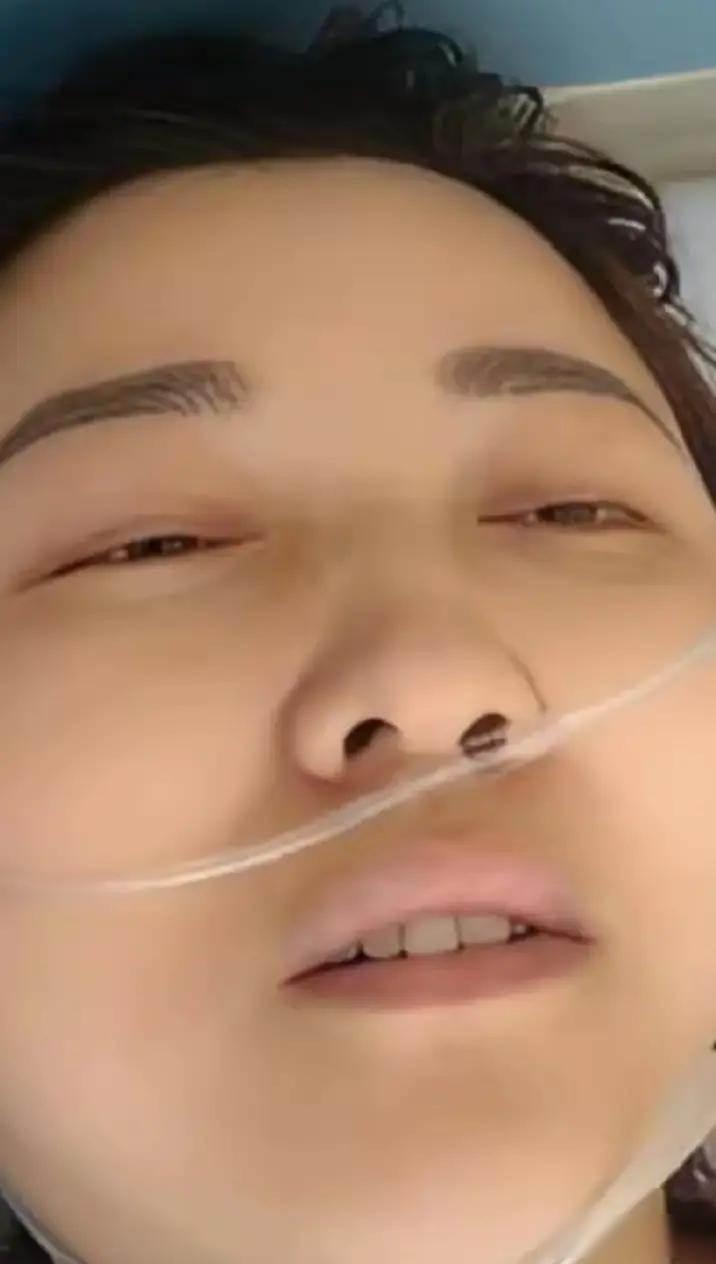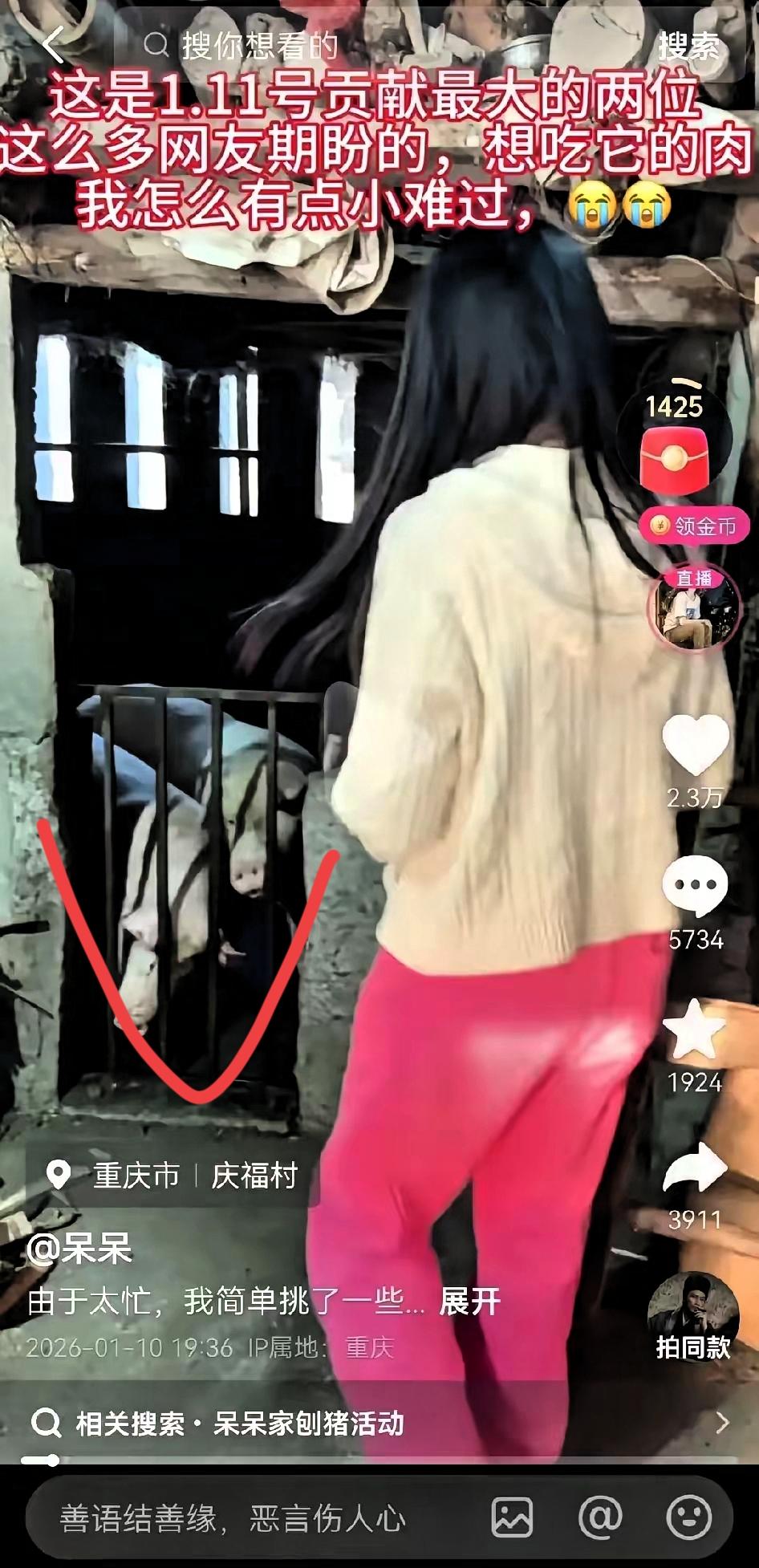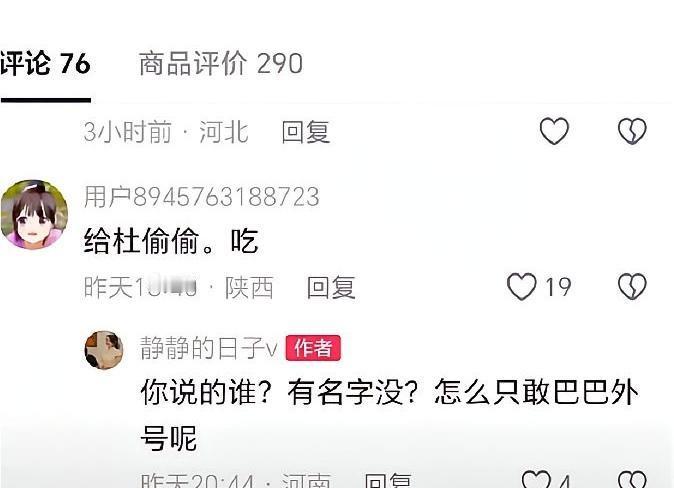今天接到一个蒙古国号码我挂断了次但他一直打我只能接了 电话接通后,听筒里传来一阵嘈杂的背景音,夹杂着模糊的蒙古语对话,还有人咳嗽的声音。过了几秒,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男声响起:“你好,请问是林晓吗?” 我愣了一下,报出自己的名字,问对方是谁。他顿了顿,说:“我是乌兰巴托中央医院的护士,这里有位病人叫陈卫国,他昏迷前一直攥着这个号码,说一定要联系你。” 陈卫国。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不是我舅,还能是谁?五年了,音信全无,家里都当他……唉。 我手有点抖,问人怎么样了。护士说,脑出血,刚抢救过来,还没醒,身边就一个破本子,写着这号码。挂了电话,我靠着墙站了好一会儿,窗外正好有辆大货车轰隆隆开过去,震得玻璃嗡嗡响。定了定神,我才给我妈拨过去。电话那头,听完就只剩压抑的抽泣声,然后她说:“去,快去把他接回来。” 哪有那么容易。我翻着航班信息,最早一班飞乌兰巴托也得明天清早。夜里收拾行李,捡了两件厚衣服,塞了点常备药,心里乱得像团麻。灯也没关,我就坐在沙发上发呆,空调外机呜呜响,吵得人心烦。 到了地方,我才知道什么叫抓瞎。满街的西里尔字母,说话听不懂,羊肉味儿直往鼻子里钻。找到医院,看见我舅躺在监护室里,身上插着管子,头发白了一大片,瘦得脱了形。我隔着玻璃看他,忽然想起他走那年,给我买了支冰淇淋,化得满手都是,他一边笑我一边拿手帕给我擦。那手帕好像还是格子的。 护士其其格人挺好,帮我跑手续,说医疗费不急。我就在医院旁边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每天过去守着。有时给他擦擦手,有时就干坐着。第四天下午,阳光斜斜地照进病房,灰尘在光柱里打转。我正看着那灰尘出神,忽然听见一声很轻的、沙哑的:“……晓啊。” 我腾地站起来,凑过去。他眼睛睁开一条缝,看着我,看了好久,好像认不出,又好像全认出来了。他嘴动了动,没说出话,眼泪顺着眼角皱纹流进鬓角里。我赶紧按铃,手按下去的时候,发现自己也在哆嗦。 后来他慢慢能说话了,断断续续的,说生意赔了,没脸回来,就在这儿凑合活着。说最想喝我妈熬的小米粥,稠稠的,上面一层米油。我说,回去就让她熬,熬一大锅。 半个月后,我们上了回国的飞机。起飞时,他一直盯着窗外下面那片越来越远的、黄绿交织的土地,直到云层盖住一切。他收回目光,拉了拉盖在腿上的毯子,轻声说:“这回,可真是不走了。” 家就是这样吧,有时候你以为线断了,其实它只是绕远了。兜兜转转,那头总有人攥着,等你回来。
浙江某医院走廊里,男人的嘶吼像炸雷——“谁拦我救儿子,我跟谁拼命!”话音
【14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