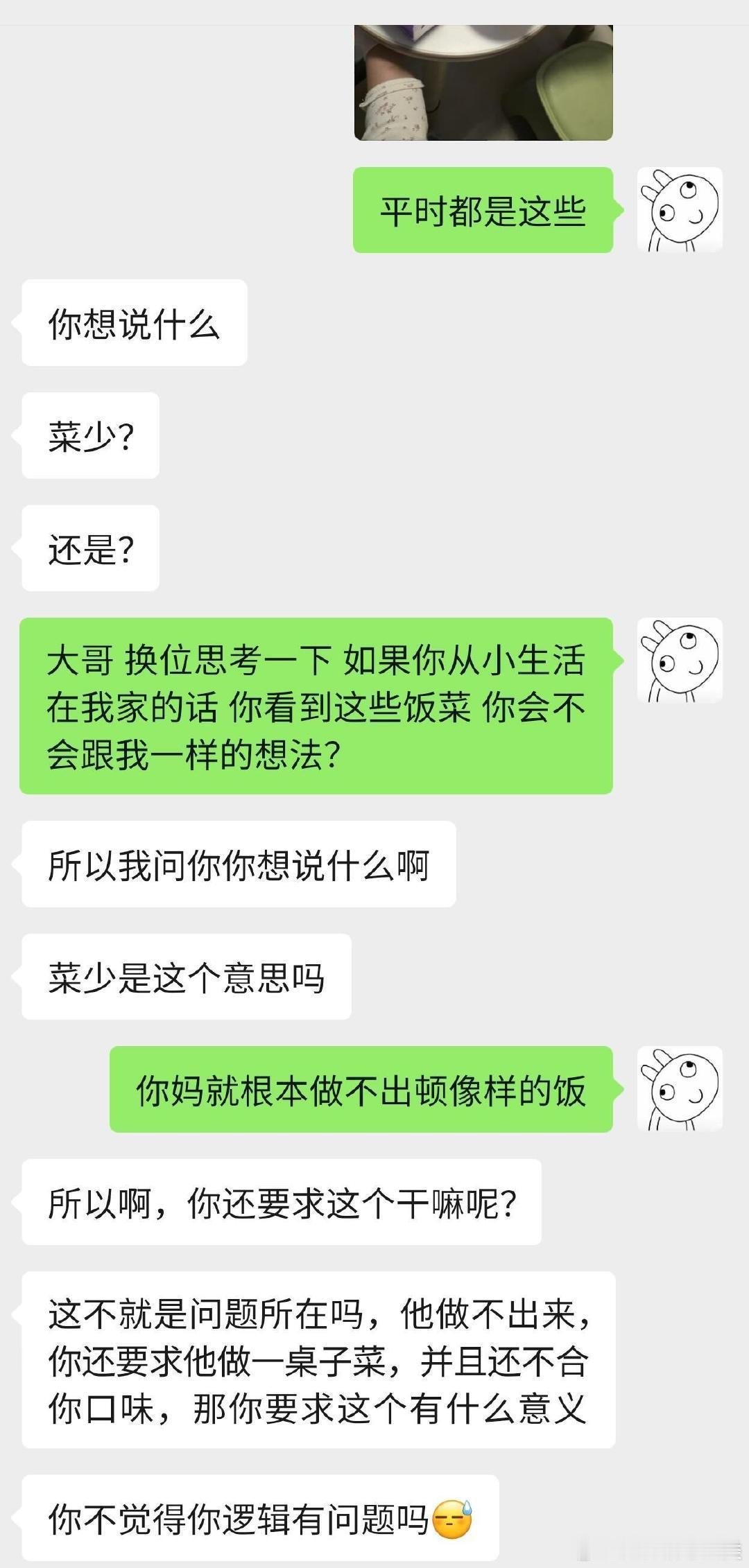1947年冬,山东一户农家的女主人,将一些吃的递给门前的乞丐,乞丐没有接,开口的一句话却让女人泪流满面。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山东一户人家的门被轻轻推开。门口站着个衣衫破烂、浑身沾满泥巴的人,头发结块遮住脸庞,只有一双眼睛透着执拗的光。 开门的女人定睛看清门口的人,身子一趔趄就扑了过去,双臂死死抱住他,滚烫的泪水一下子浸透了他单薄的衣襟。 这个人就是韩子栋。谁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像乞丐的男人,刚从几千里外的重庆逃回来。 韩子栋的晚年过得格外平静。身边人偶尔提起《红岩》里的华子良,他也只是默默听着,很少说那就是自己的原型。 这份“运气”,是十四年装疯卖傻换来的。时间回到1947年前后,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高墙之上架着电网,特务看守个个心狠手辣,这里关押的都是国民党军统认定的要犯。 可他和别的犯人不一样。在特务眼里,他就是个彻底疯了的“废人”。头发乱蓬蓬遮住眉眼,脸上总沾着污垢,整天要么对着墙壁傻笑,要么在放风院子里不停转圈。 特务们常拿他寻开心。把地上的虫子递到他面前,逼着他吃,他二话不说就抓起来塞进嘴里。动手打他、开口骂他,他也只是嘿嘿傻笑,没有半点反抗。 久而久之,“疯老头”成了他的代号,特务们对他彻底没了戒心。出门买菜的时候,还会喊上他帮忙提篮子,把他当成免费的苦力使唤。 没人看透这份疯癫背后的隐忍。韩子栋在大雨里奔跑,不是真的糊涂,是为了唤醒被牢狱生活磨萎缩的肌肉,为逃跑积攒力气。他吞吃虫子、忍受打骂,是故意装出来的模样,只为让敌人放下所有防备。 那间牢房又阴又潮,霉味呛人。他躺在冰冷的地上,每天都在心里默默琢磨着事儿。算着关押的日子,算着逃跑的路线,像一头耐心的猎豹,静静等待最佳时机。这个时机,他一等就是十四年,直到1947年8月18日。 那天,特务卢兆春要去磁器口买菜。不知道是那天天气晴好让人心情舒畅,还是打心底里认定韩子栋是个彻底的疯子,他竟然只带着韩子栋一个人,就走出了白公馆的大门。 卢兆春买完菜,被几个熟人拉进了路边的茶馆。赌瘾上头的他,早已把身边的“疯老头”抛到脑后。 他回头瞟了蹲在门口的韩子栋一眼,那人缩着身子像只没骨头的癞皮狗。他笃定这个连路都认不全的傻子,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他把枪往桌上一放,就投入到牌局里,吆喝声盖过了周围的喧闹。 韩子栋蹲在门口,表面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地面,注意力却全在屋里的特务身上。 他用眼角余光紧紧盯着卢兆春,看着对方全神贯注盯着手里的牌,连眼皮都很少抬。韩子栋知道,机会来了。 他慢慢站起身,装作要去解手的样子,一步一挪地朝着茶馆后面的小巷走去。刚转过墙角,脱离特务的视线,那个“疯老头”瞬间变了模样。 他身子一挺,迈开大步朝着嘉陵江边狂奔,速度快得像一头冲出牢笼的猛兽。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心脏跳得快要炸开,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拼命跑。 跑到江边,江水滚滚流淌,岸边孤零零系着一条小木船。船主不在,船桨却好好地放在船上。韩子栋来不及多想,纵身跳上船,拼尽全身力气划动船桨。 身后远远传来特务发现人失踪后的叫骂声、哨子声,他知道,自己终于逃出了白公馆这个鬼地方。 可逃出白公馆,只是苦难的开始。从重庆到山东老家,几千里路途,他身无分文,衣衫破烂,还被军统悬赏捉拿。 他心里清楚,大路上全是搜捕他的人。不敢有半点侥幸,只能专拣那些荒无人烟的山野走,白天躲着太阳,晚上摸着黑赶路。 饿了就到地里刨几个生红薯,连皮都不擦就啃着充饥。渴了就趴在河沟边,喝几口浑浊的脏水。 为了不被认出来,他故意把泥巴抹在脸上、身上,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乞丐。路过村庄时,不仅要躲开路人的目光,还要忍受恶狗的追咬,承受不懂事孩子扔来的石块。 四十五天,整整四十五天。好几次和搜捕的国民党士兵擦肩而过,对方闻到他身上的臭味,都捂着鼻子厌恶地推开他,没人会想到,这个邋遢的乞丐,就是他们要找的要犯。 支撑他走下去的,是怀里藏着的重要情报,那是必须亲手交给党组织的东西。还有对妻子李玉珍的牵挂,他始终相信,妻子一定在老家等着他。 终于,他走到了家门口,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屋里的炉火微弱,却驱散了他身上的寒气,温暖了他饱经磨难的身心。 看着妻子熬红的双眼、满是冻疮的双手,这个在特务严刑拷打下都没掉过一滴泪的硬汉,眼眶泛红,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韩子栋用隐忍和坚守,从黑暗里闯出了一条生路。那些藏在疯癫背后的清醒,那些埋在苦难里的坚守,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动人。这份风骨,穿越岁月,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