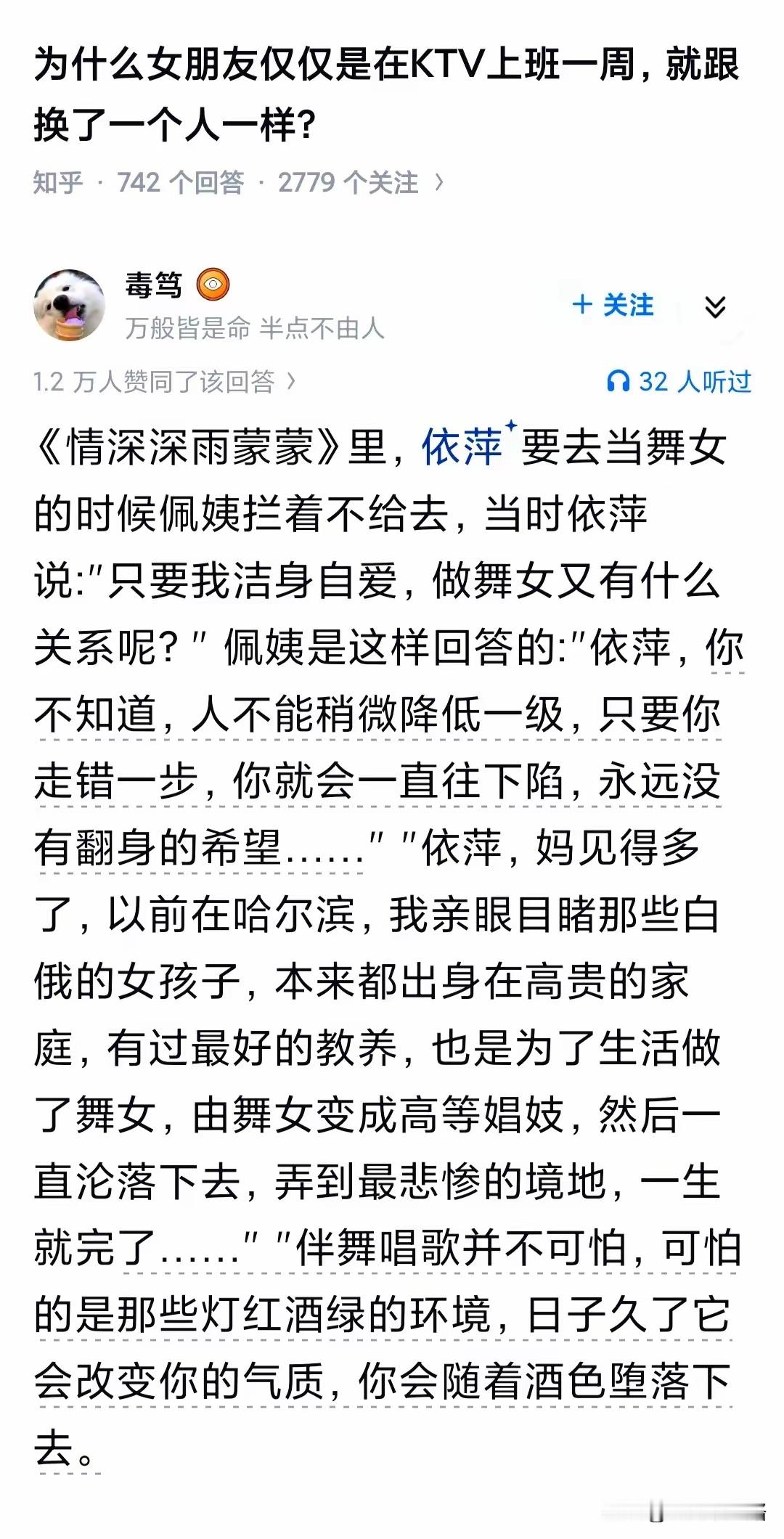1936年7月27日,哈尔滨警务厅档案室,一份法医报告把经办人吓得手一抖:乳头焦黑开裂,括约肌彻底罢工,心肺像破风箱,可人还清醒。这是赵一曼被“科学”折磨七小时后的体检表。 档案室里,煤油灯的光摇摇晃晃,把那张纸上的字照得发白。负责记录的警员是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人,叫小林,平时跟着老刑警查户口、抓小偷,从没见过这种阵仗。他攥着笔的手直抖,墨水滴在纸上,晕开一片黑。报告上写着“电刑持续7小时,皮肤呈焦褐色,乳头碳化,括约肌功能丧失,心肺功能严重受损,意识尚存”,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他眼里。 赵一曼是1935年11月在珠河被日军抓住的。她当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团政委,带着队伍在山林里打游击,被叛徒出卖后,被关进了哈尔滨警务厅的地下室。审讯她的,是警务厅长涩谷三郎,一个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军官,据说他以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后来改行当警察,最擅长用“科学方法”对付抗日志士。 第一次提审是在12月的一个雪夜。赵一曼被两个日本兵架着走进审讯室,她的棉袄破了,腿上全是血,可站得笔直,眼睛里没有半点害怕。涩谷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用生硬的中文说:“赵一曼,你只要说出抗联的据点,我就放了你。”赵一曼冷笑一声:“要杀要剐随便,别想让我背叛组织。” 涩谷的脸一下子沉下来。他挥了挥手,两个日本兵把赵一曼按在椅子上,开始用皮鞭抽。每抽一下,赵一曼的身体就颤一下,可她咬着牙,一声不吭。抽了二十多下,涩谷又让人拿来竹签,一根根扎进她的指甲缝里。赵一曼疼得浑身冒冷汗,可还是骂道:“你们这些强盗,总有一天会被赶出中国!” 从那以后,每天都有审讯。涩谷用尽了各种办法: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烙铁烫,可赵一曼始终没松口。到了1936年7月,涩谷急了,他决定用“电刑”——这是他从日本带来的新玩意儿,说是什么“科学审讯法”,能把人的神经彻底摧毁。 7月27日早上,赵一曼被带进审讯室。她已经瘦得脱了形,脸肿得像个馒头,可眼睛还是亮的。涩谷坐在电椅旁边,按下了开关。电流穿过赵一曼的身体,她的身体猛地挺起来,又重重地摔回椅子上,喉咙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可等电流停了,她又慢慢坐直,吐出一口带血的痰,说:“你杀了我吧,我是不会说的。” 这样的过程重复了七次。每次电流加大,赵一曼的痛苦就多一分,可她始终没求饶。到了第七次,她已经快失去意识了,可当涩谷问她“抗联的据点在哪里”时,她还是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知道。” 审讯结束后,涩谷让法医给赵一曼做检查。那个叫小林的警员跟着去了,他站在门口,听见里面传来赵一曼的呻吟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等他进去的时候,赵一曼正躺在病床上,胸口的衣服被撕开,露出焦黑的皮肤,乳头已经碳化,连周围的肉都烂了。她闭着眼睛,可还能听见她呼吸的声音,像破风箱一样,每吸一口气都要费好大劲。 小林拿起笔,手抖得写不了字。涩谷在旁边催:“快点写,把情况详细记下来。”小林咬了咬牙,写下了那些可怕的词:“乳头焦黑开裂,括约肌彻底罢工,心肺像破风箱,可人还清醒。”写完之后,他把笔扔在地上,转身跑了出去,跑到院子里,对着墙呕吐起来。 后来,小林偷偷打听赵一曼的情况。有人说,她被关在医院里养伤,可每天都骂看守;有人说,她写了一封信给儿子,说自己对不起他,让他长大后做个有用的人;还有人说,她在临死前还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林听了,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想起第一次见赵一曼的时候,她还笑着说:“小伙子,别害怕,我们会赢的。”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赴刑场。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走在路上,还唱着《国际歌》。路过的人群里,有个老太太抹着眼泪说:“这是个英雄啊!”小林站在人群中,看着她的背影,想起那份体检表,想起她在审讯室里的样子,想起她骂日军的声音。他知道,这个女人用生命守住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守住了中国人的尊严。 现在,哈尔滨的纪念馆里,还保存着赵一曼的那份体检表。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可每一个字都在告诉后人: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牺牲。而那些曾经折磨她的人,早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被人唾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