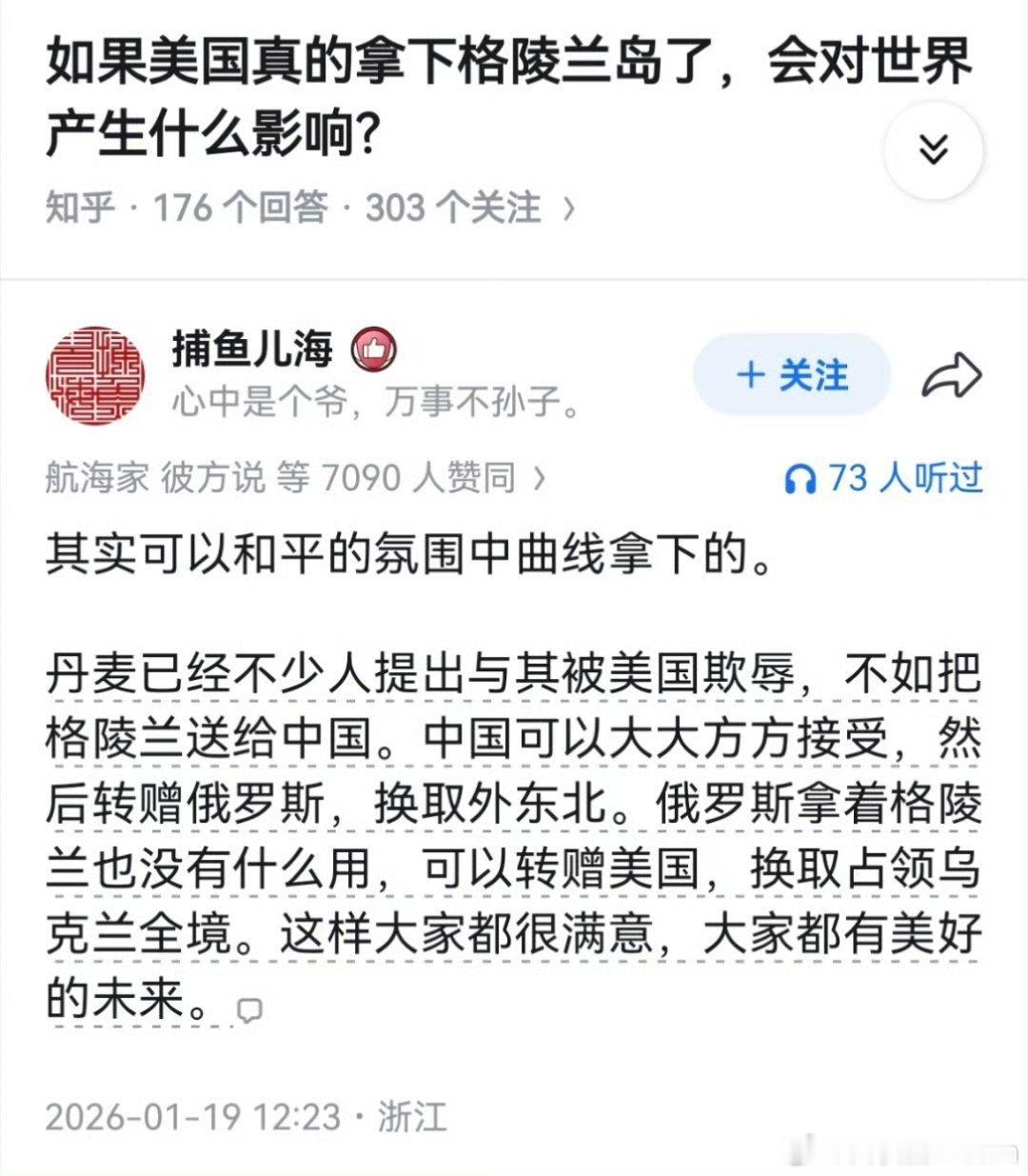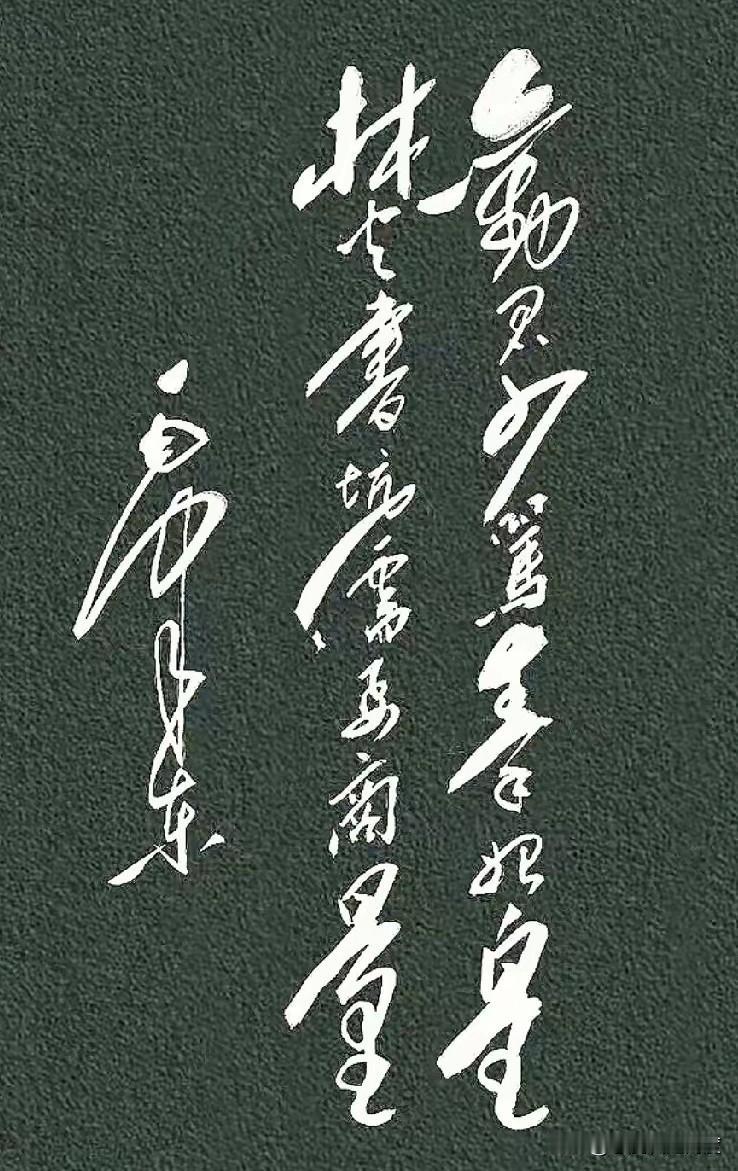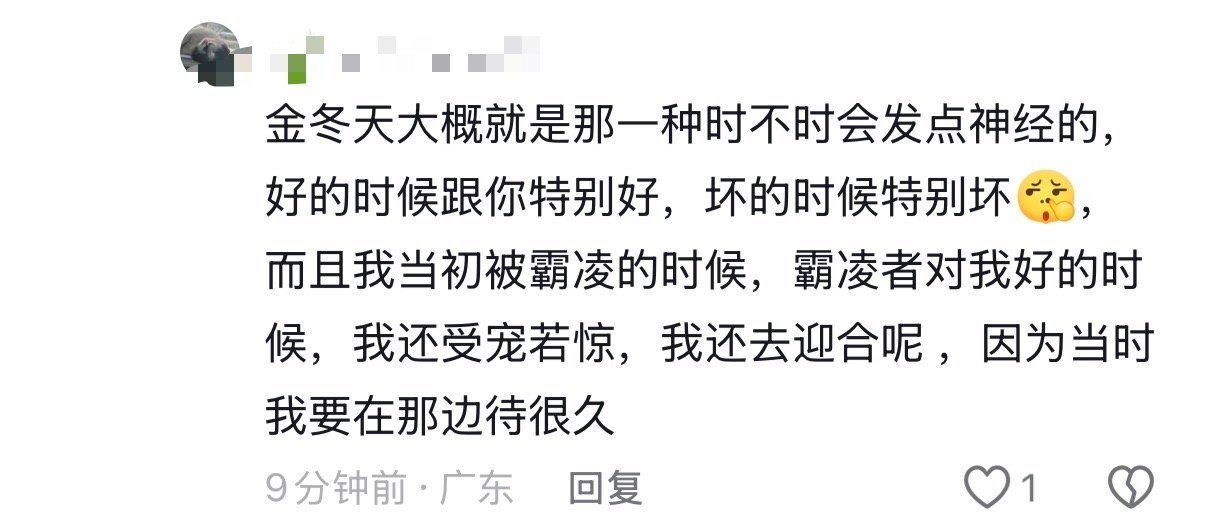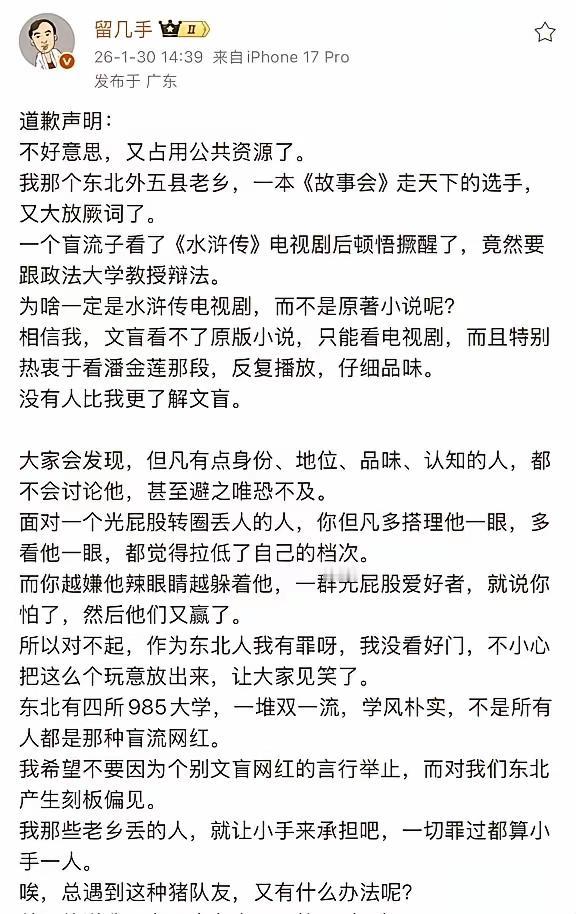女承“父钵”? 田禾,身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雕塑大师田世信之女,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和父亲一样投身于雕塑工作,我觉得她的这件作品也不雅观。 田世信的雕塑作品如“老子”“秋瑾”等,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与抨击,田禾为此为父亲辩解开脱。然而,瞧瞧她为民国才女张爱玲所做的雕塑,其手法与父亲如出一辙,好似得了父亲的“真传”,却也未见得高明多少。张爱玲一生坎坷,漂泊不定,情感经历曲折,但她的才情风貌和人生结局绝不是这雕塑所呈现的这般凄惨可怜。看那雕塑,双眼空洞无神,一脸麻木不仁,还像孕妇似的捧着肚子,活脱脱一个鲁迅先生小说《祝福》里痛失幼子"阿毛"的“祥林嫂”。要是张爱玲有后人,我想他们肯定会找上门来。 田世信的雕塑争议早已不是新鲜事,苏州金鸡湖畔的老子像以吐舌露齿的造型打破公众认知,金鸡湖景区的秋瑾雕像又因五官扭曲、神态狰狞被指消解英烈风骨,两次争议都踩中了公众对历史文化人物的情感底线。田禾当时站出来为父亲辩解,说父亲的创作是捕捉人物内心挣扎的破茧式写意,还将大众的不满归因为审美层次不足,这番回应没能平息争议,反倒让更多人看清田氏创作的核心问题,不是技法生疏,而是对人物精神内核的刻意偏离与刻板解读。田禾自幼在父亲的工作室长大,看惯了泥坯与刻刀,耳濡目染下走上雕塑道路,天津美术学院的专业学习让她掌握了扎实的造型功底,家学加持与科班训练本该让她跳出父辈的创作窠臼,走出属于自己的艺术路径,可她塑造张爱玲的每一处线条、每一个神态,都在复刻父亲的创作逻辑,把对人物的片面认知,直接转化为僵硬且失真的形体表达。 张爱玲的人生从不是任人揉捏的悲情剧本,她早年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一支笔写尽都市男女的情爱与凉薄,文字里藏着清醒的通透与孤傲的风骨。晚年移居美国后,她深居简出、频繁搬家,常年被身体不适与避世心态困扰,却始终没有放下纸笔,三十年间与友人往复百余封书信,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即便居所简陋、生活清简,也始终保持着文人的自持与体面。她的孤寂是主动选择的精神独处,是不愿与世俗周旋的自我坚守,和祥林嫂被命运碾压、被苦难吞噬的麻木绝望,有着本质的区别。祥林嫂的悲是底层女性无处可逃的生存绝境,张爱玲的孤是知识女性主动疏离的精神边界,二者的苦难形态、精神底色完全不同,田禾却用同一套悲情化的创作手法,把张爱玲塑造成了失去灵魂支撑的可怜人,彻底抹去了这位民国才女最核心的精神气质。 公共人物的雕塑创作,从来不是艺术家的私人情绪宣泄,更不是照搬固定模板的流水线作业。老子是道家文化的符号,秋瑾是民族英烈的代表,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标杆,这些人物早已融入公共文化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与认知。雕塑家的使命,是用形体传递人物的灵魂,是用艺术语言还原人物的风骨,而不是拿着“写意”“先锋”的借口,随意扭曲人物形象,消费人物的苦难标签。田禾承袭了父亲的雕塑技法,也承袭了父亲的创作短板,只看到人物人生里的坎坷片段,却读不懂坎坷背后的精神力量,只敢用夸张的神态、失真的体态放大悲情,却不敢直面人物真实的复杂与立体。 家学传承的意义,从来不是复制父辈的风格与争议,而是站在父辈的技艺基础上,更新认知、拓宽边界,用更成熟的思考、更真诚的表达,完成艺术上的迭代与升华。田禾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有得天独厚的创作起点,本该读懂张爱玲文字里的高傲与清醒,读懂她人生里的倔强与自持,却偏偏选择了最浅薄、最失真的表达,把一位文坛才女塑造成了面目模糊的悲情符号,既辜负了自己的专业素养,也辜负了公众对经典人物的文化情感。 艺术可以有个性,可以有创新,但不能脱离基本的人文尊重,不能无视公共的文化共识。真正的雕塑艺术,塑的是形,立的是魂,丢了魂的作品,再精巧的技法也只能是没有温度的泥坯,再标榜艺术价值,也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