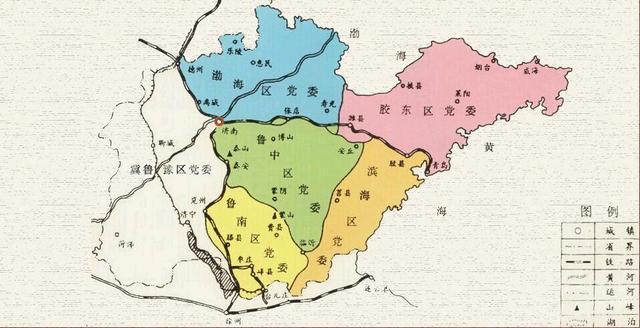1949年淮海战役后,萧县临涣集的打谷场上,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裹着士兵棉袄,和数十名灰色俘虏一起蹲在地上,只在登记表上写下四个字:我是军长。 名字报到华东野战军机关时,几十行战俘名单上,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停了笔,认出这是湖南平江那位因一次学潮被教会中学开除的学生,两人已近30年未见。 他在档案里是一串年份:1932年黄埔四期,1937年淞沪与南京,1938年万家岭强攻张古山,1945年雪峰山围歼日军一个师团;几次负伤后升到军长,还写出在两军中通行的《合同战术》。 按当时规定,这一级别战败将领多被送往北京功德林,与王耀武、杜聿明等十多名军官一同改造,但1949年冬天钟期光只说一句“去军校当教员”,让他从战犯队列被硬生生挪到了讲台一侧。 此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他一讲就是十几年,把1930年代的会战细节拆给新中国第一代军校学员听;回头看1949年的那份名单,有人说这是善用军事人才,也有人会想,当时在那块不足1平方米的纸上,其实还可能写出多少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