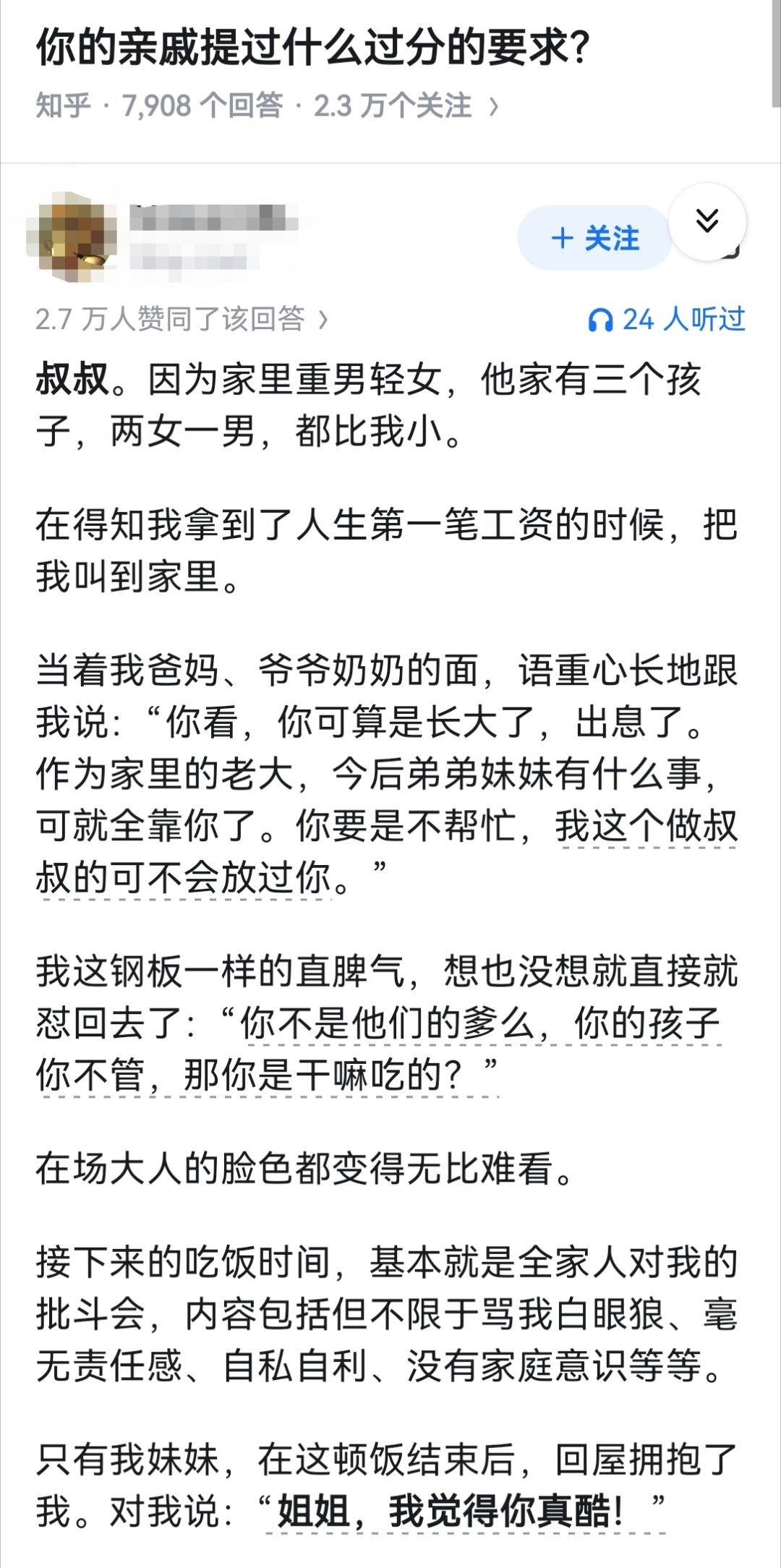我真搞不懂我妈! 结婚20多年了,我妈只来过我家几次,每次呆几天就走了。 平常我和老公请她,开车去接,她也总拒绝,怎么劝也不听。她说,这是你们小两口的家,不能老打扰我们的生活。 上个月整理储藏室,翻出一捆用红绸带扎着的柴禾,木头早干透了,裂缝里还卡着片干枯的银杏叶。 这是前年搬家时我妈送来的,她说老家讲究“进门有柴,日子有财”。 那天她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新家玄关处,脚尖都没敢完全踩进地毯。 木柴捆得整整齐齐,红绸带在门口瓷砖上蹭出细碎声响。 她蹲下身,手指在柴缝里抠了抠,抽出个信封塞进我手里——后来才发现,那捆柴里藏着两万块钱,纸币被柴火熏得带着松木香。 这是她第四次来我家,也是唯一一次没说“添麻烦”的话。 她摸着新刷的墙,眼睛笑成条缝:“地砖真亮,能照见人影了。” 可第三天一早,她还是背着包要走,说地里的萝卜该收了,再不回去要被霜冻坏。 更早的一次,是十年前老公做手术。 我凌晨打电话说情况不太好,她没说要来,只问清了医院地址。 第二天傍晚,她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个保温桶,裤脚还沾着泥。 “县城老中医说的,天麻炖母鸡补元气。”她掀开桶盖,蒸汽扑得眼镜片发白,“我坐最早的长途车去山里买的,现杀的鸡,还热乎。” 老公醒后她守了两夜,第三天天没亮就收拾东西:“你们照顾病人够累了,我在这儿净占地方。” 最让我难忘的,是刚生完孩子那年。 她来医院看我,放下个布包就往婆婆手里塞钱:“亲家母,辛苦你了,这六千你拿着买营养品。” 又递给我个存折:“这一万你留着,给孩子买奶粉。” 我让她住家里,她摆摆手:“我夜里打呼,影响你和孩子休息;做饭口味重,怕你们吃不惯。” 一周后她走时,我发现她偷偷把我换下的月子服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阳台栏杆上,风一吹,蓝格子布料晃悠着像面小旗。 公公去世那年冬天,她倒是在我家待了整七天。 可那七天,她几乎没跟我说过几句话,天天陪着婆婆坐在沙发上,递水、削苹果、听婆婆讲过去的事。 临走前她拉着我和老公的手:“你妈(指婆婆)这辈子不容易,你们多担待。” 转身又塞给婆婆个手绢包:“这是我攒的,你留着零花,别委屈自己。” 我们不是没劝过。 “妈,您都70岁了,跟我们住,我们也好照应。” “城里医疗方便,小区里还有老年活动中心。” 她总笑着摇头:“我在老家住惯了,街坊邻居都熟,早上能去公园打太极,傍晚还能跟你张婶跳广场舞。” 有次视频,我看见她在院子里劈柴,斧头抡得老高,木柴“咔嚓”裂开时,她咧着嘴笑——那笑容,比在我家看到新地砖时还要亮。 有时我会想,她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城里? 是怕电梯太快会晕,还是嫌超市的菜没有老家集市新鲜? 或者,她只是觉得,孩子们成家了,就该有自己的天地,她这个当妈的,远远看着就好? 前几天视频,她正给窗台上的多肉浇水,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撒了把碎银。 “妈,下个月我们回去看您。” “不用不用,”她赶紧摆手,“你们忙你们的,我好着呢,昨天还跟你张婶去爬山了。” 挂了电话,老公叹口气:“妈这是怕给我们添麻烦啊。” 我望着手机屏幕上她没来得及关的摄像头,窗台上那盆多肉胖乎乎的,叶片上还挂着水珠。 突然想起她送柴来时说的:“日子就像这柴禾,得自己烧才暖。” 或许,她不是不愿来我家,只是想用她的方式,让我们的“柴禾”烧得更旺些吧? 可我还是想问,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也给您添添“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