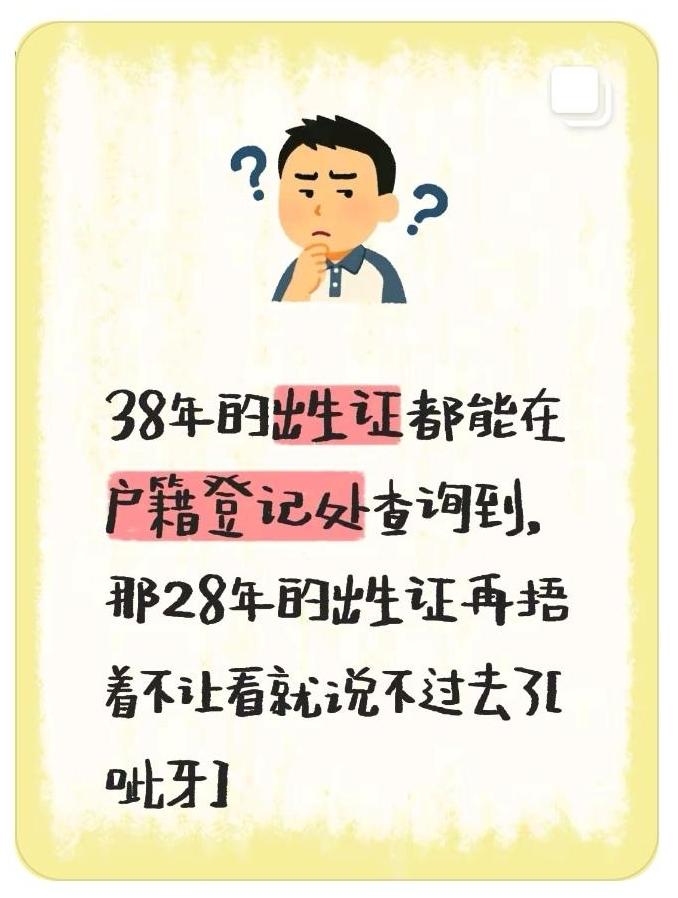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不成,被日军安置在医院,一名护士每次给他换药,都会多给他一张干净的纱布,郑意识到,他最后的情报有救了。 1942年的上海,沦陷区的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郑文道是中共地下党上海联络站的骨干,负责传递日军动向的核心情报,却因叛徒出卖被捕。日军的酷刑没能撬开他的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浑身是伤的他趁着看守不备撞向墙壁,只想以死保守秘密,可最终还是被日军抬进了医院,成了严密监视下的“活囚犯”。 病房里只有一张铁架床,窗户钉着粗铁条,门口两名日军士兵端着枪日夜值守,连他翻身的动作都会引来警惕的呵斥。每次换药的日军军医态度冷漠,动作粗暴,纱布用完就扔,从不多给半片。直到第三次换药,进来的换成了一名年轻护士,穿着洗得发白的护士服,眉眼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她换药时动作很轻,避开伤口最疼的地方,消毒水擦拭时会下意识地放慢速度。郑文道起初没在意,只当是普通护士的恻隐之心,可当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手指悄悄一松,一片叠得整齐的干净纱布落在了他的枕边,眼神飞快地与他对视了一秒,便低头匆匆走出病房。 郑文道的心猛地一跳。他躺在病床上,眼角的余光瞥着门口的日军,缓缓将手伸到枕边,攥住那片额外的纱布。纯棉的纹理粗糙却干净,绝不是日军医院里那种反复使用的旧纱布。他忽然想起出发前联络站负责人说过的话:“若遇紧急情况,会有同志以‘多一份物资’为信号接头。” 难道,眼前这位护士,就是自己人?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换药,这位名叫沈兰的护士都会多留下一片纱布。有时是趁日军转身点烟的间隙,有时是假装整理床铺时悄悄放下,从不多说一个字,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郑文道渐渐确定,这不是偶然,沈兰是来帮他传递情报的。 可情报怎么写?没有笔,没有纸,身边全是日军的监视。他看着自己手臂上未愈合的伤口,突然有了主意。每次换药后,他都会趁着夜深人静,用指甲抠破伤口边缘的结痂,蘸着渗出的鲜血,在纱布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日军即将对苏州河沿岸地下党联络点进行大清剿的时间和路线,还有叛徒的具体信息。 写情报的过程比受刑还煎熬。伤口被反复抠破,疼得他浑身冒冷汗,只能咬着枕头强忍,生怕发出一点声音。每写一个字,都要小心翼翼,确保字迹虽小却清晰,写完后再将纱布叠成极小的方块,藏在床板的缝隙里,那是沈兰每次整理床铺时都会留意的地方。 沈兰很快发现了床板下的纱布。那天她换药时,故意将药盘掉在地上,弯腰捡拾的瞬间,手指飞快地伸进缝隙,将纱布藏进袖口,整套动作行云流水,门口的日军丝毫没有察觉。郑文道看着她挺直脊背走出病房的背影,心里既欣慰又担忧,他知道,沈兰带着这份情报离开,每一步都踩着刀尖。 果然,没过两天,病房里的日军看守突然增多,军医换药时眼神凶狠,反复盘问“有没有和其他人接触”。郑文道心里一紧,以为情报暴露了,可他始终咬定“除了换药护士,没见过任何人”。日军搜遍了病房的每个角落,床板、被褥、甚至伤口的纱布都拆开检查,却什么也没找到——沈兰早已将情报转交给了地下党联络站,自己则继续留在医院,装作若无其事。 又过了一周,郑文道从日军的交谈中零星听到“苏州河据点扑空”“叛徒失踪”的消息,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他知道,沈兰成功了,那份用鲜血写就的情报,拯救了整个联络站的同志。可他也清楚,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日军一旦确认情报泄露,绝不会放过他。 沈兰似乎也察觉到了危机。那天换药时,她趁着给郑文道盖被子的瞬间,悄悄塞给他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上面只有三个字:“今夜走”。郑文道攥着纸条,眼眶发热。他不知道沈兰用了什么办法安排撤离,只知道这意味着她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深夜,医院突然停电,整栋楼陷入一片漆黑。日军的呵斥声、脚步声乱作一团,郑文道按照纸条上的指示,悄悄挪到病房角落,掀开一块松动的地板砖,里面藏着一套护士服和一把小巧的剪刀。他快速换上护士服,用剪刀剪短头发,刚走到门口,就看到沈兰举着蜡烛跑过来,低声说:“跟我走,后门有同志接应。” 两人借着烛光,在走廊里快速穿行,遇到巡逻的日军,沈兰就用日语解释“病人需要转移病房”,从容不迫的态度竟骗过了对方。直到跑出医院后门,坐上一辆等候已久的黄包车,郑文道才敢回头看,沈兰站在门口的阴影里,朝着他的方向轻轻点头,随即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后来,郑文道辗转到了延安,才从联络站同志口中得知,沈兰是一名潜伏在日军医院的地下党,为了接应他,提前策反了一名日军清洁工人,制造了停电事故,自己却因为暴露身份,不得不连夜撤离上海,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2年的那场医院接头,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却藏着地下工作者最纯粹的信仰与默契。郑文道用鲜血传递情报,沈兰用勇气搭建生路,他们素昧平生,却因同一个目标生死与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