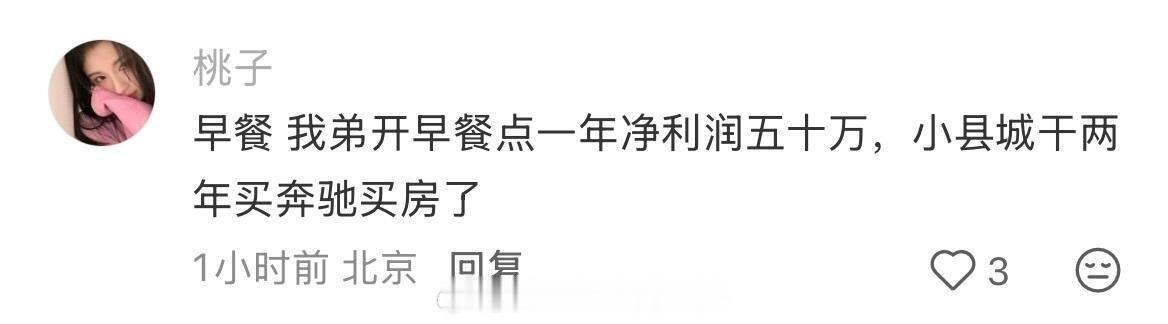当年老婆也是她们村的村花,花了重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抱回家,可现在又咋样呢?年轻时总觉得娶老婆一定要娶最漂亮的,人到中年才发现漂亮的当不了饭吃,反而会给你无尽的折磨,一下子伺候不到位人家马上就甩脸色!我那天起晚了,随便炒了个青菜,她扒拉两口就把筷子往桌上一放:“盐都不舍得放?你是想让我淡出鸟来?”盘子磕在桌上哐当响, 当年在村口第一眼看见她挑水,蓝布衫被风掀起角,扁担压得肩膀微红,我就觉得——这姑娘眼睛里有光,是我们村最亮的星。 媒人说她家要三间瓦房加一台缝纫机,我咬咬牙把准备盖猪圈的木料卖了,又借了三叔的钱,才算把“村花”娶进门。 那时候总跟兄弟吹:“我老婆,十里八乡数第一,你们谁有这福气?”夜里偷偷看她睡颜,觉得这辈子值了。 可现在呢?厨房瓷砖缝里的油污擦了又长,她总说我洗碗不擦灶台,我嫌她拖地非要顺着纹路——日子早被这些碎事磨出了毛边。 那天我起晚了,闹钟响第三遍才弹起来,冰箱里只剩半把青菜,急急忙忙倒油下锅,忘了放盐都没察觉。 她端着碗扒拉两口,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盐都不舍得放?你是想让我淡出鸟来?” 盘子磕在桌上哐当响,我心里那股火“噌”地就上来了——年轻时捧在手心里怕摔了的人,现在怎么成了一点就炸的炮仗? 其实她不是一直这样的。刚结婚那年我发烧,她守在床边用酒精擦手心,整夜没合眼,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子,还笑着说“你命金贵,可不能有事”。 后来呢?我忙着跑运输,她在家带孩子、种责任田,我总说“你在家多轻松”,没看见她手上的茧子比我方向盘上的还厚。 那天她摔筷子后,我闷头抽烟,看见她偷偷揉太阳穴——后来才知道,她那天偏头痛犯了,疼得厉害,吃什么都没味道。 年轻时总觉得婚姻得有个漂亮的开头,像年画里的才子佳人,可日子过着过着才发现,年画会褪色,能撑着走下去的,是她半夜给你掖被角的手,是你咳嗽时她递过来的温水,是两个人都累的时候,能说句“今天辛苦了”。 那天晚上我没跟她说话。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买了她爱吃的韭菜,炒了盘带点辣味的炒蛋——她吃的时候没说话,嘴角却偷偷翘了一下。 人到中年才懂,当年费九牛二虎之力娶回家的“村花”,不是用来供着的菩萨,是要一起在烟火里磨性子、搭伙过日子的伴儿。 漂亮当然好,谁不喜欢看好看的人?可婚姻这锅粥,光靠颜值当柴烧,迟早会糊;得两个人都往灶里添点理解、加点包容,才能熬出暖乎乎的甜。 现在她偶尔还是会嫌我袜子乱扔,我也会笑她追剧哭得抽抽搭搭,可厨房飘出来的油烟味里,总混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甜——那是当年村口的星光,落到了柴米油盐里,成了日子本身。
家族聚餐,姑父当众笑我:“挣那点钱不如跟我干。”我低头扒饭没吭声。散场后,他豪车
【2评论】【3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