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红军名将侯中英,最后的一张影像,他的意志极为坚定,不向敌人透露半点有用的信息,敌人恼羞成怒,将他残忍杀害。 如果你现在去翻阅那一帧拍摄于1932年的老照片,很难不被那个人的眼神给“烫”一下。照片里的人衣襟敞开,瘦骨嶙峋,胸膛上交错的伤疤像干枯的河床。那是红三军团五军一师师长侯中英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影像。与其说那是死囚的留影,倒不如说是一个胜利者的蔑视——那种要把镜头甚至镜头背后的刽子手生吞活剥的凶狠。 但这股子狠劲儿,真不是天生带来的。他也是肉体凡胎,1900年出生在湘鄂赣边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里。在那片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的土地上,他原本只是一个看着地主鞭子发抖、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种地娃。直到二十岁那年,接触了新思想,看了太多乡亲在水深火热里求告无门,那颗反抗的种子才彻底炸开。为了这点盼头,他扔下锄头冲进农会,从地方游击队的小卒干起,一路把自己锤炼成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虎将。 你要是仔细看那张照片上他身体的细节,就会发现很多伤其实不是最后那几天受的。有些伤疤,是在攻打长沙的城墙下留下的。那时候云梯被炮火炸断了,也没人下令,他把半截断梯往城墙上一架,不管那个大铁钩子是不是划破了大腿,甚至血顺着裤脚管像溪水一样淌,他连哼都不哼一声,只顾着往上蹿,那一刻他在战友眼里就是个“疯子”。 还有些伤,是在反“围剿”的山沟里落下的。粮草断绝的时候,他就带着大家啃树皮、嚼皮带。有一次深夜遭遇肉搏战,大刀砍卷了刃,他直接用拳头砸、用牙齿咬,那场仗打完,手指甲硬生生被掀掉了三个,可第二天老乡看到他时,他正用刺刀挑脚底板跑烂的血泡,还咧着嘴笑,说这下跑得更快了。 这种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硬骨头,敌人是拿他没办法的。1932年那个惨烈的春天,形势急转直下。赣州战役打得胶着,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为了给大部队争取哪怕是一丁点儿撤退的空隙,侯中英把生的路让给了别人。最后时刻,他被敌人包围,枪膛里的子弹打光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怕落入敌手,他就在枪林弹雨里把纸塞进嘴里,嚼成纸浆生咽了下去。等到胸口中弹倒在樟树下时,他全身上下除了那口气,什么有用的都没给敌人剩下。 抓到这么一个红军高级将领,敌人觉得自己捞到了宝。审讯室里,一开始还是摆着“礼贤下士”的谱,美酒佳肴满桌,高官厚禄许诺,想用荣华富贵买他嘴里红军的去向。但这笔买卖在侯中英这里注定是亏本的。面对那些虚伪的笑脸,他只有怒斥和不屑。这一招行不通,敌人就露出了獠牙,审讯室变成了屠宰场。 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那具身躯承受了什么。皮鞭蘸着凉水抽,那是家常便饭;老虎凳、红烙铁乃至灌辣椒水,能用的刑具都用遍了。最残忍的是,那些丧心病狂的刽子手甚至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把他整个人吊在房梁上。肋骨被打断了,昏死过去就被冷水泼醒。可每一次醒来,面对审讯者的咆哮,那个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汉子只有两个字的回应:“不知”。在这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子弟心里,账算得很清楚:身子烂了是自己的,但只要守口如瓶,红军的根就在。 1932年3月26日,敌人彻底绝望了。他们明白,从这个钢铁做的人身上榨不出半点油水,便决定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刑,妄图用恐惧震慑百姓。那天太阳毒得很,侯中英被拖到了稻田边。他不像一般的死囚那样萎靡,尽管身上没一块好肉,走起路来还要拖着满身的血污,但他把那被打断的脊梁硬是挺了起来。 在这个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没有哭喊求饶。在那滚烫的泥水地里,面对即将落下的屠刀,他积攒起最后一口气,把一口带血的唾沫狠狠吐在刽子手脸上。在那一刻,他或许想到了自己这辈子虽然短,但打过土豪、分过田地,为受苦人出过头,这辈子值了。随着一声“我这辈子够本了”的怒吼,那个仅仅32岁的年轻生命,连同他满腔的热血,一起融进了脚下这片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 当地的村民没敢大张旗鼓,只能偷偷把这位“侯师长”埋在满是稻茬的田里。没有墓碑,就在坟头压了一块刻着字的青砖,上头写着“硬骨头”三个字。后来村里的老人总跟后生们讲,那块砖头缝里长出来的稻子,总是比别处的密,风一吹沙沙作响,像是有人还在那里练兵。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回头看侯中英最后那张照片,依然会被那种纯粹的意志力所震撼。那个年代的先烈们,可能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傍身,他们的逻辑简单而粗暴——为了让后人能挺直腰杆,为了不用再给地主交租,为了这片土地能长出属于自己的粮食,他们甘愿把命当作那一块块铺路的青砖。这不仅仅是牺牲,这是对光明未来的“预付”。当我们站在霓虹闪烁的今天,真的应该在心里给那位衣衫褴褛的前辈敬个礼,因为是他那句“够本”,换来了我们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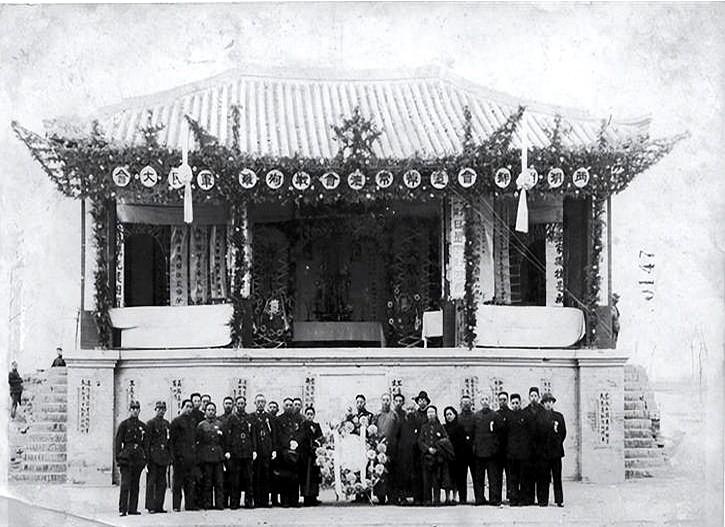




用户10xxx34
致敬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