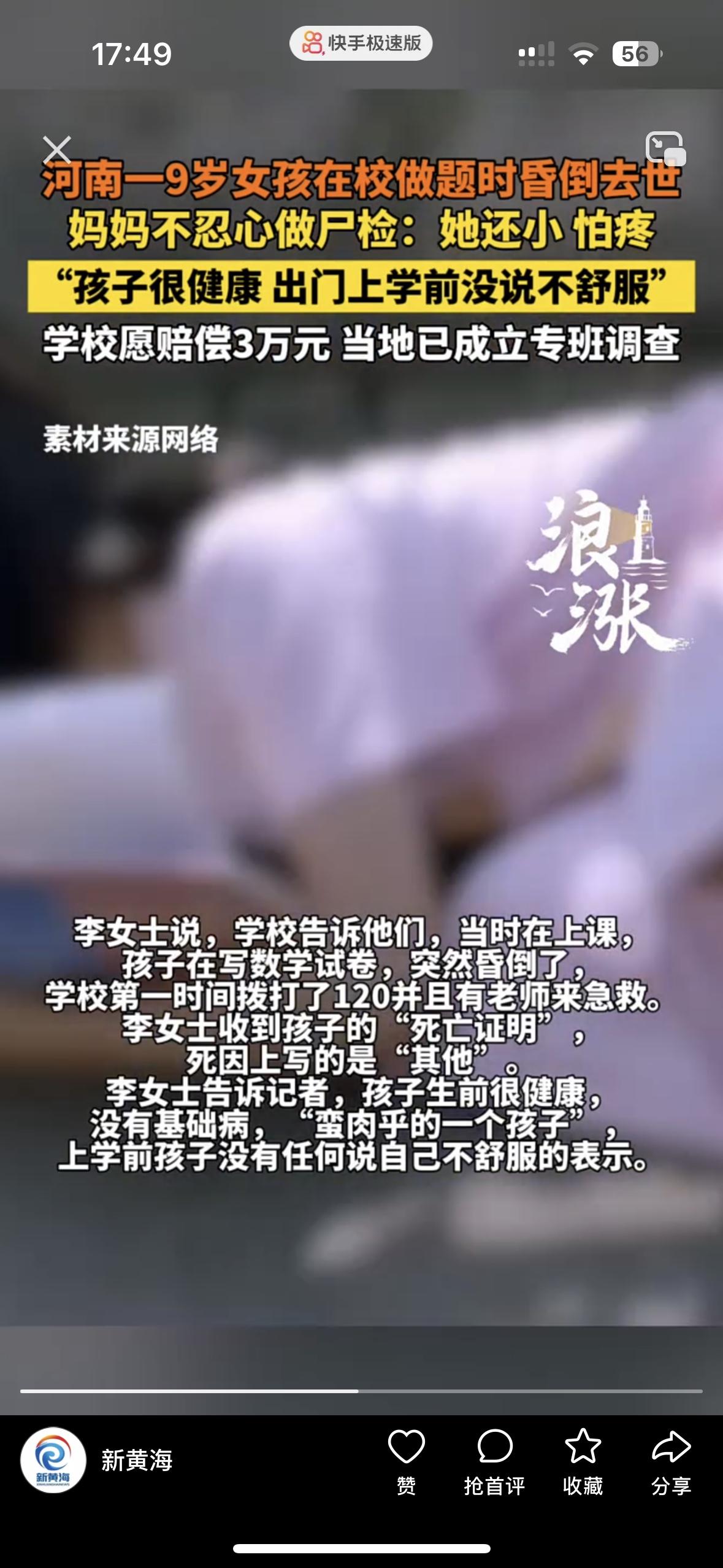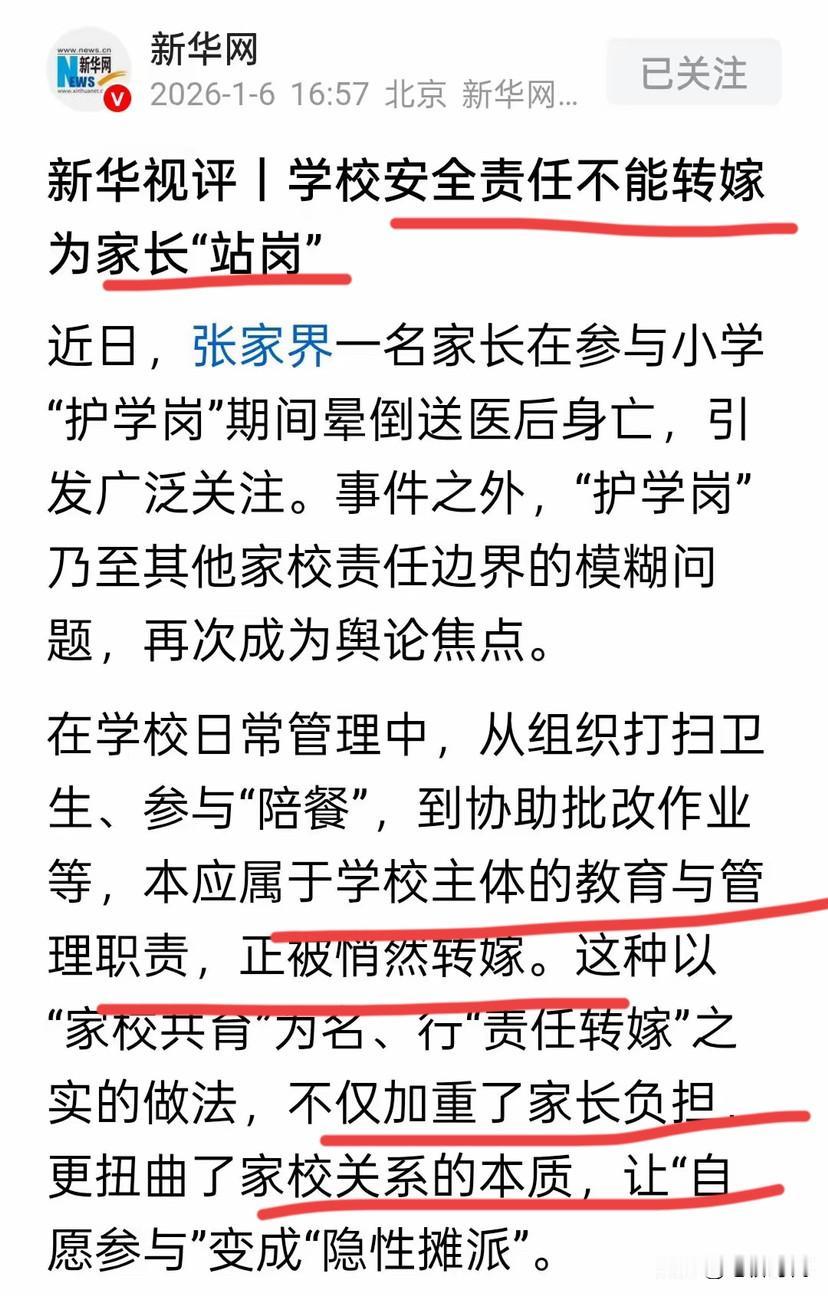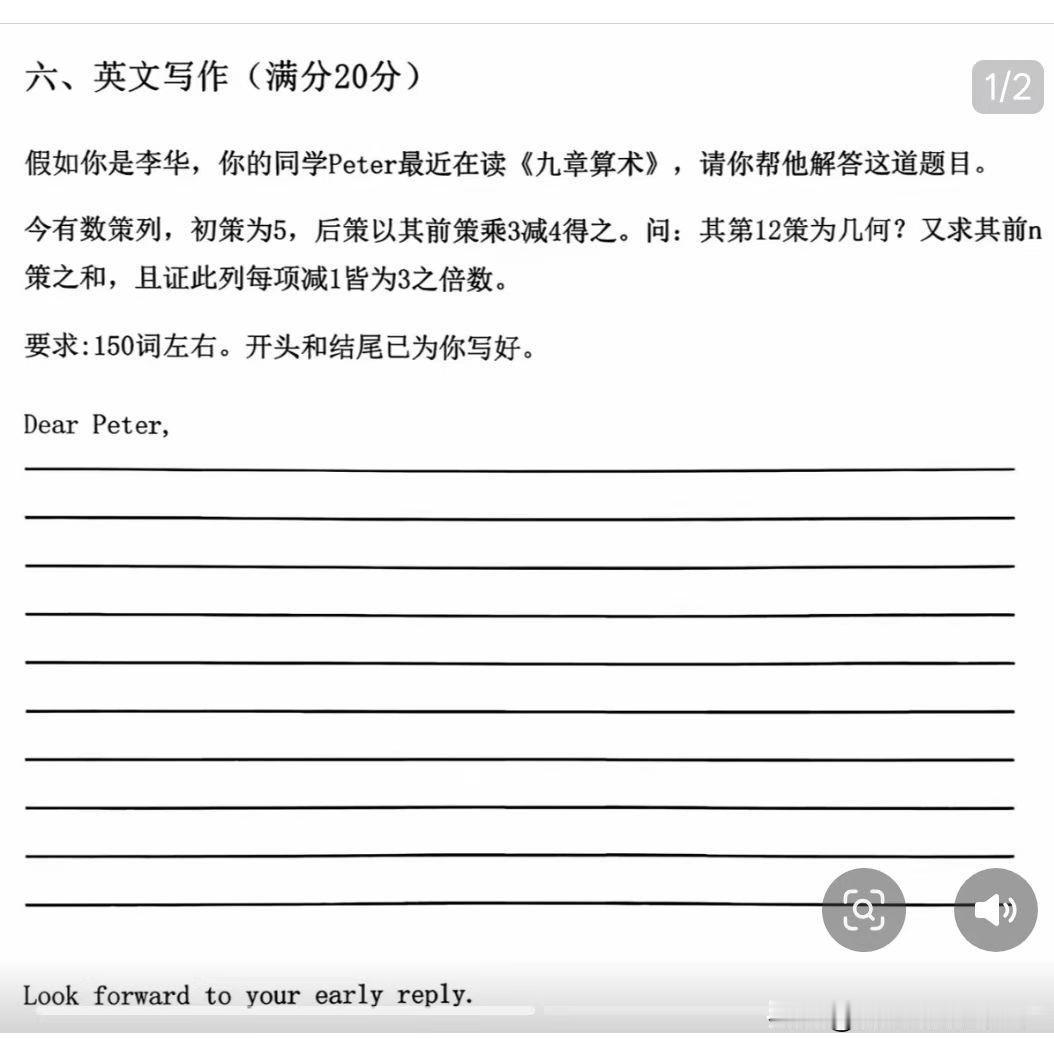1996年,公费留学的黄大年加入英国籍,父母强烈反对,他说:就算骂我,我也要加入英国国籍!12年后,他突然卖掉英国别墅,决定回国,妻子犹豫,他直接撂下一句狠话,要么随我回国,要么离婚! 这事儿听着就让人心里揪得慌。一个当初拼了命要拿英国护照的人,怎么扭头就把伦敦郊区的别墅挂牌出售,连夜打包行李非要往回赶?周围朋友全懵了,说他是不是在英国待出毛病了。其实黄大年清醒得很,他那股劲儿从来没变过,只不过年轻时想出去,中年时想回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热”烧得正旺。黄大年握着公派名额踏上英伦土地,眼里全是国内没有的先进仪器、宽松的学术氛围。实验室通宵亮着的灯,咖啡馆里随时能开始的学术争论,这些像磁石一样吸着他。拿到永久教职那天,他打电话回家,父母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父亲最后只说了一句:“家里供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变成外国人。”黄大年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还是把材料递进了移民局。他知道会被骂“忘本”,但在那个年代,留在西方搞科研,对很多学者来说就是“走上巅峰”的代名词。 日子一年年过去。黄大年在英国有了房子、车子,花园里玫瑰开得正好。可夜深人静时,他总盯着电脑屏幕上国内同行发来的邮件出神,那边项目缺关键技术,那边团队遇到瓶颈……某个冬夜,他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启动深地探测项目的新闻,心脏突然猛跳起来。那正是他钻研的方向。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剑桥的康河柔波,而是吉林老家冬天结冰的河面,是读书时学校墙上“振兴中华”的斑驳标语。 “收拾东西,我们回国。”吃早餐时他突然对妻子说。妻子手里的叉子“哐当”掉在盘子里。“你疯了?孩子在这儿上学,我工作刚稳定……”黄大年站起身,目光钉在窗外:“要么跟我走,要么分开。”这话冷得像刀子。他没说出口的是,前些日子参加国际会议,外国专家谈及中国该领域时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气,像针一样扎在他背上。他想起当年出国,不就是想学真本事吗?现在本事学到了,老家需要他,却窝在别人的地盘上伺候花园? 回国手续办得出奇快。飞机落地北京那天下着小雨,黄大年深吸一口潮湿的空气,竟然笑了。接机的同事差点没认出他,这个穿着旧夹克、拎着两个大箱子的人,和之前照片里西装革履的英国教授判若两人。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黄大年像颗钉子一样扎进吉林大学的地质宫,每天熬到深夜。他带着团队冲进了国内空白的研究领域,硬是在几年里把中国深地探测技术往前推了一大截。有学生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摆摆手:“欠的债得还。”没人知道他欠了什么债,但所有人都看见,他办公室的灯总是地质宫里最后熄灭的一盏。 可惜老天没给他太多时间。2017年,黄大年因病去世,年仅58岁。追悼会上,人们发现他一张存折里只剩几十块钱,奖金全捐了,工资也贴补了学生。当年反对他出国的老父亲,此刻摸着儿子的照片老泪纵横:“这孩子……心里太能装事了。” 从“就算骂我也要入英籍”到“不回国就离婚”,表面看是极端矛盾的选择,内里却是一以贯之的执拗,对专业极致的追求,对家园深沉的回响。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类似的撕裂:出去,可能背负骂名;回来,可能失去已拥有的一切。黄大年用他激进的方式完成了一个人的“闭环”。我们或许不必歌颂这种决绝到伤及家人的选择,但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历史关口,正是这种“一根筋”的人,扛起了常人望而却步的重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