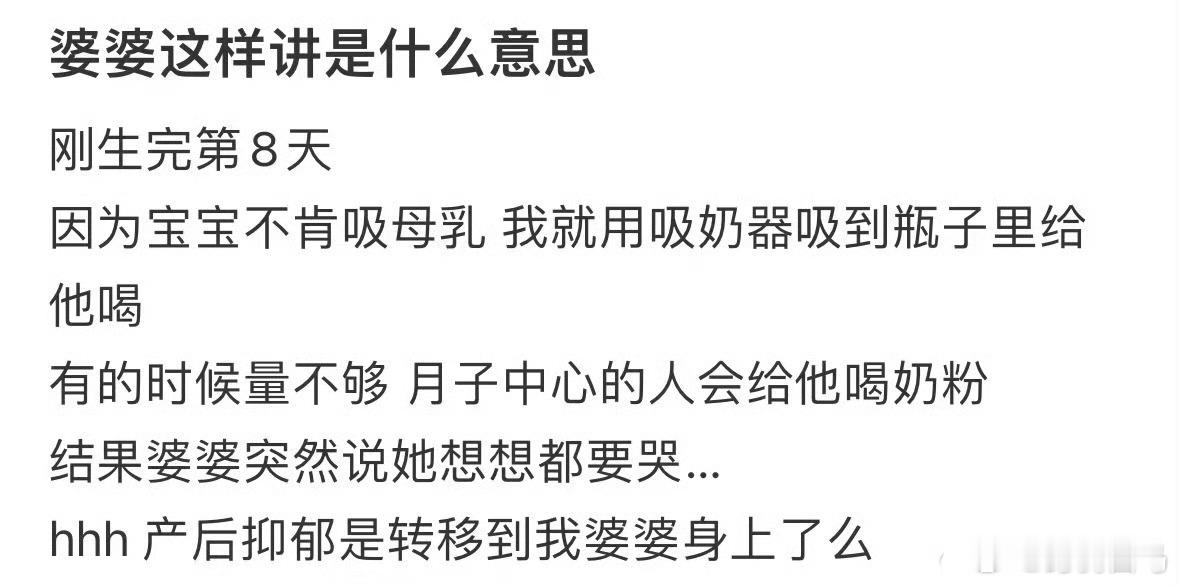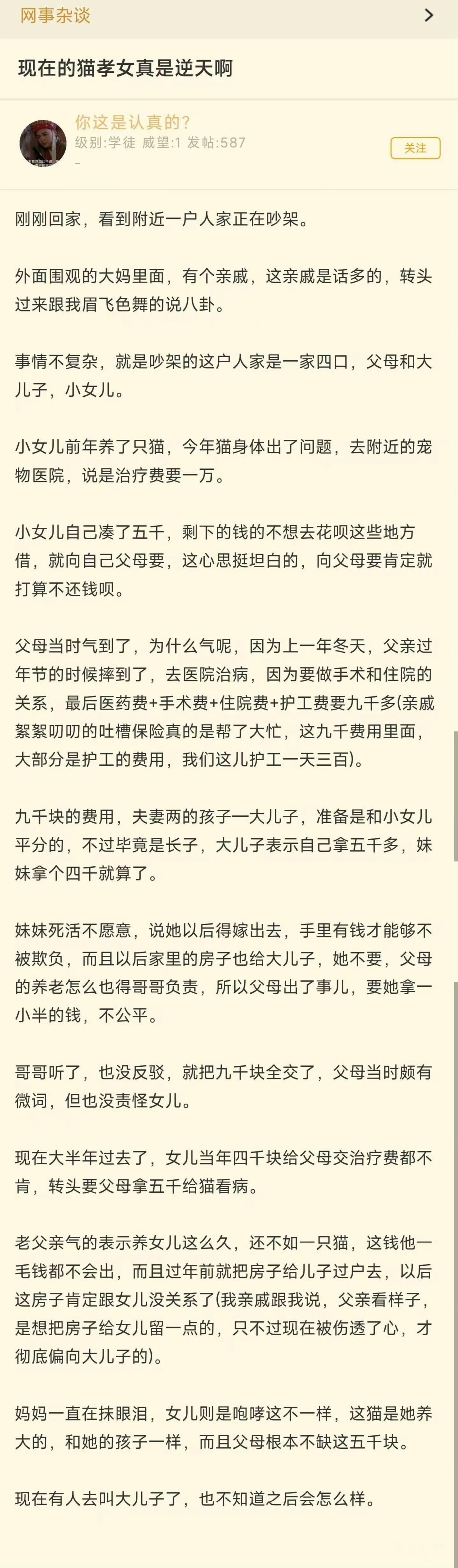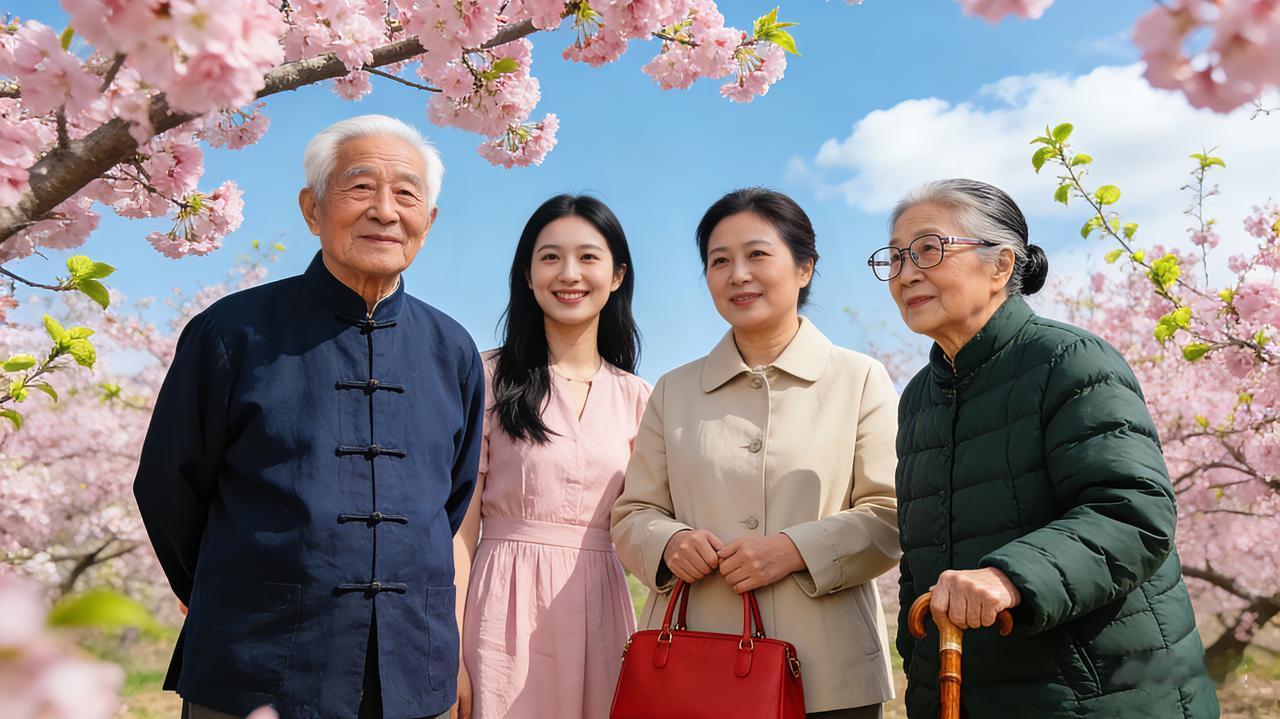昨晚,公公把收藏多年的物件一一摆放在桌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公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他说道:“你们俩是我最疼爱的孩子,这些东西平分,以后也能有个念想。”大姑姐语气不满的说道:“爸,你这分的可不公平。我嫁出去这么多年,为家里操的心可不少,凭什么和他一样?” 昨晚七点多,客厅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着,公公把樟木箱拖到茶几旁。 锁扣咔嗒一声弹开时,混着樟脑和岁月的味道漫过来——他蹲在地上,从箱底摸出个红布包,里面是用橡皮筋捆着的存折,边角都磨白了。 他把东西一件件摆开:黄铜怀表是年轻时修铁路得的,表盘蒙着层薄灰;粮票整整齐齐夹在旧报纸里,日期是三十多年前的;还有我结婚时他偷偷塞给我的银镯子,原来一直收在这里,内侧刻的小字被摩挲得发亮。 “你们俩,”公公手指在存折上顿了顿,指腹的老茧刮过纸面,“是我最疼的孩子。这些平分,以后日子难了,也算个念想。” 大姑姐刚端起茶杯,杯底在桌面上磕出脆响:“爸,这可不公平。” 她的指甲涂着酒红,在粮票上划了道印,“我嫁出去十五年,每年秋收回来帮着晒玉米,妈住院那三年,哪个周末不是我守夜?凭什么和他——”她瞥了眼我老公,“一样分?” 我捏了捏老公的手,想起去年大姑姐寄来的包裹,里面是给公公买的护膝,标签还没撕,她总说“顺手买的”;想起她结婚时,婆家给的彩礼,她偷偷拿了一半给家里盖偏房,这些事,公公或许忘了,或许觉得不必说。 大姑姐的声音发紧,尾音却扬着,像小时候抢糖吃时的倔强——她不是贪那些物件,是怕自己这些年的“操心”,在“嫁出去的女儿”这个身份里,轻得像没存在过。 公公的喉结动了动,没说话,只是把那只黄铜怀表往她那边推了推,表盖内侧,贴着张泛黄的小照片,是大姑姐十岁时的样子,扎着羊角辫,举着奖状。 那晚的物件最终没分,存折又被公公锁回樟木箱。 但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大姑姐在厨房帮公公热牛奶,杯沿碰了碰,谁也没提昨晚的话。 或许家人之间的账,从来不是“凭什么一样”,而是“原来你都记得”。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时刻,或许我该先问问她:“姐,那年妈住院,你是不是偷偷垫了医药费?” 樟木箱的锁扣又咔嗒响了一声,这次是公公自己锁的。 樟脑味还在,只是混进了点牛奶的甜香。 岁月的味道里,原来藏着的不是公平,是我们都没说出口的,疼。
昨晚,公公把收藏多年的物件一一摆放在桌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公攒了大半辈子的积
小依自强不息
2025-12-15 16:21:30
0
阅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