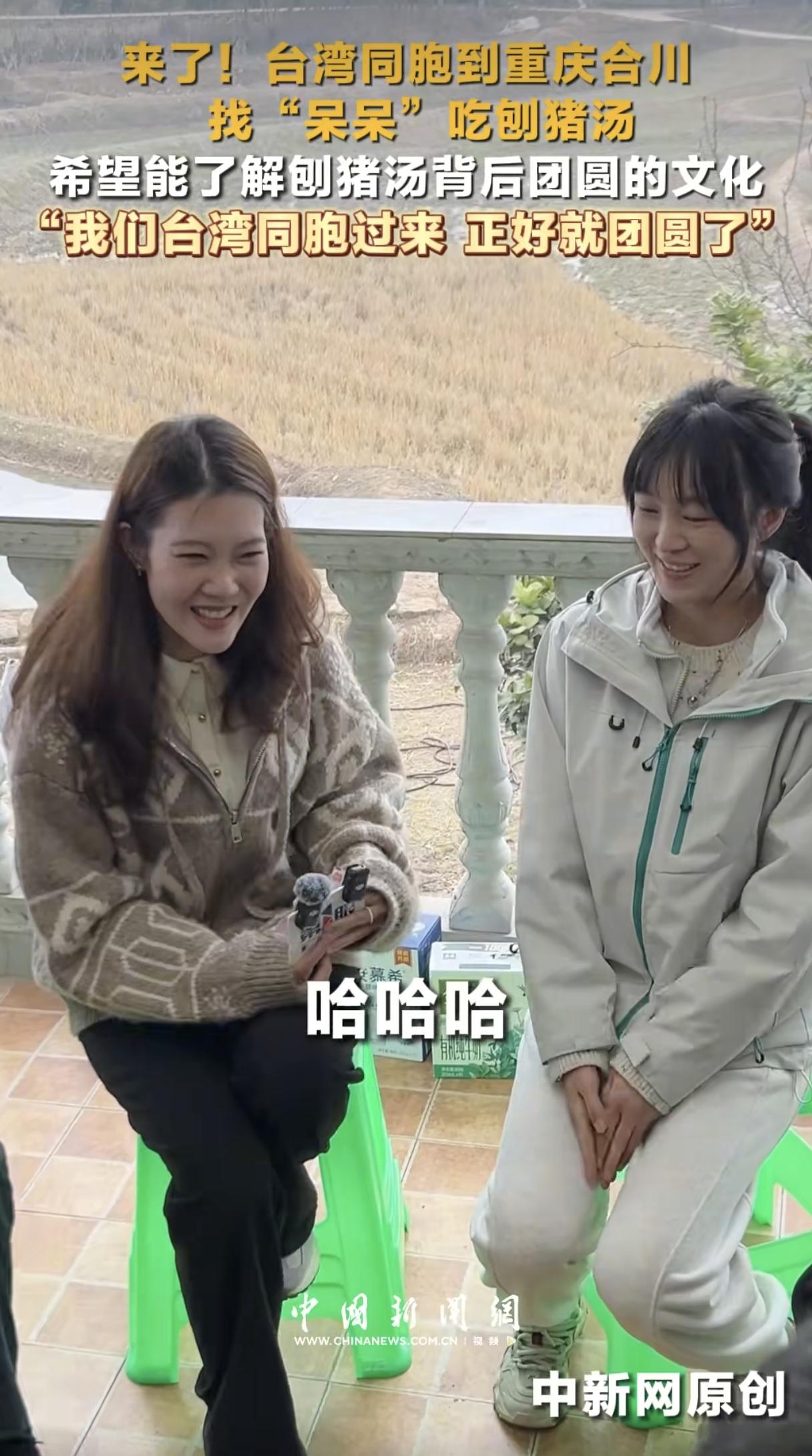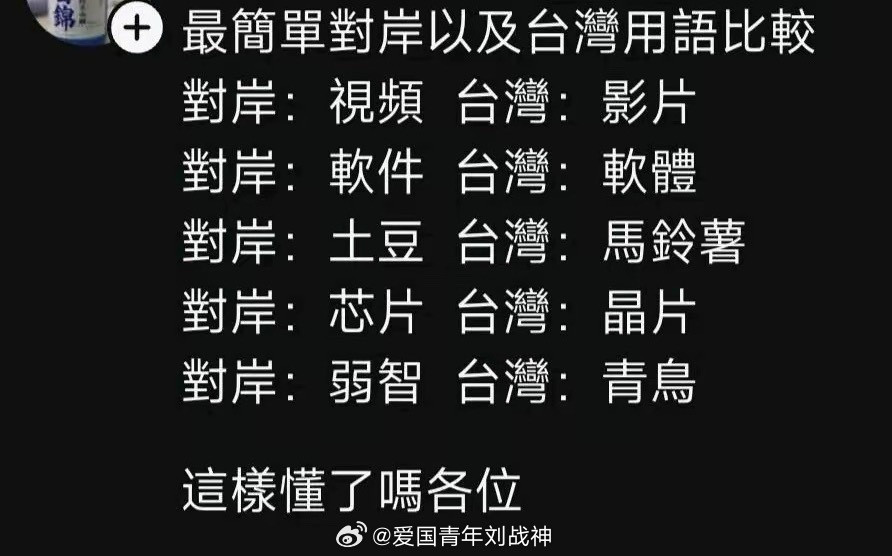刚才在火车上和邻座的一位台湾客人聊天,我问他台湾人愿不愿意回归祖国?他听到这话先是愣了一下,手里正剥橘子的动作顿了顿。 他把橘子放下,搓了搓手。车厢空调有点冷,他缩了缩肩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轻轻的:“我阿嬷去年走了,走之前,一直念叨着想回厦门的老房子看看。” 他从随身的旧背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布仔细包好的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叠用细绳捆好的信,信封都泛黄了。“这是阿嬷写的,每年一封,从1960年写到去年。收信地址都是厦门那个老门牌,虽然她知道寄不到。” 他抽出一封,信纸薄如蝉翼,字迹娟秀。“你看这封,1975年写的。她说‘妈妈,巷口的凤凰花该开了吧?我昨晚又梦到了。这里什么都好,就是没有那种红。’”他顿了顿,“阿嬷是厦门人,嫁到台湾第三年,两岸就断了音讯。她再也没见过自己的母亲。” 火车咣当咣当地响,窗外是模糊的夜色。他小心地抚平信纸上的折痕。“这些信,她从不邮寄,只是每年写,写完就收好。她说,等哪天通了,要亲手带回去,一封一封念给外婆听。”他苦笑了一下,“可惜,最后还是没等到。” “那这些信……”我问。 “这次就是去厦门。”他把信仔细收好,铁盒子扣上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老房子听说早拆了,原址建了公园。但我问过了,公园里正好有棵老凤凰木。我想去那儿,把这些信念一念,烧给阿嬷,也烧给从未谋面的外婆。”他看向窗外,玻璃映出他微红的眼眶,“阿嬷总说,她的根被风吹断了,飘到了对岸。但其实,根一直在那儿,没动过,是我们这头的枝桠,一直想弯回去。” 他没再说回归愿不愿意,只是收好铁盒,静静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零星灯火。后来他靠在椅背上,像是累了,手里紧紧握着那个盒子。 火车到站,他和我道别,背着那个旧背包,慢慢消失在出站的人流里。我想,他背包里装的,不是一个铁盒,而是一座等了太久太久、终于要回家的桥。
台湾同胞赴呆呆妹家吃刨猪汤,全村围播还光盘,这波温情太戳心刷到呆呆妹家的刨
【2评论】【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