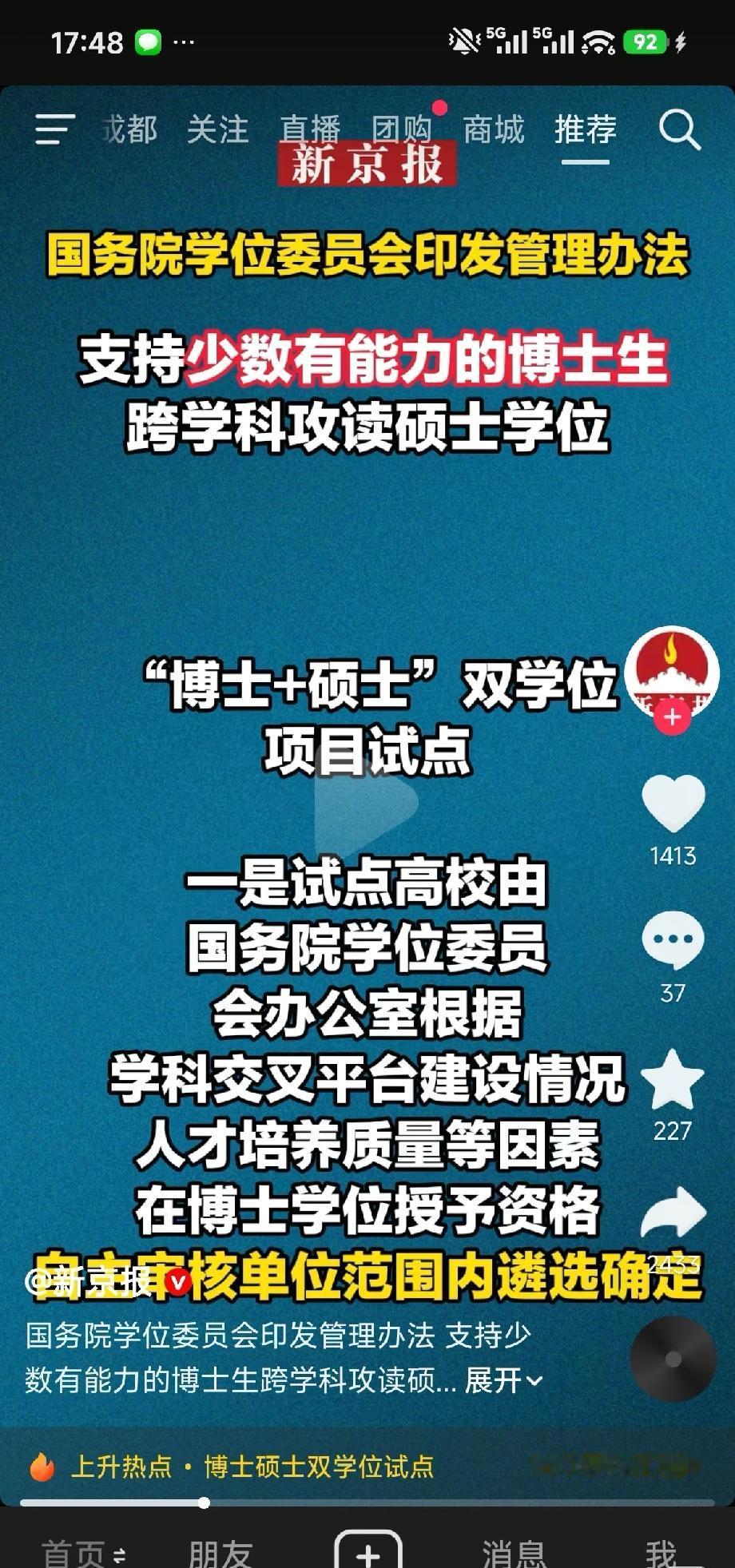我母亲的嘴巴,真紧啊。 那年我上初二,数学成绩像坐滑梯,一路往下出溜。 同桌有本《中考数学冲刺》,封皮都翻卷了,借我看了两页,例题讲得比老师还透。 放学路过镇上书店,我扒着玻璃门往里瞅,那本书端端立在书架第三层,标价三十八块——那会儿我爸在砖窑拉一天砖,才挣四十。 回家吃饭时,我扒拉着碗里的玉米糊糊,没话找话:“妈,我们班好多人都买辅导书了。” 母亲正给我夹咸菜,筷子顿了顿:“有用?” “嗯,例题可清楚了。”我声音越来越小,“就是……有点贵。” 母亲没接话,低头扒拉她的碗,筷子把碗底的米粒都扒拉干净了。 第二天早上,她塞给我五块钱:“中午在学校食堂买个馒头,别总啃凉红薯。” 我捏着那五块钱,心里有点堵——她准是没往心里去。 从那天起,母亲晚上总说去西头李婶家串门。 李婶家开小卖部,晚上总有人打麻将,母亲说去看热闹,其实我知道,她根本不爱凑那热闹。 有回我起夜,看见她屋里灯还亮着,门缝里漏出点光,像根细细的银线。 我踮着脚走过去,听见里面有“嗤啦嗤啦”的声音,像是布料摩擦。 刚想敲门,灯“咔嗒”灭了,母亲披着外套出来,看见我,吓了一跳:“咋不睡?” “妈,你咋还没睡?”我盯着她的手,她赶紧往袖子里缩了缩。 月光从院墙上爬过来,照见她右手食指缠着块白纱布,纱布角还沾着点红。 “缝被子呢,线结子勒手。”她拉着我往回走,脚步有点急,“快睡,明早还得上学。” 那之后,我发现母亲的顶针换了个新的——以前那个边缘都磨圆了,现在这个亮闪闪的,上面还有小花纹。 她晚上回来总带着股味道,不是李婶家的麻将牌味,是种淡淡的机油和线头烧焦的糊味。 过了大概一个月,那天我放学回家,刚放下书包,就看见桌上放着个塑料袋。 里面鼓鼓囊囊的,正是我在书店看中的那本《中考数学冲刺》,封皮崭新,还带着油墨香。 我拿着书跑出去,母亲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抡得高高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汗珠子亮晶晶的。 “妈!这书……” 她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把汗:“供销社张叔说,进书的车顺道拉来的,便宜了五块。” 我翻开书,扉页上贴着张纸条,写着“加油”,字歪歪扭扭的,像她平时记工分的字迹。 那天后半夜,我渴醒了,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手套缝完了,厂长今天结了工钱,正好够买书。” “手指还疼不?那天看你扎了下。” “没事,老毛病了,顶针磨得慌。” 我趴在被窝里,攥着那本书,书角硌得手心发烫。 后来我考上大学,有次回家整理旧物,在母亲的木箱底翻出个铁盒子。 里面装着她的顶针,就是那个带小花纹的,边缘已经磨得跟旧的一样圆了,上面还沾着几根线头,蓝的、灰的,像没说完的话。 盒子里还有张纸条,是村口小工厂的记工单,上面写着“王秀兰,缝手套280双,工钱140元”,日期正好是我买辅导书的前三天。 前阵子我带孩子回家,母亲正坐在炕头纳鞋底,顶针还是那个磨圆的,在她手指上转来转去。 孩子凑过去:“姥姥,你手指上戴的啥呀?” 母亲把顶针摘下来,套在孩子小手上:“这叫顶针,纳鞋底不扎手。” 我看着她手上的茧子,比顶针还硬,突然想起那本辅导书。 “妈,那时候你咋不跟我说,书钱是你缝手套攒的?” 她穿针引线,线在鞋底上钻了个洞:“跟你说啥?你那时候心思都在学习上,说了还让你分心。” 孩子拿着顶针跑了,母亲抬头看我,笑了笑:“再说,当妈的给娃做点事,还用人知道?”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纳了一半的鞋底上,针脚密密麻麻,像天上的星星。 我突然懂了,她的嘴紧,不是不会说,是把话都纳进了鞋底,缝进了手套,藏在了那本带着油墨香的辅导书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比说出来的,更沉,也更暖。
这一刻成绩已经不重要了!近日内蒙古通辽,老师正在办公室备课,突然听见楼道里同学说
【2评论】【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