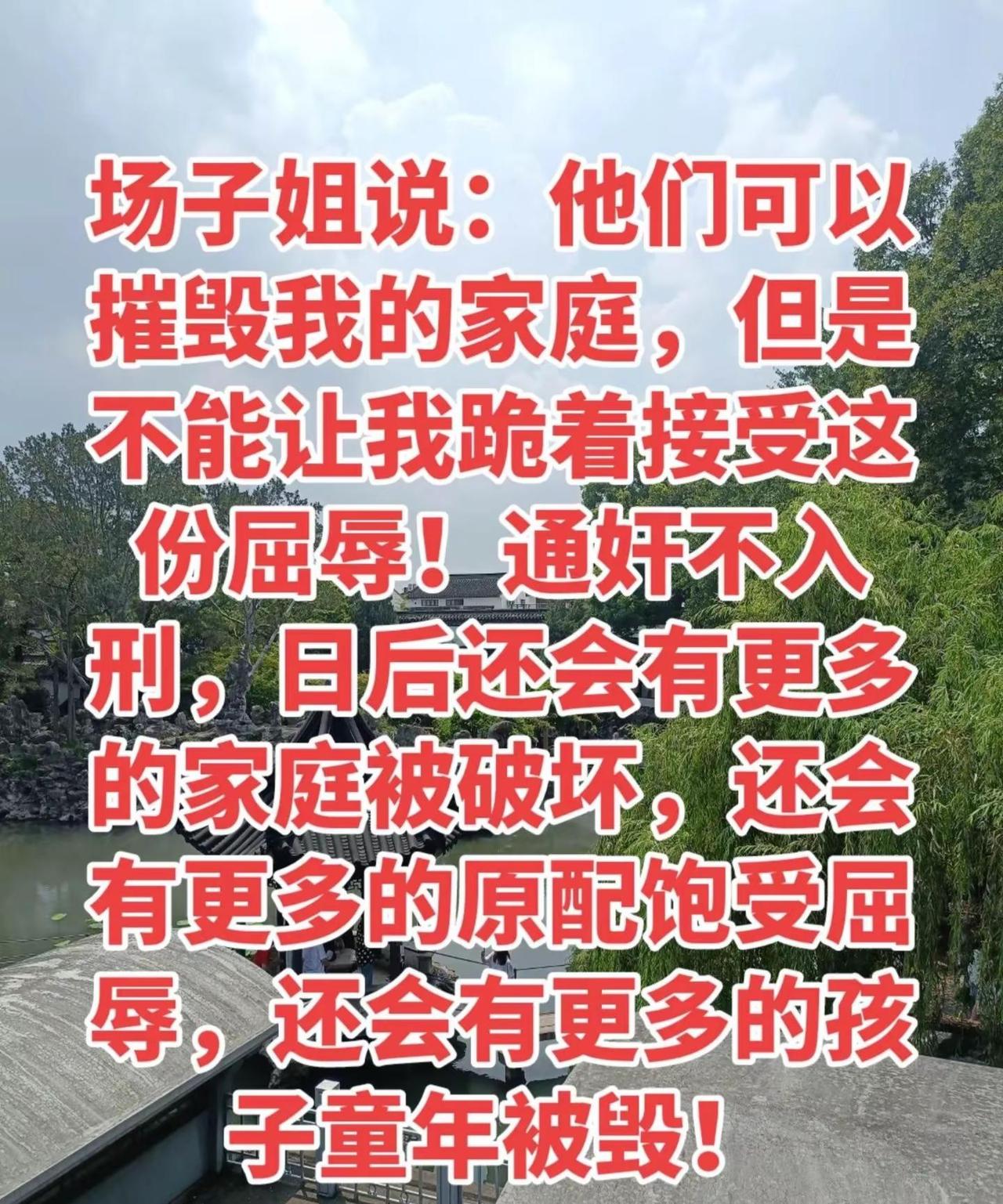86年我家条件很差,为了不做单身汉,和一个脸上有疤的女孩成家。那道疤从她左眉骨延伸到颧骨,像条暗红色的蚯蚓,媒人说“是小时候被开水烫的”。见面那天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埋得很低,手指绞着衣角,半天没说一句话。 86年的冬天特别冷,我家土坯房的窗户糊着旧报纸,风一吹就哗啦响——那时候我二十五,在村里算大龄光棍,媒人踏破门槛,说的却都是“要么带娃的寡妇,要么有点‘缺陷’的姑娘”。 她叫秀莲,脸上那道疤从左眉骨爬到颧骨,暗红的,像条没褪尽的印子,媒人叹着气说“小时候端热水锅烫的,命苦”。 第一次见她是在媒人家,她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蓝布都快变成月白色了,头埋得快抵到胸口,手指在衣角绞出三道褶子,我问“你叫秀莲?”她才蚊子似的“嗯”了一声。 婚事定得快,彩礼是两袋麦子和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我娘偷偷抹泪,说“委屈你了”,我倒没觉得委屈,只想着“总算有个家了”。 婚后头半年,我们没怎么说话。我下地干活,她在家做饭,晚上躺在一张炕上,中间能再躺个孩子。她做饭总多焖一碗饭,用布包好塞进我工具袋——我以为是她吃不完,直到有次我提前回家,看见她蹲在灶台边,就着咸菜啃凉红薯。 那年秋收我崴了脚,躺了半个月。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河沟捶衣裳,棒槌敲在石头上“砰砰”响,回来给我熬草药,药汤熬得浓黑,她自己先尝一口,烫得龇牙咧嘴才端给我,说“不烫了,喝吧”。 有天夜里我疼醒,看见她坐在炕沿,借着月光摸我的脚踝,手糙得像砂纸,指腹磨出好几个茧子,嘴里轻轻念“快点好起来吧,不然地谁种,麦子谁收”。 我以前总躲着看她的疤,觉得那是“不体面”的记号,可那天月光照在她脸上,疤的边缘竟然泛着点淡粉——后来才知道,她每天早上都用热毛巾敷那道疤,说“怕你看了心里膈应”。 当初点头结婚,不过是为了“不再打光棍”,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可后来我半夜发烧,她背着我走三里山路去卫生院,她才八十斤,我一百三十斤,她走一步喘三口气,却没放我下来,路边的荆棘刮破她的褂子,她也只顾着问“还疼不疼”——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日子过的不是脸,是心。 现在我们结婚三十七年了,秀莲的疤淡成了浅褐色,像片浅浅的云,孙子总爱用小手摸,说“奶奶脸上有朵软云彩”。 去年冬天整理老箱子,翻出她当年那件蓝布褂子,衣角的褶子还在,只是蓝布已经脆得一碰就掉渣,我摸着那三道褶子,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她时,她绞着衣角的样子——原来有些“不完美”,早就在岁月里,酿成了最暖的糖。 人这一辈子,别被眼睛骗了;那些看起来“有缺憾”的相遇,或许藏着老天爷偷偷塞给你的礼物呢。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内男孩,要娶国外女孩?
【1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