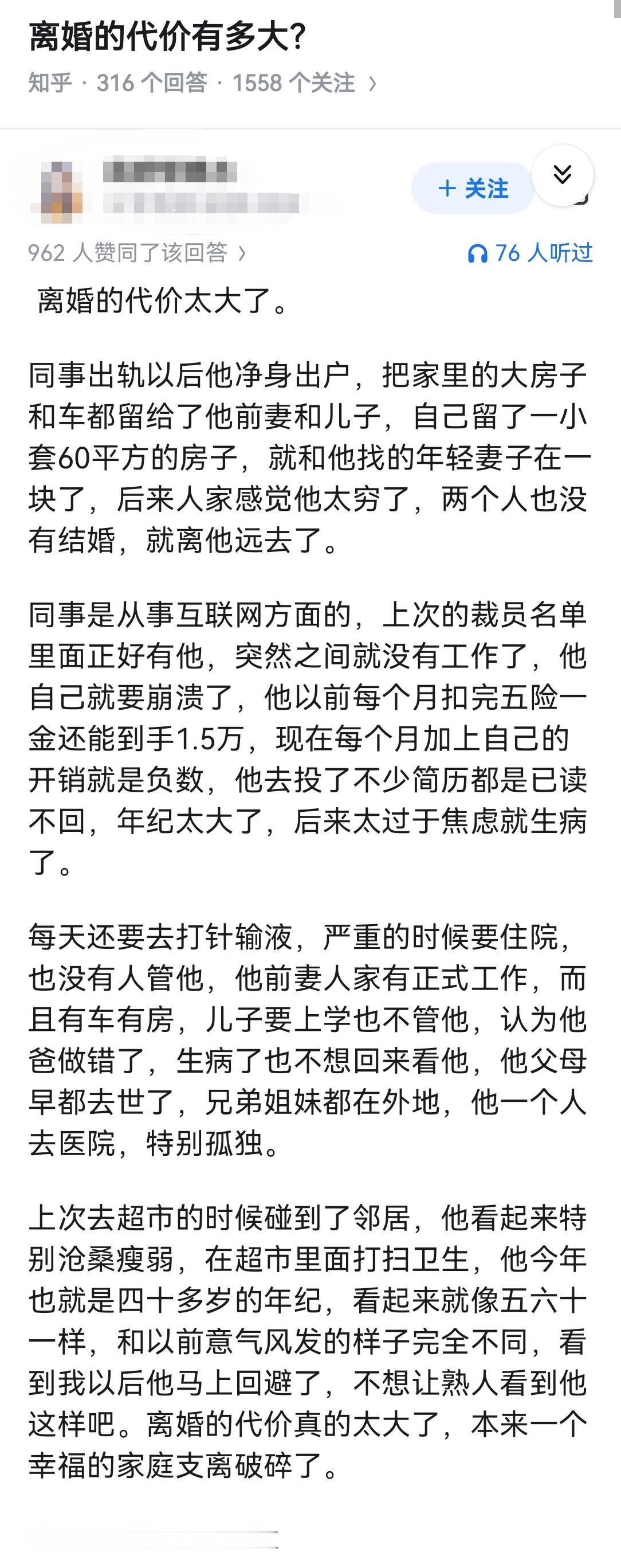女朋友比较纯洁,相识一年也止于接吻,终于有一次喝多了,住在了一起。第二天早上我是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的,宿醉的头疼得跟要炸开似的,我揉着太阳穴坐起来,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见她坐在床边,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凑过去:“怎么了这是?头疼吗?” 她猛地转过来,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床单角,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我妈说……说女孩子第一次要留到结婚,我现在是不是……” 和她在一起一年,牵手会脸红,拥抱要提前问,连亲吻都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她总说妈妈教的,女孩子要“矜贵”,界限感像透明的墙,我们都没敢碰。 直到上周部门聚餐,她被灌了两杯果酒,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却软在我怀里说“走不动了”,我没多想,把她带回了我的住处。 第二天醒时,宿醉的头疼像有小锤在敲太阳穴,我闭着眼摸手机,却听见床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不是穿衣服的声音,是布料摩擦着,混着细细的抽气声。 我心里一紧,猛地坐起来,看见她背对着我坐在床沿,睡衣领口皱着,肩膀一抽一抽的,像只受了惊的小兽。 “怎么了?”我声音还哑着,伸手想去碰她,她却猛地转过来——眼睛肿得像刚剥开的核桃,睫毛湿成一绺一绺,手里死死攥着床单的一角,指节都泛白了。 “我妈说……”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说第一次要留到结婚那天,要有红盖头,有仪式,还要……”她顿了顿,眼泪又掉下来,砸在床单上,“可我昨晚……我们是不是……我是不是不‘矜贵’了?” 我愣住了,看着她通红的眼睛,突然明白那堵“透明的墙”不是她胆小,是她把母亲的话当成了尺子,每一步都在量“对不对”——她怕的不是亲密,是自己“做错了”。 她攥着床单的手松了松,却还是低着头:“我妈说,不守住的女孩子,会被人轻看的。”这句话像根刺,扎得我心口发疼——她不是怀疑我,是在怀疑自己有没有“资格”被好好对待,所以她哭,不是后悔,是怕自己不再是那个“值得被珍惜”的姑娘了。 我没说话,只是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把她的手从床单上掰开,轻轻揉着她泛白的指节:“在我这儿,你永远是那个会因为牵手脸红的姑娘,和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没关系。” 后来她慢慢不哭了,靠在我肩上说“原来你不会觉得我‘随便’啊”,我才发现,所谓的“界限”,从来不是身体的距离,是心里的安全感。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时刻,别急着解释“没关系”,先抱抱她——告诉她,她的珍贵,和任何“第一次”都没关系。 现在她还是会在拥抱前问“可以吗”,但说完就主动把脸埋进我胸口,像只找到了树洞的小松鼠;那堵透明的墙还在,只是墙上开了扇窗,我们都能看见彼此眼里的光了。
女朋友比较纯洁,相识一年也止于接吻,终于有一次喝多了,住在了一起。第二天早上我是
嘉虹星星
2025-12-31 12:09:01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