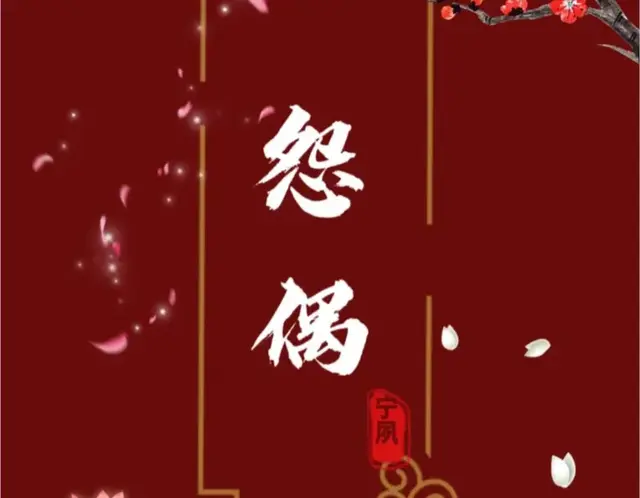《侯门夫妻重生后》
作者:起跃

简介:
白明霁及笄那年,晏家派媒人上门替世子晏长凌提亲,同是武将之后,也算门当户对,父母一口答应,她也满意。
十七岁白明霁嫁入晏家,新婚当夜刚被掀开盖头,边关便来了急报,晏长凌作为少将,奉命出征。
一年后,传回了死讯。
对于自己前世那位只曾见过一面,便惨死在边关的夫君,白明霁对他的评价是:空有一身拳脚,白长了一颗脑袋。
重生归来,看在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份上,白明霁打算帮他一把,把陷害他的那位友人先解决了。
至于害死自己一家的姨母,她不急,她要钝刀子割肉,她万般筹谋,等啊等啊,却等到了姨母跌入山崖尸骨无存的消息。
白明霁双目蹿火,“哪个混账东西动的手?!”
晏长凌十六岁时,便上了战场,手中长矛饮血无数,二十岁又娶了名动京城的白大姑娘,人生美满,从未想过自己会英年早逝。
枉死不甘,灵魂飘回到了府中,亲眼看到自己的结发妻子被人活活毒死。
重生归来,他打算先履行身为丈夫的责任,替她解决了姨母。
而自己的仇,他要慢慢来,查出当年真相,揪出那位出卖他的‘挚友’他一番运筹,还未行动,那人竟然先死了。
晏长凌眼冒金星,“谁杀的?”
得知真相,两人沉默相对,各自暗骂完对方后,双双失去了斗志。
晏长凌:重生的意义在哪儿?
白明霁:重生的意义到底在哪儿?
既然都回来了,总不能再下去,晏长凌先建议,“要不先留个后?”
白明霁同意。
就当晏长凌一心扑在了风花雪月上,自认为领悟到了重生的意义时,白明霁‘跌’入悬崖的姨母到了白家,昔日背叛他的那位‘友’人,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晏长凌:“......”玩我呢?
小剧场:
穷尽一身本领终于荡平一切,晏长陵如愿搂住了自己的夫人,本以为今生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风花雪月......
半夜突然被踢下床,“你闺女哭了,去哄一下。”
“你那好大儿,又把先生气走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二写的一手好字,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了,为人父,你总得管管。”
晏长陵:曾经有一段清闲人生摆在面前,我没珍惜......
“晏长陵!”
“来啦——”
精彩节选:
萧瑟穷秋,日犹长,外层两道凌花风门大敞,残霞金光蔓延至阶前,似轻烟的光芒里映照出一层薄薄绿荫苍苔来。
已记不清这院子有多久没来人了。
白明霁面朝庭院,盘腿坐于蒲团上,微抬手,三经绞罗绣花鸟的大袖垂至膝上,手中茶盏倾斜,水渍缓缓浸入金兽炉脊上的细密小孔,眼前笔直的一道袅袅青烟,很快没了踪影。
“我与晏侯爷说,归根结根我不过是外姓人,不该同晏家一道陪葬。”
“他答应了,给了放妻书。”
“姨母,我可以回家了。”
即便孟挽嫁入白家,成为父亲的继室已有半年,白明霁还是习惯叫她姨母。
她只有一个母亲。
便是她的生母,孟锦。
孟挽似乎从不介意,笑着道:“恭喜阿潋。”
丫鬟素商已收拾好东西,在车上等,孟挽没着急带她走,新泡了一盏茶,轻推给她,“晏家最后的一盏茶,尝尝吧。”
白明霁不擅于悲秋伤怀。
嫁入晏家一年,她从未与夫君晏长陵相处一日,对晏家并无感情,如今要走,没什么可留恋。
不仅是晏家,她对任何人或事皆是如此。
从不谈感情。
是以,每到抉择之时,她总能冷静地找到那条于自己而言,最为有利的道路。
这样的性子,彷佛天生。
三岁那年,父亲接回了他的青梅竹马,两年后,诞下了庶妹,她和母亲的处境逐渐艰难。
一个心里装着别的女人的丈夫,母亲觉得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但她认为并非如此。
这世间能永恒的东西,唯有利益。
她是白家名正言顺的嫡长女,母亲乃前太傅嫡出长女,父亲明媒正娶的夫人,凭什么要被旁人争了光芒?
为了替白家争光,她使出了浑身解数。
七岁时便能弹出一首完整的曲子。
十四岁时,一副丹青被刑部看中,雇她为官府画师。
十五岁及笄礼上,她又以无可挑剔的礼仪和一身好皮囊,从此名声大噪,博得了白太后的赞美和喜欢。
十七岁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永宁侯府世子,晏长陵。
她承担起了白家长女该有的模范榜样,成为了白家后辈中最为出彩的那一个。
她的努力,也如愿替她带来了收获。
姨娘离开白家那日,父亲曾在她屋里沉默地坐了一柱香,问她:“真不能容她?”
她答:“不能。”
她喜欢自己掌握命运。
瞧不起瞻前顾后的白云文,讨厌游手好闲的白星南。
看不惯白楚的软弱无能。
对一头栽进感情里的白明槿更是恨铁不成钢。
她一直认为自己才是活得最通透的那一个,直到某一日她回过头时,身后已寻不出一个认识的人。
如同眼前这条铺满了苔藓的台阶。
此时来接她回家的大抵也只有姨母一人了。
白明霁垂目,茶盏里飘浮起了一层青叶,轻轻吹开,送到嘴边饮了半盏,唤道:“姨母......”
她想问,她到底哪里做错了。
察觉出那样的问题,不是她这样的人应该问的,终究没能开口,问道:“阿槿还好吗。”
白明槿是她的同胞妹妹。
喜欢上了人人唾骂的刑部侍郎裴潺。
一月前两人大吵一架,至今没来,怕是还在生她的气。
“死了。”
孟挽轻淡的声音入耳,白明霁还未回过神,心口冷不防一股刺痛撕扯而来,似是没听清她的话,茫然看向孟挽。
孟挽并不着急,面上是一贯的微笑,“都死了。”
“你母亲死了,妹妹也死了,白家老夫人被你寒了心不愿再见你,你父亲视你为蛇蝎,护着你的白太后也已薨。”孟挽轻声问:“阿潋,你离开了晏家又能去哪儿呢?”
门外的金光一点一点地褪去。
震惊与疼痛交织,白明霁疼得额头冒出冷汗,便也明白了肺腑里的绞痛是什么,孟挽今日不是来接她回家的,是来要她命的。
母亲死后,待她最亲近的人只有这位亲姨母,当初为了助她嫁入白家,自己不惜与父亲决裂。
为何要来害她?
白明霁想不明白,忍着疼痛拽住她,眸子里血红如丝,质问道:“为何?”
孟挽被她拽得斜了身子,没有回答,而是从身后取出一个漆木盒子放在几上,打开盖,轻推到她面前,“你父亲给的,让我带话给你,你体面了一辈子,最后必然也想走得体面些。”
里面是一条白凌。
凉意渗进骨头,肺腑里的疼痛到了极限,白明霁竟也麻木了。
孟挽倾身过来,五指捏住她的下颚,将她的视线扭向院外,“知道白家为何没人来接你吗?”
白明霁心往下沉,彷佛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脸上的血色眼见往下退去。
“因为他们都厌恶你,恨不得你死。”
孟挽看到了她脸上闪过的一丝慌乱,满意地松开她,缓缓从她手中抽回衣袖,“你父亲身为兵部尚书,乃三品官阶,纳个妾却被自己的女儿闹得满城风雨,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
“你大义灭亲,带着大理寺的人上门指认白老夫人陷害了你母亲,逼得她从此不敢再踏出房门半步。”
“你气性高,瞧不起愚钝之人,白家两位公子被你踩在脚下,见到你都怕。”
“还有阿槿,就因为她喜欢的人,你不喜欢,便执意让她断绝情爱。”
“知道她怎么死的吗?”孟挽轻叹:“我不过是告诉她,以你阿姐的性子,怕是永远都不会妥协,她的人生容不得瑕疵,也容不得自己的亲人有半点瑕疵,不如我来做主,替她许了这门亲,昨日亲事定下来了,谁知她又自缢了,你说她到底为何不想活了?”
孟挽扫了一眼她苍白的脸,目露怜惜,“你以为是你拯救了白家,可白家上下实则视你为蛇蝎。你奋力往高处爬,以为会迎来他们对你的喝彩。”
“你错了,他们对你只有憎恶,晏家给你了一条活路,你就能活了?”
那一字一句无不刺耳,犹如一把把尖刀刺入心口,不断绞着她的五脏六腑,尖锐的嗡鸣几乎刺穿了耳朵,嘴角鲜血涌出来,白明霁抬手抹了一把,满手粘稠,目光中夹杂着被揭穿后的恐惧和恨意,浑浑噩噩地朝她扑去。
孟挽起身退开,看着她扑在一旁的木几上,几面上的一株松柏落下,碎片满地,无不狼狈。
孟挽又走上前,怜爱地摸着她的头,似往日那般温柔地同她道:“阿潋,你没错,错的是他们。”
“我也没错。”
“瞧你,每一步都走对了,不一样落得个举目无亲的下场。”
“潋潋,这样活着真的幸福吗?”
那样的神色充满了溺爱与怜悯,就像母亲死的那一日,孟挽来到灵堂,将她搂进怀里,对她说,“我知道潋潋心里苦,潋潋不怕,有姨母在。”
脑袋里看着跟前这张被水雾模糊的脸,脑袋突然一团混乱,逐渐成了空白,唇瓣轻颤,苦痛地道:“我不知道......”
孟挽一笑,“你知道,很痛。”
“当年你母亲也很痛苦。”
“你们下不了手,姨母来帮你们一把。”
凌乱的思绪从混沌中一瞬炸开,白明霁慢慢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盯着她,喉咙里的嗓音几近嘶哑,“是你杀的母亲?”
孟挽不乐意了,“是你们自己走到了绝路,关我何事?”
“你们这样的人,没有心,眼中永远只有利益,下场不是早就注定了?”
“你母亲当年同说我,她活得很痛苦。”
“既然痛苦,不如死了,我成全了她......”
孟挽的声音忽近忽远,白明霁喘不过气来。
幸不幸福,她不知道,她未曾有过,并不在乎,但有一样孟挽说得没错,她没有心,谁都别想从她身上讨到好。
锋利的瓷片划破掌心,用尽最后的力气,她将那块破碎的瓷片刺进孟挽的颈子后,自己也倒在了地上,仰头往外望去,最后一眼入目,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腹部的疼痛慢慢地变得迟钝,眼睛一阵阵发黑,耳边声音传来,她已辨不清是孟挽在挣扎,还是从门口灌进来的风声。
她拼了一辈子。
还是没能得到善终。
她想保护的人,也一个都不在了。
圣贤人道:尽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她这般孤魂野鬼,应该入不了轮回。
—
昨夜一场骤雨起,狂风卷着闷雷响了半宿,今晨刚住点。
“上月来信,说是走水路,白家的船只都到扬州了,又改成了马车,这一路上车轮子撵着稀泥走,不存心折腾人......”
一阵细风穿透窗纱,漠漠轻寒拂向临窗人的脸颊,白明霁扭回头,便对上了一双敢怒不敢言的怨怼目光。
说话的人正是白家那位游手好闲的二公子白星南。
一触到白明霁的视线,白星南立马缩了脖子,四下里一张望,见马车内就他们两人,脊背顿时挺直,防备地看着她,“我已满十五,高你一个头了,你若再敢以暴力服人,我可要还手了。”
白明霁一笑,“你哪回没还手?”
“是你不讲武德,老揪我头发。”
“你没揪?”
白星南不乐意了,“谁有你豁得出去,自小打架回回拼命,非得赢了才算......”
“你倒是拼点命,也不至于连童试都没过。”
脚下的马车一顿,应到了城门,白明霁没再搭理他,拂开窗帘,瞧去窗外。
几日阴霾后,久违的日头似水洗过般穿透翠柳,初阳浇枝,叶面残珠如露,入眼满目芳华。
当下确乃惊蛰时节。
剧毒断肠之时,她瞧得清楚,庭外碧云天,黄叶地,是个穷秋。
虽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她没死,几日前醒来,自己又回到了半年前。
孟挽还未嫁入白家。
今日才进城。
白星南极为不愿跟她走这一趟,“孟氏成过一回亲的人了,来我白家是为大伯续弦,用得着我这白家的二公子来接......要说我,这事压根儿就不该你管,你已经是晏家少奶奶了,晏长陵不在家,你又不用相夫教子,闲来时养点花花草草,过个轻松日子不好吗,非要回来盐吃萝卜淡操心......”
白明霁撩起帘子往下跳。
白向南嘴里嘟嘟囔囔,跟着下了马车,两人一前一后走去城门口的茶馆。
惊蛰的天气乍暖还寒,白星南双手套入袖筒内,一到茶馆卯腰便往屋里钻,“太冷了,先喝盏热茶。”进去后没见人跟进来,又探出个脑袋,唤了一声,“长姐......”
白明霁已背过身,面朝着城门,婀娜的身姿立在茶馆门前的青石阶上,青丝垂于身后,腰间处的水蓝发带随着裙裾迎风飞扬,身影纹丝不动。
“客官,几位?”
他才不会陪她受冻,白星南转过头,“两盏茶,做好了,给门外那位姑娘送一盏去。”
小二一笑,“好呢,不就是晏家少奶奶嘛,名动京城的白家大娘子,小的认识......”
白明霁等了好几日,只为今日。
她要再杀一次孟挽。
好好清算,慢慢杀。
候了半柱香,头顶的日头越来越淡,隐约飘起了零星雨点。
听到身后有脚步声,白明霁以为是白星南,待人走到跟前,脚步便主动往对方的伞底下靠了过去。
手肘相碰,一股清淡墨香入鼻,白明霁诧异地转过头。
来人并非白星南。
而是大理寺少卿岳梁。
前世母亲死后,为了证明是被人害死,她不惜挖坟开棺,大半夜跑去岳府砸门,愣是把岳梁从被窝里拉了出来。
尤记得那晚岳梁站在棺材前,脸色黑如锅底,后来许是被她缠得没了脾气,一来二去,倒也成了半个知己。
前世死之前,才见过他,不算陌生。
冷风刮来,雨点往里倾斜,岳梁把伞往她头顶移了移,侧目问:“等人?”
白明霁点头,“嗯。”
雷雨天,城门口的人并不多,能躲的都进了屋,站在外面的只有他们两人,莎莎雨声中岳梁低声道:“令堂的案子,白老夫人与白尚书均没有确切的作案证据。”
母亲的死,前世她一直怀疑是祖母和父亲所为,如今既知道了凶手是谁,白明霁便道:“多谢大人,往后母亲的案子,不必再查了。”
岳梁眉宇间正泛出几丝疑惑,“驾——”城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
两匹快马疾驰而来,进了城门,也不见半点减慢的痕迹,很快踏进两人跟前的水坑,泥水爆开,瞬间四溅,岳梁一只手握住她半边肩膀,下意识挡了过去。
白明霁从他怀里抬头望去,面色带着微愠,视线正好与前面那匹马背上的人对上。
是一张意气风发的少年脸。
身上和脸上染了些泥水,称得上狼狈,但那双眼睛看人时赤|裸张扬,眼底的锋芒暴露无遗,如同一只从长空直下,俯视而来的鹰隼。
白明霁没见过此人。
见岳梁被泥水几乎浇污了半边身子,再看着那扬长而去的马尾,眉头蹙起,“粗俗。”
这话引得一旁面色本还怔愣的岳梁,回过头来,怀疑地看着她,“你,不认识他?”
白明霁不明白他为何这么问。
她应该认识?
没等岳梁解释,城门外又是一阵打马声。
这回马匹还没到两人跟前便停了下来。
马背上的小厮翻身而下,快步走到白明霁跟前,神色慌张,拱手禀报道:“娘子不好了,这几日落雨,山路湿滑,昨儿半夜,孟娘子的马车跌入了山崖......”
两匹快骑疾驰入城,一路扬起泥水,到了闹市方才减缓。
虽落雨,京城最繁华的前门长街人群依旧熙熙攘攘,周青光夹紧马肚与前面少年并肩,对适才一幕印象深刻,扬声调侃道:“没想到半年过去,京城世风竟如此开放,连岳少卿这样的人,也能铁树开花,当街与小娘子搂搂抱抱了。”
“少管闲事。”
细雨沾湿了发冠,少年面上的泥土也被冲刷干净,肤色白皙,泠泠水渍贴在面上,如同白玉镶了一层流光。
先前眸中的那道锋芒早已敛去,宽大的朱红斗篷铺在身后,眉目间的英气随着他唇角的舒展,散出几分浑然天成的傲慢贵态来。
阴霾天里,乍一瞧,不觉让人眼前一亮。
少年勒住缰绳,停在一家酒铺前,从怀里掏出一粒碎银,抛向撑开的直棂窗扇内,“两坛桃花酿,纯的。”
雨天铺子前竖着的一根桅杆上悬着一盏白纱灯笼,阴沉的天光下折射出一圈明黄的光芒,待卖酒的老板看清跟前少年的脸后,惊呼道,“晏世子?”
“前线的仗打完了?”这可是京城里的名人,酒铺老板探出大半个头,摆出一副要与其畅谈的热情,“大宣将士是不是跪地求饶了?”
人人都喜欢听痛打落水狗的故事,本国将士一旦出征,百姓恨不得敌军是纸糊成的,一刺就穿,一推就倒。
晏长陵没应,坐在马背上半弯下腰,微微上扬的唇瓣勾出一道明朗的笑容,“这酒好卖吗?”
“小本买卖罢了,还过得去,不敢劳世子费心。”
“安心卖你的酒,家国战事,也不用你来操心。”说完手中长矛探去铺子,勾住绳子挑起了两坛子酒,夹马继续往前,直奔侯府。
晏家乃皇室宗亲,又因父辈立下过汗马功劳,门第显赫,府门乃一扇朱漆将军门,枋与柱相连,额枋上竖着一块牌匾。
牌匾上的“晏府”二字,乃晏家老王爷当年亲手所写。
落雨的缘故此时府门紧闭,周青光扣了五六下门环,里头才传来动静。
见到门外两人时,门房一脸震惊,怀疑自己看错了,“世子回来了?!怎的没提前传信,奴才这就去通报老爷......”
晏长陵一脚跨入门槛,“不必,父亲在哪里,我自己过去。”
门房快步跟在他身后,“惊蛰天雷雨不停,今日陛下免了早朝,庄子的人趁暴雨前摘了几框橘子,这会子人都在老夫人院子里聚着呢......”
晏长陵将手里的酒坛子递给了身后的周青光,脚步直径朝老夫人的梧桐院走去。
七进的院落飞檐连廊,以花格栏杆作装饰,棂条上雕刻着繁琐的云纹和灯笼框纹,一直延绵到正屋门外。
步上廊内,隐隐的说话声从窗格内渗出,“世袭官职没了,今后再好的出身,想要入仕都得科考,外头百姓放着烟花爆竹庆祝,直呼万岁,我晏家却被架在了火炉子上被人盯着烤,一句不能依靠祖荫,害得老二别说实职,在京城连个挂名都捞不到,沦落到了要做地方官的境地,只怕赴任那天,便是全京城最大的笑话......”
官职改革,得有牺牲。
皇室宗亲,不愁饿不死,就算什么都不用做,也能领俸禄过日子。
可之后呢?
便是再也起不来了。
“荫不及族人,谁还愿意继续卖命......”
“慎言!”
便是在这片刻的安静中,外屋的丫鬟忽然唤了一声,“世子爷。”
屋内几人一愣,齐齐朝帘门望去。
老夫人上了年纪畏寒,三月了屋里还烤着火盆,晏长凌抬手掀起卷帘,碳火的温暖馨香扑面而来,与记忆里那场萧瑟血腥的画面截然不同。
“世子?”
“云横!”
“你怎么回来了?”
晏长陵拱手一一见礼,“祖母,父亲,二伯二婶,三婶......”
进屋前,他已整理了一番仪容,此时对着众人牵唇一笑,笑出了风光霁月的俊态,可不就是昔日那副招人眼的风流模样。
还真是世子。
屋内的人终于从惊愕中回过神,争先问候,屋里的丫鬟一通忙乎,备座的备座,沏茶的沏茶,晏长陵上前靠着老夫人身侧入了座。
等所有人寒暄完,一旁的晏侯爷晏尘阙才皱眉问:“仗打完了?”
“尚未。”晏长陵答得倒是干脆。
晏侯爷眉头皱得更深,未等他再开口,老夫人便出声打断,“天下的仗能打得完?如今官场动荡,这时候回来正好......”
半刻不到,府邸上下全都知道了晏家的世子回来的消息,屋里的小辈们也一窝蜂的涌来了梧桐院。
十几个高登坐得满满当当。
都是熟悉的面孔。
晏长凌扫了一圈,没见到一个陌生的。
在他这一眼寻望中,晏老夫人也终于想了起来,屋子里少了一个人,转头问:“少奶奶呢?”
边上的一位丫鬟过来垂目回禀:“今晨一早,说是有要事回白家去了。”
又回白家。
晏二夫人忍不住插话,“能有什么要事,用得着她天天往娘家跑,世子都回来了,还不去寻?”
自从侯夫人去世后,府上的事务皆是晏二夫人帮衬着老夫人在打理,上回在那新妇跟前吃了个闭门羹后,已好几个月没管过,也不知道成什么样,转头吩咐身旁另一位仆妇,“你去竹院走一趟,盯着人早些把院子收拾出来,好让世子先回去更衣......”
—
白家。
城外的消息一传回来,二房的嬷嬷伞都顾不上撑,湿着两边肩头,一踏入屋内便急切地禀报:“二爷二夫人,出事了。”
今日白家上下原本就紧绷着一根弦,一听这话,白二夫人心跳都快了,“怎么,真遇上了?”
上月白家大夫人的杖期已过,白家大爷也到了该续弦的时候。
人选定了两人。
一位是白大夫人的妹妹,也就是白明霁的亲姨母,孟挽。
一位则是曾被白明霁亲手赶出白家的阮姨娘。
姐姐去了,由妹妹来填房,京城之内的大户人家并非没有先例,但耐不住阮姨娘是白大爷心中的遗憾和求而不得。
好不容易熬到了正牌夫人生死,终于能将受了委屈的旧人重新迎入门,眼里怎能容得下旁人。
且那孟挽还嫁过人,死了丈夫。
白明霁今日来接孟挽的同时,白大爷也正在迎回阮姨娘的路上。
但孟挽也并非没有成算。
若白明霁能赶在阮姨娘进门之前,先一步将孟挽接进白家,再去宫中求白太后做主,就算白大爷接回阮姨娘也没用。
两厢里都在较着劲,这要是回来的路途中忽然碰上,会发生什么,简直不敢想。
嬷嬷却道:“孟家娘子的马车翻了!”
“什么?!”二夫人惊得站起身来,回头看向白二爷,两人均是一怔。
嬷嬷继续道:“雨天路滑,路不好走,那孟娘子又心急走了近道,马车翻在了九岭坡,连人带车跌进了悬崖......”
白二夫人深吸一口凉气,好半晌才回过神,“大娘子人呢?”
“倒是立马赶过去了,还能如何,十几丈高的山崖,孟娘子已是尸骨无存。”
好端端的人,突然死了。
这就是命啊。
二夫人捏着绢帕,又慢慢地坐了回去。
白二爷皱着眉,思忖片刻,起身便往外走。
白二夫人一把将他拉住,“你去哪儿?”
“人都出事了,总得去瞧瞧。”
白二夫人更不能让他走了,“人没了,你去瞧有何用?本就是他们父女间的较量,你掺和进去,站谁?一个帮的不好,里外都不是人......”回头吩咐嬷嬷,“把门关上,就说二爷昨儿个喝多了,我看顾着。”
等到白明霁从城门赶回来,整个白府已是鸦雀无声。
别说主子了,偌大的院子连个仆人都看不见。
白星南躲在了她十步之外,恨不得也能遁了,听说孟挽出了事后,他大气都不敢出,被白明霁拖着去了一趟城外,亲眼看到了马车翻滚的痕迹后,更是看都不敢看她一眼。
自己这位长姐从小要强,想做的事没有一件不如愿,头一回见她失利,还是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可谓是满盘皆输。
要她那样傲娇的人,对着昔日被自己赶出去的姨娘叫母亲......
白星南打了个寒颤,不敢往下想。
偷偷窥了她一眼,见其面色紧绷,着实不敢招惹,赶紧差身旁小厮去传人,很快小厮回来了,头垂到了胸口,“老夫人头疼犯了,还在歇着呢。”
“父亲母亲呢?”
“二爷昨夜喝了一宿的酒,早上才回来,二夫人正在伺候汤药......”
白星南不死心,又问:“大公子呢?”
“在屋里悬,悬梁椎骨。”
白星南:......
平时读书怎没见他如此用功。
本还想问二娘子白明槿呢,及时想起来,半月前,因她私自外出去看刑部裴潺,被身旁这位长姐禁了足,还在关着禁闭。
合着丢了他一人在这儿受死。
欲哭无泪地扭过头,眼里那抹生不如死突然被一双清透的眸子捕捉到,白星南心头一跳,便听白明霁问:“我很可怕?”
白星南腿都软了,“长姐,我向你保证,就算大伯明儿真把阮姨娘接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承认她身份,更不会叫她一声伯母......”
白明霁没说话,唇角努力动了动,“没事。”这几日她已经尽量在笑了,“你回屋吧。”
话音一落,白星南脚底如同抹了油。
那弓腰驼背的样,毫无半点志气可言,心绪忽然一阵翻涌,‘废物’二字在脑中破土而出,白明霁眼睫轻颤,一口气从城门外憋在了如今,唇角压了又扬,扬了又压,起伏几回,终究还是暴露了情绪的波动。
“站住。”白明霁忽然道。
白星南脊背一僵。
“你去同他们传个话,门既然要关,就关得结实点,别不该开的时候他又打开了,那样会让我觉得是在故意针对我。”周围更安静了,白明霁扫了一眼角落里露出来的几方衣角,淡声道:“既知道我脾气不好,就别招惹。”
好好说话,见人就笑,不好意思,她真不是那块料。
纵然这辈子依旧举目无亲,不得好死,她也改不了了,就这样吧,破罐子破摔,总算舒坦了,转过身跨出门槛,也不用勉强挤出笑容,烦躁的心绪索性挂在了脸上,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孟挽死了。
与前世完全不一样,不觉让她怀疑,这醒来的人生到底还是不是上辈子。
醒来后这几日她一直在等着孟挽,如今人说没就没,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正犹豫要不要去找白太后,借些人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转过身,却见晏二夫人跟前的老嬷嬷,脚底生风般朝她疾步而来,迎面就道:“少奶奶,赶紧回吧,世子爷回来了。”
谁?
脑子里的茫然和怒意还未完全退去,白明霁一时没反应过来,脱口而出,“哪个世子爷。”
传话的嬷嬷一愣,僵硬地笑了笑,“少奶奶这话问的,还能有哪个世子爷,您的夫君,晏世子回来了。”
她的夫君。
永宁侯府世子,晏长陵。
回来了?
一个本该半年后死在战场的人?白明霁思绪彻底乱了,讶然地盯着嬷嬷。
嬷嬷见她这反应顿时一噎,先前听二夫人背地里数落,说她莫不是她忘记自己已嫁了人,如今瞧来,还真给忘记了。
走过去一把搀扶住她胳膊,待扶上马车后,便立在窗前板着脸道:“有几句话,少奶奶或许不爱听,老婆子今日也非得说了,少奶奶已是出嫁的人了,别动不动就往娘家跑,这不得体,先前便也罢了,如今世子爷已回来,还望少奶奶往后谨记自己的身份,论起规矩,少奶奶还是京城姑娘们的楷模呢......”
这话多少带着揶揄。
上辈子在晏家住了一年,白明霁参加过的家宴,一个巴掌都能数过来。
夫君不在,她顶多算半个晏家媳妇。
与晏家人的相处,主打一个井水不犯河水。
至于不相干的人,她懒得费神。
放在往日,尽管晏家有人对她这番目中无人的行为看不顺眼,但奈何理亏,嫁过来就让人家守了空房,加之她身后的那位白太后,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如今世子回来了,总算有人治她了。
怀揣着这般心思,嬷嬷今儿要叮嘱的话格外多,到了晏家,等白明霁从马车上一下来,张嬷嬷便跟在她身后继续说教,“院子里的奴才,原本是伺候世子的人,纵然一时不合少奶奶心意,好歹也是十来年的老人了,少奶奶不该将人撵了。”
言下之意,如今人回来了,我瞧你怎么交差。
见白明霁一句不吭,张嬷嬷心中暗自感慨,这人啊,万不能太傲,总有栽跟头的时候。
想起先前她一副天灵盖上长眼睛的样,如今倒是巴不得这关头上闹出个事情来,好让世子瞧瞧,娶的是尊什么样的菩萨。
盼什么来什么,两人的脚步刚上竹院长廊,便听见里面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隐约能听出是白明霁跟前的金秋姑姑。
张嬷嬷心头一跳,这也太灵了,眼睛里生了光,嘴里却装模作样地道:“有什么天大事还值得吵一番,也不瞧瞧今儿是什么日子。”
脚步不觉走到了白明霁前头,到了人群背后,双手往胸前一叠呵斥道:“这又是怎么了?”
二夫人刚派过来的姚姑姑被拦在门外,也不知道金秋说了什么,气得她脸颊发红,回头见是张嬷嬷,这下有了底气,声音也大了,“嬷嬷来得正好,您给评评理,今儿世子爷回来,二夫人好心让咱们的人过来帮忙打扫,谁料这门前多了一道门神,把咱们拦在外,不让进了。”
张嬷嬷听明白了。
什么样的主子养什么样的奴才,又是老一套。
上回被撵的几个奴才告到二夫人跟前,二夫人好心好意找上门来调解,白氏以头疼要歇息为由,让二夫人吃了个闭门羹。
张嬷嬷把目光看向了金秋姑姑,也不指望她能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放人进去。
果然金秋姑姑道:“别说是张嬷嬷,今日就算二夫人来了,这赶出去的奴才,岂有再请回来的道理。”
说的是姚姑姑身后的一位丫鬟。
那丫鬟原本是屋里伺候世子爷茶水的人,名唤玉珠,人是机灵,但话太多,白明霁喜欢清净,便把她调去了后厨。
后厨婆子多,适合她唠嗑。
但她不愿意,跪在白明霁跟前哭,问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与其被她这般羞辱,不如放她走。
本以为她是世子的人,白明霁不敢处置,谁知白明霁竟成全她,当场把牙行的人叫了过来,玉珠吓得大哭求饶,二夫人听到消息把人拦住,暂且收在了自己屋里。
今日八成是听说了世子回来的消息,打了要来诉说冤屈的主意。
金秋姑姑死活不放人,几人便端着水盆,拿着扫帚堵在门口。
张嬷嬷一听金秋姑姑如此说,转过身便对刚下长廊的白明霁,嘴角扯出个无奈的笑容来,“奴才无能,还是少奶奶处理吧。”
众人这才瞧见刚下穿堂的白明霁。
个个脸色微变,垂目往后退。
众所皆知,这位少奶奶不好惹,旁的主子动了怒,摔个东西骂上一顿便也罢了,她不是,但凡被她抓到错处,那便甭想再呆在院子里了,一次机会也不会给。
玉珠不久前才领教过。
鼓起勇气抬头,便见白明霁正冷眼盯住她,“你还有话说?”
触到她目光,玉珠心头便是一跳,脖子又缩了回去。
换做往日她确实不敢再来,今日不同,有人替他撑腰,硬着头皮冲出去跪在了院子中央,摆出一副要升堂伸冤的架势,同她叫嚣:“奴婢不服。”
金秋姑姑没见过这等子死皮赖脸的,倒吸一口凉气,“这会子天晴,能跪了。”
然而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她能说得过姚姑姑,却没玉珠的口才,反倒被玉珠蛇缠棍子缠上了,“奴婢知道姑姑读过书,说起话来走路绕小道,总要拐个弯,殊不知这墨水喝到了肚子里,五脏也被染了色,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我技不如人,没有姑姑一根筷子拣花生米的本事,这才惹了少奶奶不快,要来发落奴婢。”
一顿夹枪带炮,说金秋姑姑挑拨了。
有了上回的教训,玉珠明白当奴才的万不能同主子对着干,这回学聪明了,把矛头对准了白明霁的陪嫁姑姑身上。
“你!”
金秋姑姑气结。
当初就因为这点,娘子才容不得她。
抬眸看向白明霁,见其一身占了雨雾,没功夫同她掰扯,“娘子先回屋更衣,她愿意跪着就跪着吧。”
若是上辈子,白明霁或许会杀鸡儆猴。
重生回来,她背负着血海深仇,定不是来管这些鸡毛蒜皮之事,这屋子的主人既然已回来了,该如何处置随他。
正要进屋,那玉珠竟不依不饶了,大声哭喊起来,“奴婢跪着无妨,只等少奶奶消气,今儿就算是跪死,奴婢也认,奴婢生是竹院的人,死是竹院的魂。”
最后两句抬高了声音,竟叫得比烈妇还贞。
白明霁转过身,倒好奇她哪里来的底气,一道清朗的声音突然从对面廊下的卷帘内传来,“谁要死了?”
惊蛰雨水缠绵,檐下装上了一排厚重竹篾卷帘,挡了雨雾也挡住了视线,待细风过,吹得帘子起伏,里面那道影影绰绰的身影在一众人的注视下快步走了出来。
是位年轻公子,青色剑袖圆领袍,手握一把银枪,从踏跺潇洒踱步而下,举手投足一股少年将士的干练,五官却不似武将的粗矿,白皙精致,唇角的一抹笑彷佛天生。
有些熟悉。
白明霁愣了愣,不就是打马溅了岳梁一身泥水的那人。
没等她反应,跪在院子里的玉珠如同见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梨花带雨般地哭诉,“世子爷,求世子爷替奴婢做主......”
白明霁又怔了怔。
实则她并没见过晏长陵,新婚当夜她头上的盖头刚被掀开,门外便来了宫人,等她抬头时,只看到了一个匆匆离去的背影。
边沙之地,竟能养出这样的细皮嫩肉。
倒不是小白脸。
少年的阳刚之气洋溢在了脸上。
四目交汇还能感受到他视线里散出来的灼热,一双黑眸澄明深邃,似是在星海里浸泡过,含着笑漫不经心从一众人身上扫过,略过她时突然一顿,似乎城门口的那一眼,也没将她认出来,是以,又在她身上多停留了一阵。
她一身妆花金线绫罗,气势自与下人不同,此时能站在他房门前,什么身份不言而喻。
晏长陵自然也看了出来。
新婚夜记不清有没有见过白氏,似是瞧过,又没瞧过,印象模糊,即便是前世最后一眼,她脸上沾了鲜血,也没看真切。
这回倒是瞧仔细了。
肩上披着的还是适才在城门口见到的那件披风,肩膀有些消瘦,显得身姿格外婀娜窈窕,头上发丝被雨水打湿,沾了云烟。
时下京城文人颇多,但凡长相过得去的小娘子,都被称为美人儿,大多美人儿在于皮相和点缀,瞧过之后则了无痕,记不清长相,跟前的姑娘不同,本身就是一块美玉,不需要过分的雕琢,沉静中流露出来的清雅从容,倒让人过目不忘。
确定自己之前是没见过。
隔了两世头一回相见,比起城门前见到的那一幕,对她上辈子那般凄惨的结局更有感触,含笑对她点了下头。
对方俯身还了他一礼。
耳边的呜咽哭声还在继续,晏长陵这才垂目看向脚边跪着的那位奴婢,问道:“你哭什么?”
嗓音偏低沉,听进人耳朵,像是被一汪暖暖的泉水包裹,玉珠愈发委屈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像是向家长告状的孩子,巴巴地等着主子替自己做主,“世子爷,少奶奶要撵奴婢走,还打发了牙子要将奴婢卖了......”
只要跟过晏长陵的人,谁都知道他护短。
晏长陵如她所愿地往白明霁的位置看去。
白明霁面色坦然,也没反驳半句。
晏长陵又回过头问玉珠:“何故撵你?”
“奴婢,奴婢冤枉......”
“什么冤屈,说来听听。”院子里有一方石桌,之前他喜欢在这里与客人下棋,如今一场雨,上面铺满了落叶,横竖身上湿了,没去顾上面的水渍,往石凳上一坐,手中银枪靠桌竖着。
张嬷嬷心头激动,忙同姚姑姑递了个眼色。
姚姑姑会意,这是要清理门户了,忙领着带来的丫鬟出了院子,跨出门槛后,话里有话地道:“今日青天老爷在,谁还能有冤屈?”
在竹院有冤屈的,不就那几个被白明霁赶出来的奴才。
深院里围墙一围,四四方方也算得上一座小城,有点热闹,谁也不想错过,赶紧找人传话。
院子内玉珠也意识到自己今日占了上风,人跪在晏长陵跟前,妙语连珠,“奴婢也不知到底哪里得罪了少奶奶,思来想去,估摸着许是世子爷那套茶具少奶奶想换,奴婢一时糊涂,护了两嘴......”
金秋姑姑喉咙里‘嘶’出一声,“你那是护了两嘴,十嘴都算少的了,你是如何说的你忘了?你......”
“奴婢伺候了世子爷五年。”玉珠一声打断她,膝行几步,拖着哭腔道:“世子爷人不在,奴婢想着屋里总得留点之前的东西,好有个念想,少奶奶不爱听,还要把奴婢给卖了,若非二夫人那日拦了下来,奴婢,奴婢早就,奴婢不活了......”说着要起身去撞树,被边上的婆子拉住,众人七嘴八舌相劝,好不热闹。
很久没这么被吵过了,白明霁眼皮子两跳,头偏向一边,正想回避,前面石凳上坐着的人,忽然回头,朝她望来,“不过来听?”
白明霁抬头时,他已收回视线,从袖筒内掏出了块干爽的帕子,递给旁边的侍卫,“水擦干,让少奶奶坐。”
确定他唤的是自己,白明霁走了过去。
见她乖乖地坐在世子爷身旁,闹腾的玉珠终于安静了下来,摆出一副不是自己非要找事,而是被逼无奈的委屈状,“若是奴婢一人,奴婢倒也觉得是自个儿不是,可院子里的人少奶奶换了大半,奴婢着实,着实想不明白......”
晏长陵颇有耐心地听她说,“还有谁冤屈了?”
话音一落,外面一串仓促的脚步声回应了他,三五个小厮接二连三同玉珠跪成了一团,齐声喊冤,“世子爷,求世子爷替小的做主......”
白明霁对这几人有点印象。
半夜出去赌钱,被她回来撞上,第二日一早便让他们收拾东西滚蛋。
冤,哪里来的冤?
但人不是他的,晏长陵要想叫回来,她没意见,“我......”
几人却没给她发话的机会,“世子爷,奴才伺候世子爷十年了,从未有过差池......”
“小的替世子爷养了阿俊六年,也不知奴才走后,旁人有没有好好待它,奴才对不住世子爷......”
“世子爷......”
好吵。
白明霁讨厌哄哄闹闹,一吵头便疼,指甲不自觉想去扣东西。
“奴才做得不好,愿意受罚,求世子爷不要赶奴才走......”
“求世子爷.....”
满院子的喊冤,一声赛过一声,白明霁都快把膝上的一缕金线扣出来了。
“世子爷......”
眉心突突两跳,白明霁忍无可忍,压在心口的怒火说爆就爆,手边上正好有个趁手的家伙事,抄起搁在石桌旁的那把银枪,起身,脱手一扔,“砰——”银枪稳稳当当地插进了几人身后的榕树枝干上,憋着的一口气她全使了出来,力道不小,银枪的尾巴“呼呼——”一阵摇晃。
连着落了几日的雨,树枝上积满了水,哗啦啦落下来,跪下的几人被淋了个落汤鸡。
可算都闭嘴了。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白明霁也终于吐出了那口气,“吵什么吵!”
耳边死寂般的安静。
怒气慢慢散去,回过神待看清对面树上定着的是什么东西后,白明霁心下一凉。
她听说过那杆银枪的来历,乃皇帝当年登基时,亲自所赐。
十六岁时便伴着他勇闯沙场,几年下来,饮血无数。
眼眸轻轻往边上转去,余光瞥见一道目光正盯着自己,便也没那个必要再去来个对视。
谁也没说话,等着她自己收场。
扔了人家的枪,总得捡回来。
白明霁一边往树下走,一边义正言辞地道:“再吵就卖了!”
可扔的时候没掌握好高度。
伸手够是够到了,但使不上力,一下没拔动。
又使劲,还是没动。
再拔下来,只会更难看。
白明霁迫使自己回头,迎上对面那道黑沉沉的目光,平静地道:“是我为难他们吗?当奴才得有当奴才的样,主子回来,不伺候更衣,反而来伸冤,这算哪门子的忠心。”
脚尖一挪,又道:“我去替世子叫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