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阶上》
作者:尤四姐

精彩节选:
直房里的油灯,总是不怎么亮,每隔一刻钟须得剔剔灯芯。遇上一点风吹草动,那一星火旗就噗噗作跳,命悬一线般。
引珠放轻手脚,把打好的袼褙搁在桌上。她惦记了好久的新鞋终于完成了第一步,今晚先切了底子,明天夜里就能包边了。
手里的大剪子使劲绞,绞得指腹几乎磨出水泡,边绞边咬牙切齿抱怨:“今儿永寿宫把衣裳退回来了,你知道吧?要说这金娘娘,可真够难伺候的,好容易挑出来的珊瑚锦,绣上了牡丹带,我打量富贵得很,人家愣是瞧不上。”
坐在桌前画消寒图的人依旧低着头,仔细在白纸上打好格子。眼看要冬至,入了一九,就该盼着春来到了。消寒图上的每一笔,都是个崭新的盼头。
不过宫里有定规,比方说“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那是主子们的消遣。皇上的养心殿里都挂着这样的字眼,当差奴婢们的直房里,得换一种说法儿。于是换成“春前庭柏,风送香盈室”,听上去一样的意境,和主子们错开了,就不犯忌讳了。
可惜板画房那些势利眼,不愿意给他们这些人专门印制,要想消寒,得自己动手画。内官监这一片,就数如约的字写得好,因此年前二十张的定例,必要她来完成。画完了送到内织染局、尚衣监等衙门,不为别的,就为讨个好儿,混个脸熟,将来办起事来也方便。
引珠自顾自嘟囔完了,没听见她应声,回头瞧了她一眼,“嗳,明早怕是又要送到你那里去了。”
如约含糊说好,没往心里去,招得引珠摇头,“他们就是欺负你没脾气,什么麻烦活儿都找你。要是换了我,早和张太监闹了。”
引珠的抱不平,自有她的道理,后宫的主子们只管挑剔,不知道她们针线上的苦恼。
就说镶滚,有镂花、缝带、如意镶等,衣身居十之六,镶条居十之四。加上珊瑚锦本来就细软,要想拆改得花大力气,稍有不慎拆坏了,整件衣裳就糟蹋了。
永寿宫娘娘的拆改,全凭她的兴致,阖宫数她最麻烦。有时候并不真嫌衣裳不入眼,就是心境不顺,刻意找麻烦。
这一挑刺不要紧,苦的是针工局的人。起先她们还挨数落,到后来掌司太监弄明白原委,也就不多言了。大不了叹口气,耷拉着眉毛抬抬手指,干活儿吧。
和上头的主子论长短,谁有那个胆儿!
如约收起笔墨,含笑说:“不打紧,我那头的差事都办得差不多了,正好得闲。”
引珠张了张嘴,大概有些怒其不争,最后还是把话咽回去了,赌气道:“你得闲,得闲就来帮我纳鞋底吧。”
随口的一句排揎,竟果真把她招来了。她套上顶针,顺手给袼褙包起了边。
所以一个人太过任劳任怨,到底好不好呢?魏如约,针工局出了名的老好人,她踏实勤勉,就算吃了亏也不抱怨。活儿是比别人多干了许多,但要论人缘,着实没人能比她更好,算是有得有失吧。
“金娘娘的袄裙要拆改,我明晚怕是腾不出空来,你先做好了圈底,后儿夜里我帮你一起纳底子。
她说着,用力扥了扥棉线。就是那一扬手,一段洁白的腕子从袖底探出来,那份纤细、那份玲珑,饶是个女人,也要被她迷住了。
引珠犹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打从心底里发出的赞叹。读书不多的人,没有精致的词汇来形容她的美,唯知道一点,这姑娘说不出的齐全与体面,体面到与她的来历格格不入,不像是市井人家出身。
大邺朝宫女的采选,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官员进献,一种是民间采选。官员进献的,通常都是有背景有身份的,做宫人至多不过两三个月就晋了官女子,不再从事粗活儿累活儿了。剩下她们这种,家里老子做教书先生或是屠户的都有,引珠的爹就是泥瓦匠。打听了如约的来历,说祖上做过小官,后来半道没落了,靠着祖产做些买卖。商户人家,虽比他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强些,但进了宫除非大把使银子,否则断乎爬不上去。只能窝在这针工局,受太监驱使,没日没夜干活儿。
宫女不该太出挑,就该一眼看上去灰蒙蒙地,这叫本分。以前引珠安于这种本分,心底里认为平凡是因为欠缺打扮,只要插上花,年轻姑娘有几个不娇媚!可自从见到如约,这种想法被彻底打破了,人家明明也是同样一身素袍子,为什么就能透出不争不抢的优雅从容来?
那天引珠盯着她研究了好一会儿,最终认明白一点,面孔身条儿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长得丑的,捧着龙肉都像送牢饭的;长得漂亮的,就算提着恭桶,也像提花篮。
叹口气,摸了摸面皮,长相是爹娘给的,改变不了,可以学一学人家的性子。但如约的性子也不易学,这份大肚能容,比宰相还豁达三分。你要跟她一样,得拿出吃亏是福的精神头来,引珠自问心胸狭窄,断乎做不到。
好在运气不错,和她分到一个直房里。原本是四人一间的,另两个调到别处当差,床位就空了出来。仗着如约的好人缘,上头的掌司太监没再往她们这里填人。总是住得舒服点儿吧,四个人腾挪不开,两个人正好。
白天忙得脚不沾地,到了夜里回直房,才略略品出一点短暂的岁月静好。两个人一边做针线,一边闲谈职上的事由,忽然听见外面吵嚷起来,引珠嘴里说着“不会哪处走水了吧”,跳起来便推窗朝外张望。
如约手上的活儿没停,针扎进白布里,稳稳当当,分毫不乱。
只听引珠和经过的人打探,“出什么事儿了?”
路过的小宫女高兴得过节一样,“狗头灯死在水井房里啦。”
所谓的狗头灯,是司礼监随堂邓荣,脸上时时挂着假笑,一双眼睛贼溜溜,分外注意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宫女。照着引珠的话说,被他瞧一眼,像被扒光了似的,这人就该瞎、该死!
如今真的死了,宫人们个个透着高兴,一得消息就跑出去查看。内官监不在宫内,在紫禁城东北那一片,虽也是高墙阻隔,但规矩较之宫里松散多了。晚间各道门大多不落锁,毕竟要防着随时领差事,因此出了点事大可奔走相告,赶过去瞧热闹。
引珠打了鸡血一样,回身对如约说:“咱们也瞧瞧去。”
如约摇了摇头,“死人有什么好看的,怪吓人的。”
正因为害怕,不敢一个人去,才要找个伴。
引珠上来强拽她,“走吧,走吧,远远看一眼就回来。这狗头灯,谁不盼着他死,上回还偷着掐娟儿的屁股呢。这回可是老天爷开眼,不去啐口唾沫,对不住自己。”
如约没办法,只好被她拽着走。大晚上黑灯瞎火的,走得高一脚低一脚,好不容易穿过了巾帽局夹道,那个水井房就在皮房边上。还没进院子,就看见人头攒动,想是主事太监还没来,能容闲杂人等旁观。
引珠简直像个改锥,一点缝隙就能钻进去。她领着如约挤到了最里边,什么远远瞧一眼,早就不算数了,实打实看了个仔细。只见几个火者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硬把人从井口拽上来。死沉死沉的尸首,扑通一声扔在地上,像个灌满了水的皮口袋,周围的青砖转眼就被浸湿了。
有人惊叹:“哟,真是他!昨儿下半晌就找不见人,原来上这儿受用来了。”
好在是冬天,一昼夜了还没发臭,不过人给泡得发白发胀了,据说敲冰还费了不少劲儿,点了火折子往下扔,才看清楚长相。
死透了的人,面目显然和平常不一样,引珠这会儿有点怕了,往后退了半步,“怪瘆人的哩。”
看看如约,她不声不响地,胆子却挺大。出神地盯着死人看了好一会儿,看得引珠直发毛,拽了拽她的袖子道:“别瞧啦,仔细夜里做噩梦。”
如约那双眼,这才从狗头灯身上移开,语气似乎还有些遗憾,“好好的,怎么没了呢。”
司礼监忽然死了随堂,这不是小事,人打捞上来不多久,秉笔太监金自明就带着手下办事的过来了。
水井房一周点了火把子,照得黑夜亮如白昼。跳跃的火光晕染了那些妆缎织就的蟒袍,为首的秉笔往前踱了两步,蹙着眉,掖着鼻,万分嫌弃地认了尸,这才对底下人发话:“清场,严查。怎么死的,查个明白。”
底下人说是,很快扬手吆喝起来,“散了,散了!”又责问最先到的火者,“怎么办的差事,招了这么些人过来!这一圈还有一片没踩过的地方吗,脚踪儿全踩没了。”
火者畏畏缩缩辩解,“曹爷,哪儿拦得住啊……”
金自明不耐烦,扫视了凑做堆的人群一眼,那道声线又冷又硬,“还磨蹭什么?”
这下子谁也不敢拖延了,眨眼作鸟兽散。
引珠拉着如约回到直房,抚胸道:“那个金太监,比躺在地上那位还要吓人。”
那是自然,死了的还能跳起来打人吗?活着的才叫厉害,保不齐就能把你折腾个半死。
景山以北这一片,都由司礼监做主,秉笔又是司礼监有头有脸的人物,进得了内阁、批得了红,别说在内官监吆五喝六了。
如约收拾了桌上的东西,招呼引珠,“时候不早了,快歇吧,回头见咱们屋亮着灯,又来敲门。”
引珠赶紧把鞋样子夹进书里,脱了衣裳爬上床,扭身吹灭了案头的油灯。
躺下睡不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她:“你说狗头灯怎么会死在井里?是自己掉进去的?还是被人塞进去的?”
窗口有淡淡的月光照进来,照出如约的侧影,那双眼睛在黑暗中也有微光,淡声说不知道,“衙门里人多,利害牵扯也多,死上个把人,早就不稀奇了。”
引珠对狗头灯的下场拍手称快,“那王八蛋,死得不冤枉。我瞧他这阵子总借故找你,还怕他打你的主意呢。这回好了,死了就安心了,你也少受点罪。”
月华在如约的唇角勾勒出一道上仰的光影,她的言语依旧轻描淡写,“都是职上的往来,他吩咐我办事,我听差遣领命。”
引珠嗤笑了声,“你呀,就是不爱把人往坏处想。”
脑筋简单些倒也好,简单了没烦恼,就不用胡乱琢磨了。
外面还在喧闹,脚步顿地,咚咚直响。
引珠翻了个身,心道多大点事,死了个狗头灯,司礼监跟炸了窝似的,明天老爷儿不是照样升起来吗。
反正和针工局不相干,还是琢磨琢磨,永寿宫那两件衣裳怎么拆改吧!
盘金满绣、牡丹带,还有金白鬼子栏杆,这些镶滚的花样做成之后很漂亮,但那些安享尊荣的主子们,不知道缝制过程多费心思。
如今要拆,拆比做更难十倍。针工局的人是宁愿做十件新的,也不愿意返工一件,遇上这种活儿,能躲就躲,但都躲了,谁来干呢,活儿自然落到了如约身上。
如约也不算新人了,前年采选进来,来了就没挪过窝。照说两年时间,够熬出个小姑姑来了,但她不欺负新人,从不把手上的活儿分派给小宫人。金娘娘的衣裳到了她手里,她二话不说,坐在窗前拿细剪子,一点一点挑出线头来。
今天天气很好,局子里的值房没有大房檐,用的都是支摘窗。拿棍子撑起来,日光透过回字心屉,横平竖直地洒满南炕。炕桌上搁着个笸箩,里头放置各样的针线工具,笸箩旁还有一只粗陶的杯盏。内官监都是做下等活儿的,所用的器具自然也是最次一等。杯盏的盏底画了朵蓝色的花,下笔粗陋斑驳,一眼看上去,分辨不清是梅还是莲。
日光在小小的杯盏中跳跃,一片光斑投影在如约的额角,像个金箔制成的闹蛾。她总是沉得下心来,再繁复的活计都听不见她抱怨。
引珠不忍心她一个人忙,自告奋勇来搭手,可惜没什么耐性,一会儿叹口气,一会儿又大声咳嗽,到最后终于喊起来:“这可怎么拆,缎子都拆出洞来了!”
身在针工局,每天得重复同样枯燥的活儿,宫里的宫眷内臣们,都是按着日子换衣裳的。比如腊月二十四祭灶后换葫芦景补子,正月十五换灯景补子,三月初四换罗衣、四月初四换纱衣……每一次更换,都是一场浩大的战事,她们得提前几个月就开始预备,这还不算金娘娘这类莫名多出来的活计。
如约已经习惯了这种忙碌,听见引珠抱怨,只道:“你那儿不也有差事要忙吗,去瞧瞧白绫袄预备得怎么样了吧。”
所谓的白绫袄,是正月十六的行头。宫里也有这样的习俗,出了阁的女子上身穿白,下着蓝裙,十六夜里结伴出游摸门钉,一则消百病,二则宜生男。究竟管不管用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个说头,总得应个景儿。
引珠实在没耐性了,站起身嘟囔:“我这眼睛不成了,一样东西盯久了犯重影,别不是要瞎吧。”
如约笑起来,“这么就瞎了,针工局不得瞎一大片吗。”
这里正打趣,忽然见一个太监打起了门帘,夹带进一阵刺骨的寒风,高声招呼着:“魏姑娘,司礼监传你去一趟。”
引珠和如约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引珠急着问:“传她做什么呀?是为了邓爷的事儿吗?我们和邓爷没什么往来,让她去,她也交代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司礼监的回事太监虽照过面,但没什么交情,也套问不出什么内情。语气里有些不耐烦,掖着手道:“我就是个传话的,和我说这些,实在犯不上。”
引珠讨了个没趣,悻悻然撇撇嘴。转头又去看如约,眼神里满是担忧。
如约安抚她,“没什么要紧,问几句话就放回来了。”
引珠呆呆地点头,但谁都知道司礼监是龙潭虎穴,里头的太监坏得很。万一查不出原委,随便找个替死鬼顶缸,那如约岂不是要倒大霉吗。
担心归担心,终究是束手无策,只好把人送出门,千叮咛万嘱咐:“可要留神回话。”
如约让她放心,跟着回事太监走了。司礼监就和针工局隔着一条夹道,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去处。顶级的太监衙门门头高大,里头来往的,全是穿锦缎蟒衣的人。如约进门,见几个随堂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说话,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了眼,又若无其事咬他们的耳朵去了。
上首的秉笔太监正喝茶,慢条斯理地进了块点心,这才抽出空来问话:“是魏姑娘吗?”
如约肃了肃,说正是,“不知金爷传奴婢来,有什么示下?”
金自明倒是一副寻常样貌,语调甚至带着温存,盖上了盖碗道:“咱家领命侦查邓荣死因,但凡和他有过交集的,一一都要传来问话。你别怕,走个过场,据实回明就完了。照着仵作的勘验,邓荣是前日午时前后落水的,魏姑娘,前日午时,你在哪里?忙些什么?”
如约俯了俯身道:“回金爷,局子里午时是饭点。奴婢用饭大约两刻,用过了饭,正有一批补子赶制,就回值房了。”
金自明点点头,“可有人能为你作证啊?”
如约想了想道:“每日午时三刻,尚衣监分发贡线。那天我手上的金丝线恰好用完了,就去尚衣监补领了丝线。”
她也算对答如流,且有理有据,没什么破绽。但金自明却听说了别的传闻,探究道:“邓荣这人,出了名的不安分,针工局的姑娘,个个对他敢怒不敢言,我都知道。昨夜加紧走访,据说他近来单独见了你两回,究竟是什么缘故,姑娘能同我说说吗?”
这种时候,为了撇清关系说假话,反倒是不明智的。司礼监供职的都是人精,既然问你,必定是已经打听明白了。
秉笔这话一问出口,那些闲谈的随堂都回过身来。缺了嘴的茶壶,对这种事情最是感兴趣,就算是旁听,都显得饶有兴致。
如约敛了敛神,脸上流露出一丝难堪来,“金爷既然已经查访过了,料明白邓爷的为人。我们针工局都是姑娘,他往来得多了,言语上轻薄两句是常事,我们也不敢放在心上。这两回传见我,一次是因冬至日的阳生补子,一次是因消寒图。阳生补子缺漏了两个,已经补齐了,邓爷交代的消寒图,我昨晚也画得了,回头就送到内官监去。”
金自明方才一副豁然开朗的神情,“这么说来就有根底了。”顿了顿又问,“有个叫娟儿的绣娘,和他是不是有过节呀?”
如约道:“针工局的姑娘们,和奴婢是一样的想头,只求平安度日,就算被人责难两句,愈发警醒,办好手上的差事就是了。”
她四两拨千斤,给整个针工局的人都撇清了。金自明淡笑了一声,“午时三刻尚衣监发放绣线,那么姑娘领完线之后又去了哪里?似乎没有立时回针工局吧?”
如约微顿了下,没想到这区区的一刻,都能让他们算计得这么清楚。要说回到值房没人作证,恐怕又够他们做文章了,正想拉扯时间稍作缝补,身后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字斟句酌向上呈禀:“那日仁寿宫太妃跟前李姥姥过身,送进安乐堂了。太妃给了示下,要体面入殓,小的半道上遇见了魏姑娘,请她跟着去了一趟,给李姥姥量尺寸,耽搁了约有一炷香工夫。”
如约没有回头,因为心照不宣,不过向金自明呵了呵腰,“杨典簿说的是。”
这就对上了,因出来作证的是司礼监的人,就没有继续盘问下去的必要了。
金自明重新端起了茶盏,垂眼撇了撇茶叶,“那就有劳魏姑娘了。该问的话都问完了,回去当值吧。”
如约俯身道是,却行退出了正堂。
回到针工局,引珠和张掌司在前堂等着。引珠一见到她,像秋后问斩的人遇上大赦天下,双手合什直道阿弥陀佛,“真真吓死我,就怕你有去无回,被他们盘弄死。”
如约露出笑脸来,“不过是去问个话,怎么弄得我要杀头似的。”
张掌司也松了口气,冲引珠直翻白眼,“我啊,没给忙死,早晚被你拖累死。这会儿人回来了,还戳在这里做什么?还不给我干活儿去,差事不够多是怎么的?”
引珠忙赔笑,“我这不是和掌司一样,担心如约吗。好了好了,人没事儿就行。哎呀不是我说,掌司平日看着挺矜重一个人,到了褃节儿上,真敢往出蹦。”
听得张掌司眉毛直拧,咬着后槽牙道:“好丫头,你就毁我吧!”
引珠就是个没章程的,和她计较,能给气个半死。反正人回来了,司礼监这把火没有蔓延到针工局来,就是天菩萨保佑了。张掌司正了脸色嘱咐如约:“这两天安生在局子里呆着,外头的事别管了。”
如约欠了欠身子,“让掌司操心了。”
张掌司摆摆手,踱着方步往值房那头去了。
轻轻舒口气,她重新坐回南炕上,继续忙活手中的差事。刚才的那点境遇,没有在她心里留下痕迹,仿佛拿起针线,便什么都忘了。
只不过平白死了个人,这事没有那么容易揭过。邓荣这人属于好死不如赖活着,说是自己投死,断乎不能,于是把与之有过节的都拿住了,一个个仔细审问,到最后也没审出个头绪来。
金自明手上有亟待处置的公务要忙,这个案子后来就交给了底下的随堂。邓荣平时人缘不好,属于太监堆儿里的下九流,连同僚都瞧不上他。又过了两天,如约与人闲谈时顺带打听了一嘴,据说扣起来的两个人也给放了,毕竟赌桌上哪来的大仇,一吊钱的买卖,不至于杀人。
所以内官监出了人命这桩事,渐渐搁置下来了,也就是金自明亲自过问那会儿,案子办得有模有样。到了随堂们的手里,糊弄糊弄就完了,快过年了,谁愿意天天死啊活的,都嫌晦气。
眼看年关将至,年三十日,须得把正月十五所用的灯景补子和蟒衣送进大内去。原本狗头灯的差事,就是负责针工局所出成衣的运送,顺道再把宫中需要退还拆改的东西搬回来。说实话没什么油水,还容易招贵人主子责骂,因此职上出缺,司礼监竟找不到一个愿意顶替的。
随堂们比猴儿还精,差事往底下顺,最后落到典簿头上。典簿之中,也只有一个杨稳愿意接手,但典簿不懂针工局的具体事由,那么就得找个人帮衬着。掌司太监物色人选,自然就想到了样样都曾过过手的如约。
来找如约商议的时候,脸上堆着虔诚的笑,“你瞧,针线、绣活儿、织染,你都沾点边,万一上头拿乔,你也有余量应对。不像她们,只管自己手上的活计,一问一个不吱声,到了主子跟前,那还得了!所以就偏劳你,跟着走一趟吧,说到底进宫走动好处多,不像居家过日子,安贫乐道是福分,咱们这个地方,就得出头冒尖。你这样的人才,窝在针工局埋没了,树挪死人挪活,万一运气好,遇上主子爷,没准儿立时攀上高枝儿变凤凰,这也是你的造化呀,是不是,魏姑娘?”
如约很识抬举,一句推辞的话也没有,笑道:“我不求冒尖儿,总是尽心办差,替掌司分忧,我就知足了。”
这话说得张掌司心里热腾腾的,赞叹不迭,“真是好姑娘,我没看走眼。”
事情定下了,人也选好了,各大衙门都放了心。年味儿越来越重,都紧着置办过年事宜去了,只抽调出几个小火者,把做好的衣裳装了车,趁着天色将晚不晚的时候,往顺贞门内运送。
如约已经两年不曾走出过新房夹道了,乍然走到开阔处,心境也舒展开了。顺景山东沿往南行,里头有好长一段空旷处,路上连半个人影也没遇见。
太阳还挂在西边高墙上呢,城里不知哪户性急的人家点起了二踢脚,“咚——叭——”,尖锐的响声,在半空中炸开了花。
并肩而行的两个人,到这时才正经说上话。如约问:“后来他们审你了吗?”
杨稳还是那样温和的语调,轻描淡写说没有,“案子结了,断他醉酒落井,往后不会再查了,放心。”
如约笑了笑,“我知道会是这样。司礼监不愿意耗费精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断他喝醉了酒,这么一来大家都轻省,少了好些麻烦。”
杨稳“嗯”了声,朝着空旷的天际呼出一口浊气,嘴里喃喃着:“天儿真冷啊,上回这么冷,还是五年前吧!”
五年前的冬天,不单天冷得厉害,连人心都凝结成了冰,一辈子都化不开了。
他和她,实在是世上最苦的人了,原本都该有锦绣的前程,怎么会一个做了太监,一个想尽办法摸进针工局,干起了这人下人的营生呢……
所有一切,都得从晋王政变开始说起。
晋王是先帝第三子,孝成皇后所生,与太子慕容淮都是一母的同胞。寻常人看来兄友弟恭,从不生半点嫌隙,可就是这样一个好兄弟,趁着先帝殡天,新皇还未登基的那一小段时间,扣押了所有回京祭奠的藩王,诛太子于寿皇殿,以雷霆手段接掌了乾坤。
越是站在权力顶端的人,越对权柄有偏执的热爱,这点本无可厚非。但一次权力的变更,会拖多少无辜的人下水,又有多少门户家破人亡,这些苦难,登上皇帝宝座的人知道吗?在乎吗?
如约的父亲,本来是太子詹事,掌管着东宫事务,协助三师辅佐太子。如果太子能够顺利登基,那么父亲的政途必会更上一层,作为家中的长女,她的人生也将一帆风顺。像京城所有贵女一样,除了家长里短的困扰,没有任何伤筋动骨的风险。
但偏偏老天作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血淋淋地让她体会到了。太子身边的人,几乎一夕之间被屠戮殆尽,她的家人们,也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
至于她为什么逃脱,可能是天意吧,头天去大圣安寺进香,莫名避开了锦衣卫的抄家屠杀。第二天回到金鱼胡同,才发现那座她生活了十二年的宅子,已经化成了灰烬。一具具被烧焦的尸体从废墟里抬出来,她辨认不出哪个是她的母亲,哪个是她的兄弟姐妹。
无数人在惋惜,却没有人敢多说一句。皇城里头变天了,太子做不成皇上了,太子詹事哪里还能活命。有人小声议论着,锦衣卫是头天夜里来的,子时前后听见胡同里传出哭喊声,逃出去的人也被抓回来杀了,所以那些烧毁的尸首,才都躺得齐齐整整。
她听着,只觉心被撕扯得血肉模糊,宁愿跟着全家一块儿死,也不愿意一个人苟活在世上了。活着对她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残忍和折磨,她要把自己揉烂了重组多少回,才能支撑起沉重的身体,重新在世间行走啊。
现在回头想,好在那天有人拉了她一把,她没有失态跑进废墟里,否则这会儿也已成了刀下亡魂,还怎么图谋为家人报仇。她知道,锦衣卫早晚会发现错漏,早晚还会暗中猎杀她,她当时能做的就是离开京城,找个地方暂且藏身。于是她辗转逃亡,先去了开封,后去了金陵。金陵是南苑王驻地,算得富甲一方,在那里她能找到生计,三年间靠着写字绣花,尚可以周全温饱。
可是三年了,她不能忘记仇恨,料想新帝坐稳了宝座,那些朝廷鹰犬也该放松警惕,不会再执着于追寻她的踪迹了。她得想个办法回来,恰好常买她绣活儿的主顾里,有个独自一人被舍弃在江南的姑娘,因母亲生她难产而亡,自己又染了黄疸,祖母断言她刑克父母,让人把她送回了她母亲几近荒废的老宅。
如今朝廷要采选,他爹舍不得续弦夫人所生的女儿,就想到了她,一封书信招她回去。如约便去央求她,自己愿意给她做婢女,求她带她回京。姑娘是个善性人儿,也不问她为什么,就点头答应了。
可惜好人不长寿,她们走的是水路,运粮的漕船船帮很矮,姑娘在会通河上失足落水,等捞上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从小伺候她的乌嬷嬷嚎啕大哭,既是自责,又害怕回去不能交代。自家儿女的身契都在家主手里攥着,要是问罪,不知又要被变卖到哪里。
如约替她安葬了姑娘,小心翼翼给乌嬷嬷出了个主意,“反正魏家就想送个女儿进宫,我一个人无依无靠,无所牵挂,在哪儿都一样。嬷嬷要是答应,我就替了魏姑娘,这样嬷嬷回去就能交差了,也不枉我们交好一场。”
乌嬷嬷傻了眼,心慌意乱摆手,“那哪儿成啊,不是害了姑娘一辈子吗。”
她说不碍的,“只要京里的魏家人没见过她就行。我不去沾魏家的光,单替魏姑娘进宫,也算给我自己谋了条生路。”
乌嬷嬷思忖再三,终究顾忌儿女前程,最后答应了。
所以她现在是魏如约,没有为全家报仇之前,叫不回自己的名字了。
转头看看杨稳,他倒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但付出的代价十分惨痛。他是太子洗马杨自如的儿子,他父亲被杀后,杨家的男丁砍头的砍头,充军的充军。因他当时只有十一岁,又颇有才气,被送进黄化门净了身,充入掖庭局做了太监。
他和如约是一样的,心里的恨无法磨灭,但他沉得住气,五年间慢慢从掖庭局,爬进了司礼监。时间过去得久了,他又是个审时度势的人,从来勤勤勉勉不惹事。如此淹没在太监堆儿里的听差碎催,连司礼监的掌印,都要忘了他的来历了。
可气的是那个邓荣,爱翻小帐,爱钻空子。他没有为难杨稳,因为杨稳的身世不是秘密,他盯上的是如约。邓荣身子残缺了,但他贼心不死,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消息,冬至那天挨进值房里,靠在窗边打趣:“姑娘不是魏家人吧?”
如约当时心下一跳,却要强装镇定,抬眼笑道:“邓爷说什么呢,我当然是魏家人。”
狗头灯心急得很,涎着脸“嗐”了声,“进来做宫女子,多受委屈!我瞧姑娘模样俏,天天做针线,手上都冻出冻疮来了,可怜见儿的……”说着就要来抓她的手,“快让我瞧瞧,我那儿有上好的獾子油,回头给姑娘送一瓶。”
如约闪躲得快,忙把手背到了身后。心里虽气恼,却不能得罪他,还得好言敷衍:“谢谢邓爷心疼我。可您先前的话,让我惶恐,怎么能说我不是魏家人呢。这可是欺君的大罪,恕我不敢领受。”
邓荣笑得更欢实了,“不瞒姑娘,我留意姑娘有些日子了,出去办事的时候特见了魏家人。那家子眉眼形容儿,和姑娘全不是一回事。听说把姑娘放在江南养到十五岁……江南的水米是养人,肉皮儿细嫩就罢了,眉眼还能变化?”
她听出来了,邓荣眼下怀疑的是魏家找人顶替,还没想得更深。但这人是属狗的,咬住了就不会松口,倘或深挖下去,就不一定瞒得住了。到时候被他拿捏要挟还是小事,万一抖露出来,一切努力就全白费了。好容易走到今天,毁在他手上,实在让人不甘心。
她定了定神,又接着打探,“这事儿,邓爷和别人说起过吗?”
邓荣赌咒发誓说没有,“咱家稀罕你,要是宣扬出去,岂不是害了你,这事儿我能干吗!”
如约遂说了几句软话,先安抚住他,回头找到杨稳商议,杨稳当机立断,“明儿午后,把他约到水井房来。”
她不由望了他一眼,他低垂着眉眼,人因清瘦,隐约有几分不流世俗的气韵。
她知道他的打算,邓荣这种人不能留。再问需要自己做些什么,杨稳淡淡道:“约定了他,后面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杨稳的性情就如他的名字,四平八稳,万无一失。司礼监值房里,有太多的机会能下药,等到午时之后药效正发作,届时塞进井里神不知鬼不觉,尸首上也不会留下任何打斗的痕迹。
所以第二天夜里发现水井房死了人,没什么可意外,如约听了这个消息,把心放回了肚子里。人为求自保,实在顾不得那许多,只是庆幸长夜之中还有人与她并肩而行。因为彼此有共同的目标,即便是耗费上十年、二十年,也在所不惜。
好在老天爷垂怜,没有当真让她花上一二十年。邓荣的死,竟让他们得到一个好契机,能名正言顺地走进紫禁城去。有了名头,一切就好办了,正如张掌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离皇帝越近,报仇的机会就越大。反正这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值得她牵挂的了,她知道刺杀皇帝的机会很渺茫,但她想试一试。
人活于世,总得有点奔头吧!
板车在夹道里缓行,车轱辘吱扭作响,伴着几近落下的日头,让她想起前几年在江南,偶有一次去乡间采香椿,见到农户乘着夕阳,赶着牛车,走过田埂的景象。只是如今天太冷,连老爷儿都罩上了一层霜似的。
杨稳没忘了叮嘱她,“这是头一回进大内,万事小心,不要慌张。反正来日方长,将来的针线活儿都由咱们押送,不止这一回。”
如约点了点头,往前看,前面就是玄武门了,皇城根儿下的门劵子幽深,看不见底。巨大的白纱灯下站了两列禁军,个个压着刀,板着脸,神情仿佛被冻住了,透出一股森冷之气。
凝凝神,她微低下头,跟着杨稳到了门前。守门的禁军要看牌子,杨稳掏出牙牌送上去,那禁军的班领又仔细打量了如约两眼,方才示意底下人放行。
穿过玄武门,就到了一处与皇城格格不入的地方,左右两侧廊庑繁华热闹,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廊下家”。
所谓的廊下家,原本只是最普通的太监直房,但先帝时期准许太监做些小营生,住在这里的太监们就在房前屋后种上了枣树。甜枣儿酿酒,取名“廊下内酒”,但凡沾上个“内”字儿,身价就不一样了,贫困的宦官们可以靠卖酒,赚得一点小钱。
但也因如此,廊下家逐渐经营成了紫禁城内唯一有烟火气的地方。后来太监们又另辟蹊径,仿着外头的做法,弄出了个买卖街,太监宫女扮商户酒妇,售卖各色琳琅物件。譬如古玩、小吃、旧衣裳等,当然也不乏斗鸡逐犬的消遣,以此来招揽宫中的贵人主子们。说不定运气好,万岁爷还愿意来逛逛,那可是大主顾,开张吃三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如约以前听说过廊下家,但从来没有亲眼得见,今天路过这里,恍如闯进了市井,实在让人大开眼界。
针工局的板车没有再往前,原地停了好一会儿,才等到内造处的掌事太监。只见他潇洒地一打帘,从一间茶馆里钻了出来。想是扰了他的雅兴吧,不怎么高兴的样子,一面剔着牙花儿,一面抱怨:“怎么这么晚才进来?眼看都要下钥了。”
杨稳向他呵腰,“请高师父恕罪,实在没法子,针工局紧赶慢赶,才赶出这批货。宫里催得急,不敢耽搁,所以加紧让人装了车,免得年三十匆忙。”
高太监这才没话说,招呼了边上的长随,“领他们上内造处去。”话方说完,又瞥了如约一眼,“这位姑娘眼生得很,不是宫里人?”
如约说是,“奴婢是针工局的,受掌司委派,随杨典簿来送补子。”
高太监“哦”了声,“难怪没见过。”复又上下打量了一番,啧啧摇头,“好好的,怎么给派到针工局去了。要是在大内,上廊下家弹琵琶来,不知有多远大的前程呢,可惜了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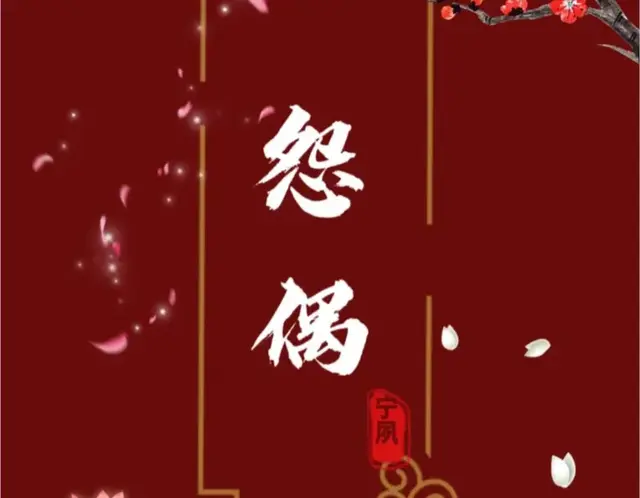







这琉璃阶上的描写太唯美了,琉璃器真是文化传承的瑰宝啊
大爱尤四姐[点赞]
《琉璃阶上》,内容
琉璃器传承千年,承载着历史韵味,别具匠心,真正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