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6年,北宋名将狄青受到弹劾,宋仁宗认为狄青忠心可鉴,大臣文彦博反问当年赵匡胤难道不是周朝的忠臣?此话一出,狄青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狄青出生于山西汾阳的普通农家,十六岁时因兄长与人斗殴,代兄受过,脸上被刺了代表罪犯的 “黥面”,发配军中。 在重文轻武的北宋,连武将的地位都不高,更何况是黥面的士兵。但狄青偏要逆天改命,他投身西北前线时,正值西夏李元昊称帝,宋夏之战爆发。宋军连遭惨败,士气低落,而狄青却在战场上所向无前。 十几年时间,狄青靠着战功,从普通士兵累迁至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成为北宋在西北的名将。 真正让狄青跃入宋仁宗眼中,视其为股肱之臣,是平定侬智高之乱。 1052年,广源州的侬智高起兵反宋,连破九州,兵围广州,宋军数次征讨皆大败而归。 危急时刻,狄青自请出征,宋仁宗破格任命其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赋予其军政全权。 狄青率大军到桂林后,当众斩杀擅自出战致败的官佐32人,整肃军纪。随后,狄青亲率精锐夜袭昆仑关,在归仁铺决战中大败侬智高主力,“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一举平定叛乱。 此役过后,狄青声望达到顶峰,宋仁宗力排众议,任命其为枢密使。狄青也成为北宋历史上,唯一 以武将身份担任枢密使的人。 狄青出任枢密使,打破了北宋 “进士拜相,将门无缘枢密” 的潜规则。 狄青枢密使的位置尚未坐热,文官集团针对他的弹劾便接踵而至。 文官集团对狄青的攻击,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出身歧视:御史中丞王举正弹劾狄青 “出身行伍,非科举出身,难当枢密重任”。 在文官看来,狄青脸上的黥面不仅是个人耻辱,更是对枢密院这一 “清要之地” 的玷污。 二是谣言中伤:京城流传着 “狄青家狗生角”“狄青府邸夜有光怪” 等谣言,直指其有 “龙兴之象”。这些无稽之谈,在谶纬盛行的宋代,却足以构成谋反嫌疑,好在狄青遇见的君主,是不擅杀的宋仁宗。 三是权力猜忌:狄青在军中威望极高,士兵见其画像皆拜,这让文官集团不寒而栗。参知政事梁适直言:“青握兵权久,恐尾大不掉。” 宋仁宗曾试图保护狄青,他将谣言告知狄青,劝其 “在家避嫌”。 狄青免冠顿首,泣血陈情:“臣起于行伍,蒙陛下厚恩,今流言蜚语,实非臣所愿。” 在文官集团的轮番轰炸下,宋仁宗的态度也逐渐开始转变。 文官集团对狄青的围剿,本质上是对 “崇文抑武” 的维护。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北宋形成了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格局,武将地位一落千丈。 狄青担任枢密使,打破了这一平衡,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 1056年的那场朝堂辩论,成为压垮狄青的最后一根稻草。文彦博的 “太祖之问”,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刺穿了狄青所有的辩解。 文彦博的逻辑极其冷酷却又难以反驳:赵匡胤当年正是凭借后周禁军统帅的身份发动陈桥兵变,那么,即便狄青毫无反意,其军事才能与军中威望本身,就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 不久后,宋仁宗下诏,罢狄青枢密使,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从最高军事长官到地方知州,看似仍是使相级别,实则是明升暗降,剥夺了所有实权。 离京那日,狄青身着便服,只带几名老仆,悄然离开开封。他曾试图向宋仁宗辞行,却被以 “繁忙” 为由拒绝。这位为大宋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最终在文官集团的目送下,孤独地走向人生的终点。 陈州的日子,对狄青而言是无尽的煎熬。朝廷并未放松对他的监视,“每月两遣中使抚问”,名为慰问,实为监视。 狄青深知自己仍在猜忌的旋涡中,终日惶惶不安。他曾对人感叹:“吾此行,必死无疑。” 果不其然,到陈州仅半年,狄青便一病不起。 1057年3月,狄青这位年仅四十九岁的名将在忧愤中离世。消息传回开封,宋仁宗 “发哀,赠中书令,谥武襄”。 狄青的葬礼上,前来送行的官兵自发佩戴白巾,哭声震野。 那些曾经弹劾狄青的文官们,大多保持着沉默,或许在他们看来,牺牲一个狄青,换取朝廷的 “安稳”,是值得的。 狄青之死,并非个人悲剧,而是北宋“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北宋历任皇帝都在重复着 “用将而疑,赏功而忌” 的循环:曹彬攻灭南唐,却因小过被贬;杨业战死沙场,反遭主帅构陷;种世衡经营西北有功,终因文官弹劾而郁郁而终。 在开封的狄青祠里,有一副对联写道:“著绩南朝,不愧宋廷柱石;图形北阙,堪称武将楷模。” 这或许是对狄青最好的评价,他未能改变北宋的崇文抑武,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武将的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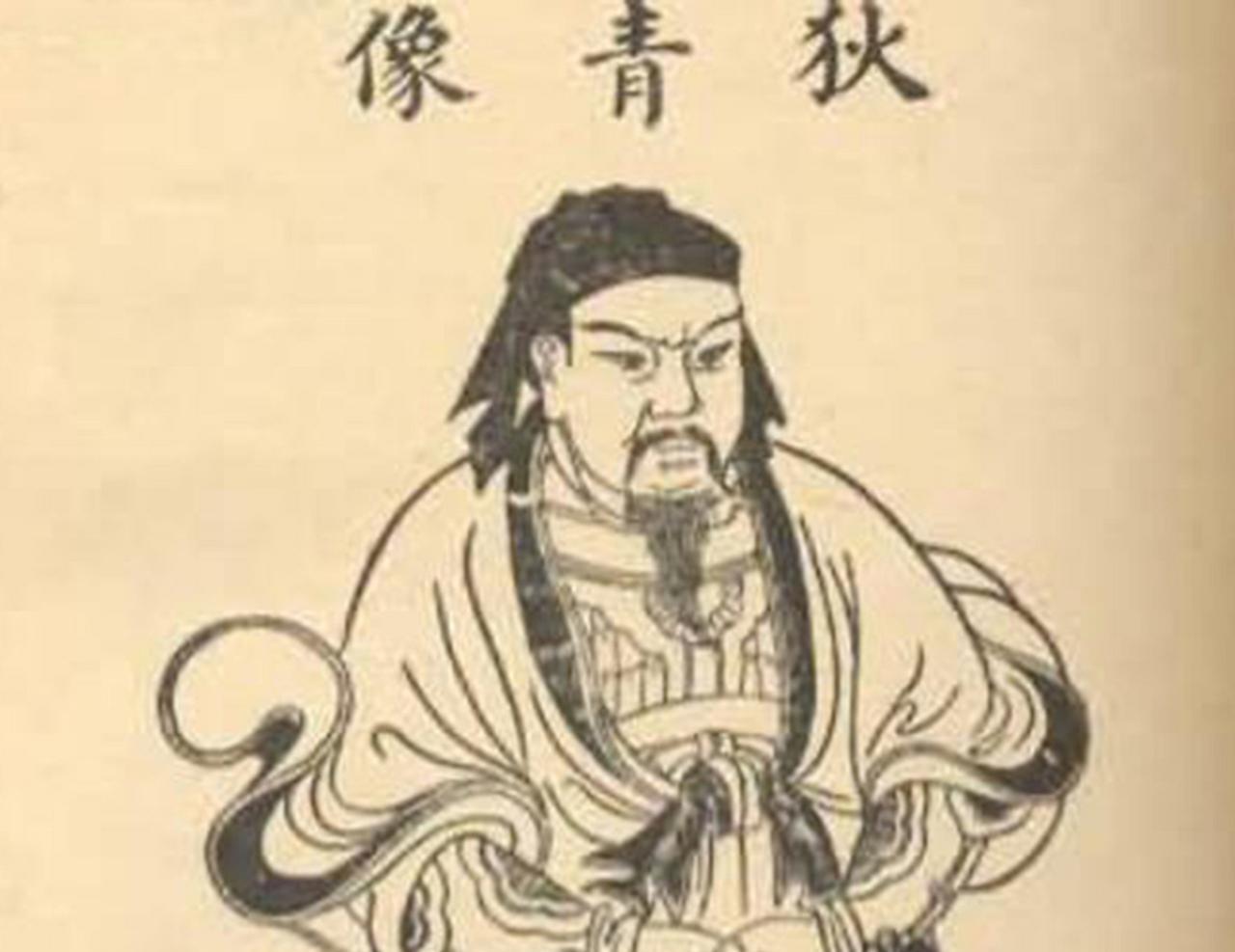

悼明
又是一篇打胡乱说的自媒体文。所谓“进士拜相,将门无缘枢密”纯粹是无稽之谈。北宋时期,夏竦不是进士,曾拜枢密使,薛向荫官出身,也拜枢密副使。大名鼎鼎富弼,也未考中进士,拜昭文相。将门出身的曹彬、王德用,也是拜枢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