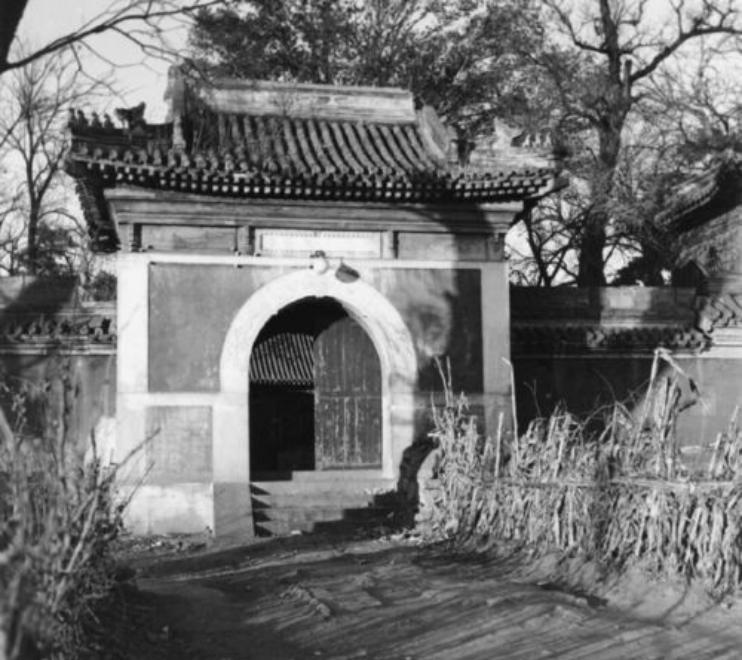37年,王凤阁一家因抗日被捕,5岁儿子小金子:我不吃亡国奴饭 “1937年4月22日凌晨,你一定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王凤阁在昏暗的牢房里贴着儿子的耳朵轻声说完,守卫粗暴推门,铁链哗啦作响。短短一句话,像火种一样烙在孩子心里,也为这段悲壮往事拉开帷幕。 此刻的通化,街面空荡,日军宪兵队灯火通明。王凤阁浑身是血,胳膊打着夹板,张氏抱着小金子缩在角落。看守递来一碗热饭,白米上还撒了几粒豆子,香味四散。小金子咽了口唾沫却转过头,闷声一句——“亡国奴的饭,我不吃。”日本宪兵愣住,狭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恼怒。五岁的孩子,把战俘营瞬间点燃成战场。 往前推四十年,1897年,通化一户教师家庭迎来一个男婴——王凤阁。家境殷实,父亲讲《左传》,母亲做江米条,那些书卷与烟火,早早在他心里种下家国的秤砣。辛亥后的东北军阀混战,王凤阁在混乱中读完吉林陆军小学。身板不算魁梧,却常在操场扯着嗓子喊“要打就打大的”,教官因此记住了他。 九一八当夜,沈阳城上空炮火映红天际。王凤阁带着一支班排护送学生撤离,亲眼看见关东军把校门口的大石狮炸成碎片。第二天,他扛起大鼓,站在柳河城口唱《满江红》,一句“怒发冲冠”吼得百姓眼眶通红。自此,通化一带的木匠、车夫、教书先生陆续跟着他跑进深山,“辽宁民众义勇军”就这么土里土气地成立。 1932年底,王凤阁率三百余人夜袭柳河伪警察署,掳走迫击炮六门、步枪两百支。中央接到电报,回了四个字:东北有望。一个月后,义勇军改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番号是第十九路。番号听上去像正规军,可吃的还是高粱米,穿的还是羊皮袄,唯一的优势是跑得快。王凤阁常说:“咱打的是游击,不是排队枪毙。” 战争间隙,他同队里一名女卫生兵张氏成婚。简陋的洞房就在果松川密林边,树皮糊墙,棉被当门,洞口吊着一盏马灯。次年春天,小金子出生,哭声惊起林间飞鸟。张氏营养不良,没有奶水,战士们把仅剩的高粱捣碎熬成糊喂孩子,谁抱得久谁就乐呵呵地说一句:“咱全队的‘司令’。” 1933到1936,王凤阁指挥百余次战斗,最凶险的一回是夜闯抚松县公署。大雪封山,巡逻灯笼像一串妖红的眼睛,他一声口哨,十几条身影飞檐走壁,炸毁弹药库,扬长而去。关东军报纸称他为“山岭之狐”,以万金悬赏。传单飘遍几县,百姓把它糊灶台,笑说“日本鬼子急红眼”。 眼看拉锯难分胜负,敌人换了招数——渗透和围剿。1936年冬,通化、临江、辑安三面合围,山岭炮声昼夜不断。自卫军弹尽粮绝,被迫拆分为若干小股,靠雪水蘑菇充饥。张氏用冻土豆刮成片给小金子磨牙,孩子咬得嘎嘣脆,却从不哭闹。士兵悄悄说:“这娃比咱硬气。” 残雪未化的1937年春,王凤阁携妻儿与十几名战士突围至老虎顶子山。夜里只敢点一簇小火,没想到火星被高处山哨发现。枪声裂空,十多名弟兄当场倒下,王凤阁臂骨中弹,被俘时仍咬牙拖着伤腿护着妻儿往树林里挪。日本军官挥刀,冷冷一句:“活的,比死的值钱。” 押解到通化宪兵队后,日军一面酷刑,一面设宴。桌上鲑鱼刺身、洋酒玻璃瓶,灯影摇晃。汉奸纪大作、廖弼辰被请来唱红脸白脸。“王司令,识时务者为俊杰。”廖弼辰挤出笑,手指捻着象牙筷子。王凤阁冷哼,“俊杰是保家卫国,不是割地求荣。”随即掀桌,酒水四溅。刺刀落在他脖颈,仍不改色。 软刀子不管用,敌人把目光转向孩子。糖块、洋娃娃、热饭,一样样端进牢房。小金子眨着眼睛看,鼻尖冒汗,却往后退一步,大声怼回去:“滚开!日本东西臭得很!”两名宪兵面面相觑,不知是怒是惧。一个孩子,在他们眼里最该软弱的存在,突然成了一面墙。 接下来的三天,牢房外频繁传来脚步声,劝降、威逼轮番上演。小金子渴得嗓子哑,也不肯碰日军递来的茶水。他把空铁碗往地上一摔,“我喝雪也不喝你们的水!”张氏怕他脱水,示意先接过来。孩子接了,却转身猛地泼向看守,铁碗当啷落地。日军脸色铁青,决定立刻处决全家。 4月24日清晨,大街被封,民众被驱赶站两旁。卡车开过,积水被车轮溅起。王凤阁被单独铐在前车,回头看见妻子抱着儿子。他冲百姓微微点头,像是交代,又像是托付。刑场两口浅坑已挖好,他拒绝跪地,纵身跳入坑内,声如洪钟:“我王凤阁,为抗日前来;今日就义,无怨无悔!”枪声突起,尘土飞扬。 张氏扑进坑里遮住小金子,子弹在她后背开出血花。孩子眼里蓄着泪,掰开母亲的手,踉跄着冲向荷枪实弹的兵列,瘦小的身影竟让那些成年人后退半步。下一秒,脉动的火舌淹没了他。年仅五岁的小金子,没来得及再喊一句口号,却以最直接的方式说明——亡国奴饭,他真没吃过。 枪声散去,刑场一片寂静。百姓无人出声,却有人把斗笠摘下,紧紧攥在胸口。那天通化的风里裹着残雪,没过多久,北满各支游击队悄然流传一句话:“打鬼子,要像小金子那样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