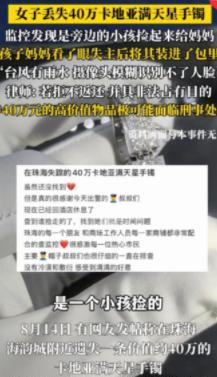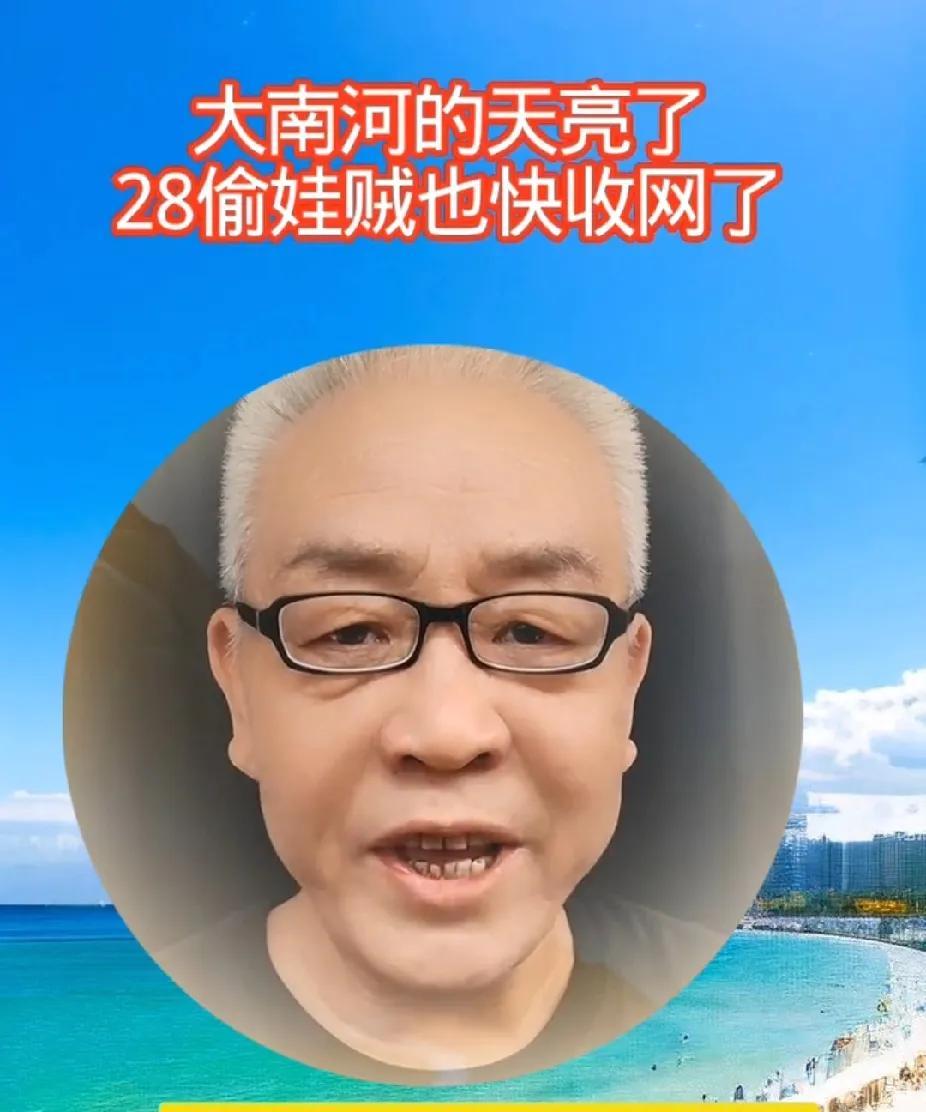1973年,81岁的美国女子赛珍珠死后,家人为其穿上中国的传统旗袍,然而因为家中晚辈没人能听懂中文,自然也忽略了她临终的遗言:我的老家在镇江,送我回镇江老家......
守在床边的美国亲眷面面相觑,没人听懂这句遗言的分量。
三小时后,这位身穿旗袍的诺奖作家在异国他乡阖然长逝,墓碑只刻着三个篆体汉字——赛珍珠。
这个被中国养大的“洋娃娃”与镇江的缘分,要从1892年说起。
那年初夏,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夫妇带着三个月大的女儿登上远洋渡轮。
当襁褓里的珀尔·巴克第一次睁开蓝眼睛,长江的波涛正拍打着清江浦码头。
两年后举家迁居镇江,父亲按中文习惯给女儿取名“赛珍珠”,在润州山麓购置的小楼成了她童年记忆的起点。
镇江城浸润着赛珍珠最初的东方启蒙,保姆王妈总在雕花木床边讲白娘子水漫金山的传说,私塾孔先生摇头晃脑教她背《三字经》,街坊小孩带她钻竹林捉蟋蟀。
十岁那年私塾先生病逝,父亲特意请来前清秀才教四书五经,书房里的《红楼梦》被她翻得卷了边。
据南京大学赛珍珠研究所档案记载,她晚年仍能背诵《葬花吟》,曾说“林黛玉的眼泪比密西西比河还长”。
1910年回美国读大学时,赛珍珠已是个能写瘦金体、会包粽子的“假洋鬼子”。
弗吉尼亚州梅康女子学院的同窗记得,这个总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姑娘,书包里永远揣着《水浒传》。
四年后她重返镇江,在崇实女中教书时遇到农学家布克。
婚后跟着丈夫去安徽宿州考察,黄土高原上的见闻震撼了她的世界观。
佃户王老汉一家五口挤在土坯房,女儿为省口粮自愿卖作童养媳。
这些场景后来都写进《大地》,书里王龙娶亲时借的红绸褂,原型就是她在宿州集市见过的嫁衣。
南京鼓楼北坡的小洋楼见证了她最辉煌的创作期,1921年到1934年间,赛珍珠在这里写出《大地》初稿。
美国出版商最初看不上这种“土掉渣的中国故事”,直到约翰·戴公司冒险出版,没想到首印5000册三天售罄。
1932年普利策奖评委会全票通过授予《大地》,六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赞她“为中国农民铸造了一座青铜纪念碑”。
不过最让镇江街坊津津乐道的,是她领奖时特意订制的苏绣旗袍,后襟还绣着金山寺塔影。
抗日烽火燃起时,赛珍珠在纽约电台用中文演讲:“中国就像长江里的大石头,洪水再猛也冲不走!”
她创办的《亚洲》杂志连载斯诺的《西行漫记》,还帮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牵线出版。
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着1943年的募捐记录,显示她为中国抗战筹得23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4000多万美金。
可惜这些赤子之心,在冷战铁幕下渐成负累。
1949年后,中美交恶让赛珍珠成了“敏感人物”。
她寄往镇江的信件石沉大海,想捐建儿童图书馆的提议被婉拒。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她连夜给中国驻加大使馆写信申请随行,收到的回函却写着“您长期歪曲新中国的作品令人遗憾”。
南京大学原外事处档案显示,这封拒绝信让她大病一场,床头始终摆着幼年在镇江拍的全家福。
最后的岁月里,赛珍珠在绿山农庄收养了六个亚裔孤儿。
孩子们记得奶奶总穿那件领口磨白的旗袍,教他们用镇江话唱童谣:“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
1973年春天,昏迷中的她突然清醒,摸着旗袍盘扣说了句完整的中文。
护士听不懂的“送我回镇江”,成了她与故土最后的羁绊。
如今镇江博物馆里陈列着她的绸面日记本,泛黄纸页上工整抄写着《枫桥夜泊》,页脚还粘着片干枯的银杏叶——那或许是她从金陵大学故居的老树上摘的。
下葬那天,六个养子女穿着她缝制的唐装,在刻着“赛珍珠”的墓碑前撒了把镇江带来的黄土。
风起时,丝绸旗袍的下摆轻轻扬起,恍惚还是1924年南京城那个春夜——31岁的女教师捧着《大地》手稿穿过蔷薇花墙,中文讲稿里夹着徐志摩译的泰戈尔诗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