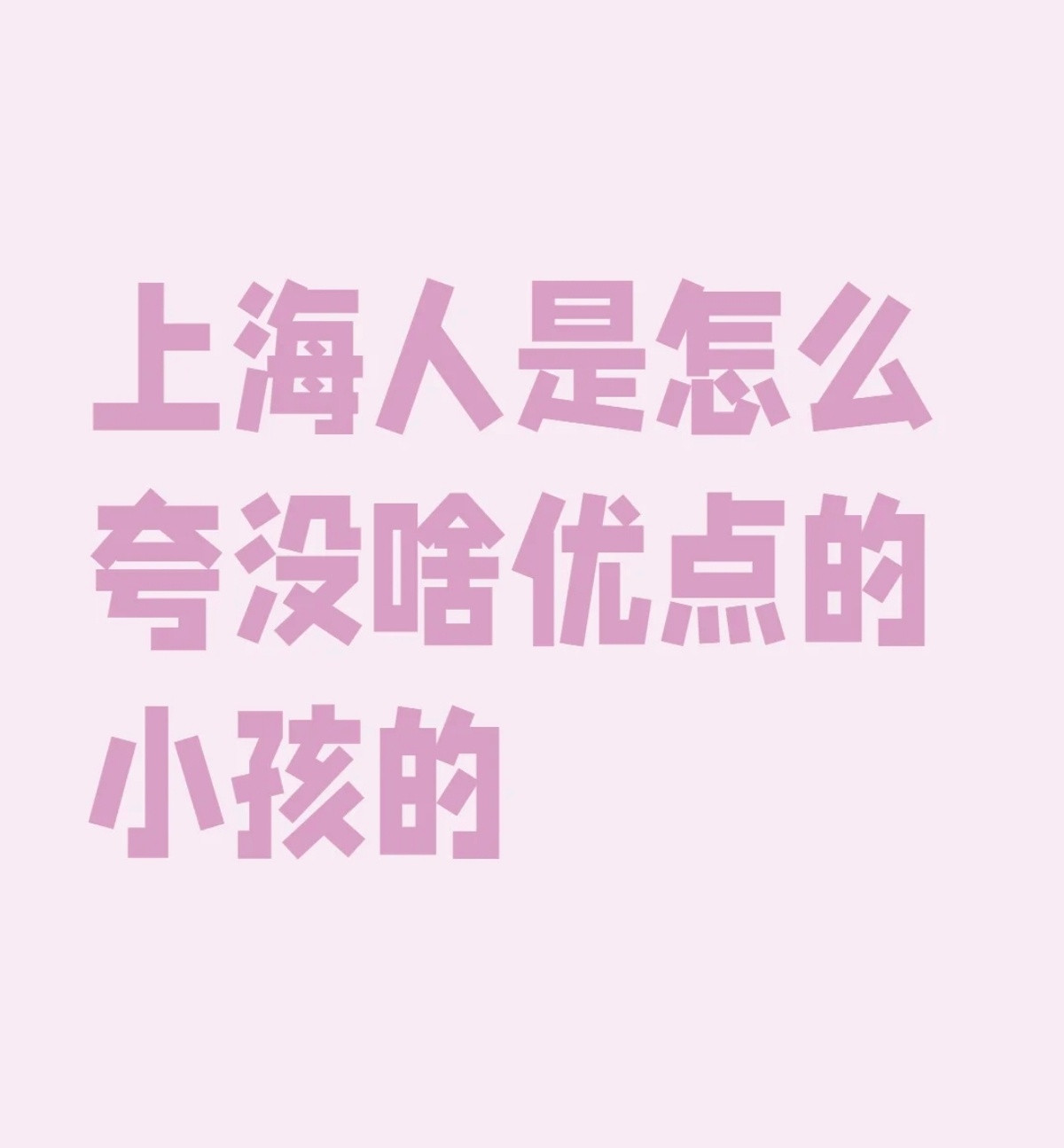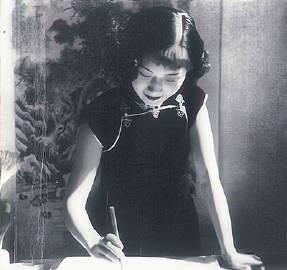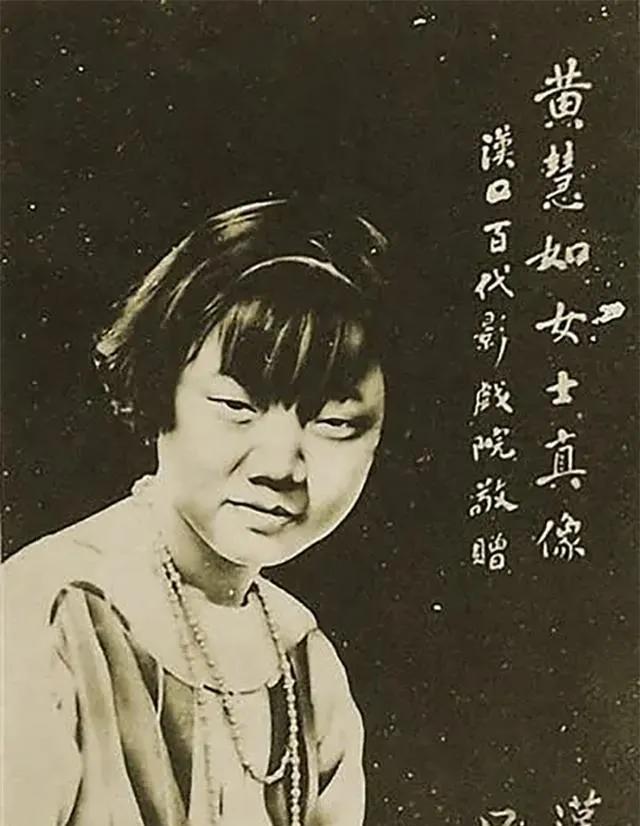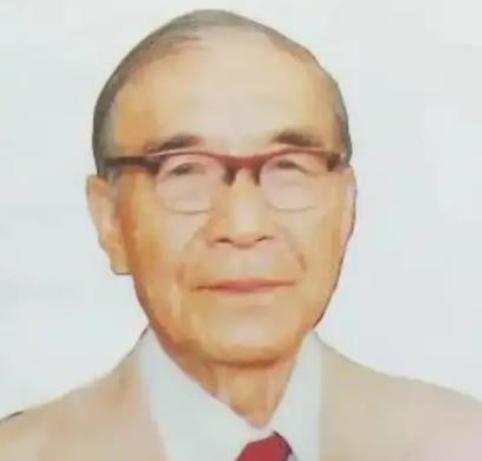2020年,上海警方在一个废弃茅房里,发现了一个衣不蔽体,浑身脏臭的流浪汉,当警方为了帮他寻亲探究其身份时,竟意外发现他居然是90年代的高考状元!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2020年冬天,上海的气温格外湿冷,几名民警在一次人口普查中走进了一片破败的老城区,那里大部分房屋已经被拆空,只剩下斑驳的墙壁和散落的砖瓦。 在一间摇摇欲坠的废弃茅房里,他们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刺鼻的气味立刻涌了出来。 昏暗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人,身上盖着破烂不堪的布条,露出的皮肤灰黄干裂,头发纠成一团,眼神空洞,仿佛与周围的一切没有联系。 他几乎不发出声音,身上的衣服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脚上只套着一只不合脚的旧鞋,民警将他带离那里,安排简单清理,并尝试确认身份。 起初,他的反应迟钝,只能断断续续吐出几个模糊的词语,其中有“北京理工大学”几个字。 信息被记录下来后,与档案系统进行比对,屏幕上跳出的结果让所有人愣住——这名看似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竟是上世纪90年代湖北省的高考理科状元姚远。 1971年,姚远出生在湖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只有几亩薄田,父母终日劳作,但对他的学习格外上心,邻里都知道他聪明好学,别人需要反复琢磨的题目,他一遍就能抓住要点。 课本翻得起毛,作业本总是整齐干净,年年考试都是全校第一,父母虽日子清苦,但总会想办法为他买参考书,他们心里清楚,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 1990年的夏天,高考成绩揭晓,他以全省理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理工大学,这个消息在小村里引起轰动,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道喜,还有人帮忙筹钱为他买去北京的火车票。 那时的他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父母的期望,第一次离开熟悉的土地,踏上通往首都的列车。 在北京理工大学,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他很快意识到这里的竞争远比家乡激烈,曾经的绝对优势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不容松懈的学习压力。 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很少与同学外出,也不参加社团活动,四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一家科研单位录用。 进入工作后,他的生活稳定下来,薪水在当时的标准里算不错,父母也为此感到安心,但长时间从事单一的研究任务让他感到疲惫,每天的工作内容像是被复制粘贴,生活像静止的湖面。 偶尔听到一些同学在企业中脱颖而出、创业有成,他心里便涌起强烈的落差感,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看不到未来的格子间里。 在科研单位待了九年,他决定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寻找新的机会,父母极力劝阻,认为这份工作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保障,但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上海的繁华和机遇吸引着他,他带着简历和希望南下。 到达上海后,他才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节奏和门槛,求职屡屡受挫,递出的简历常石沉大海,就算进入面试,也因为经验与岗位需求不匹配被婉拒。 他对工作的要求很高,低薪职位不愿尝试,高层岗位又无法获得信任,短暂的几次就业很快以离职告终,频繁更换工作也让用人单位产生顾虑。 金融危机袭来时,他所在的小公司裁员,他的名字出现在名单里,失业带来的冲击让他陷入困境,他没有对家人说明真实情况,也不愿寻求帮助。 积蓄很快耗尽,房租交不起,只能搬离出租屋,开始睡在天桥下、废弃楼里,为了活下去,他翻找垃圾桶,捡拾废品换取微薄的零钱。 日复一日,身上的衣服破得无法修补,头发凌乱不堪,身体被寒风和饥饿消耗得干瘦如柴。 这一过就是十二年,姚远与家人断了所有联系,父母曾多次来到上海寻人,贴寻人启事、跑遍大街小巷,却始终没有结果,年复一年的等待,换来的只是无声的失落。 在那间废弃的茅房被发现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曾经的模样,警方确认身份后,联系到湖北的父母,消息传到家乡,年迈的父母连夜动身赶往上海。 医院的病床上,姚远的脸瘦削、皮肤黯淡,眼中空洞的神色中隐约闪过熟悉的光,父母看着眼前的人,心中涌动的是失而复得的喜悦与酸楚交织的痛意。 回到家乡后,他在亲人的照料下慢慢恢复体力,精神状态逐渐好转,断裂的记忆也开始拼合,他在院子里坐着,看着熟悉的田地和远处的山,心里泛起一种久违的安定。 过去的荣光与坎坷像两条河,最终汇入了平静的生活,他不再急于追求所谓的高度,而是想为父母分担一些家务,让他们的晚年不再有奔波与忧心。 这段经历让人唏嘘,曾经的高考状元,走过辉煌,也经历沉沦,失落与孤独将他推入流浪的边缘。 重新回到家乡时,他已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人生,光环终会褪去,唯有在生活的起伏中学会面对自己,才是走得更远的力量。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最华人——高考状元上海打拼受挫,与父母断绝联系,12年靠捡垃圾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