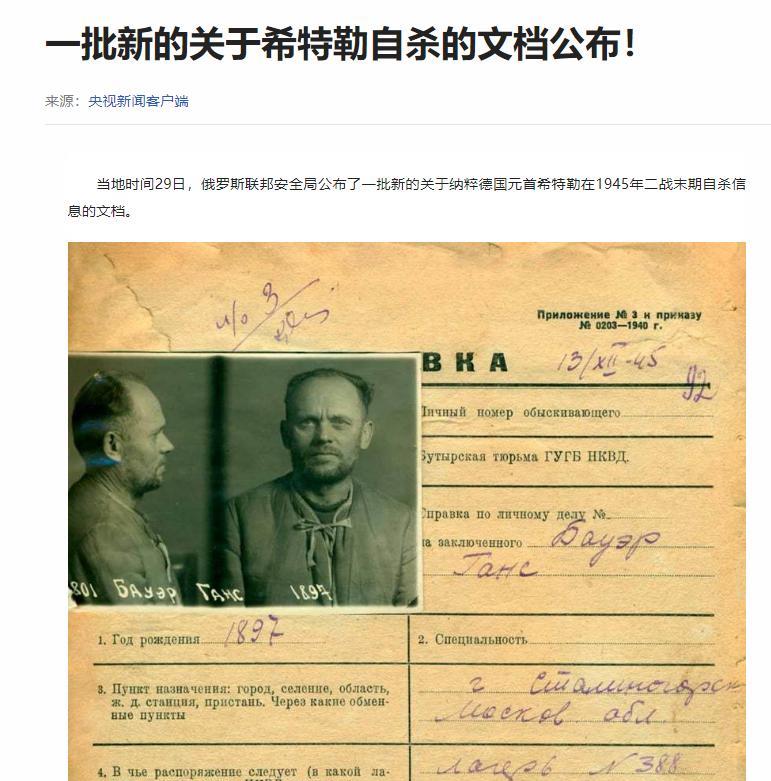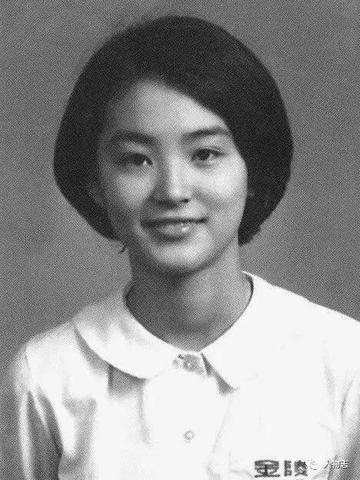公元627年,一日散朝时,李世民让长孙无忌留步,有要事相商。长孙无忌不疑有他,神色自若。岂料李世民递给他一封奏折,长孙无忌打开一看,冷汗直流,神色紧张。 奏折的宣纸边缘还带着墨香,字字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指尖发颤。弹劾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嫡长子长孙冲。奏报里说,上月洛阳漕运翻船,损失的三万石粮草,竟是长孙冲为了填补私贩盐铁的亏空,串通漕吏故意为之。末尾还粘着张账册副本,朱砂画的圈记,正是长孙家商铺的印记。 “辅机看得仔细些。”李世民端起茶盏,水汽模糊了他的眉眼。龙案上的青铜镇纸压着半叠奏折,最上面那本的封皮,分明是御史台的形制。“这是昨晚大理寺递上来的,按察使在洛阳查了半月,人证物证都齐了。” 长孙无忌的靴底在金砖地上蹭出细响,后背的官服已被冷汗浸得发暗。他想起三天前儿子回京,带回两箱西域的宝石,当时只当是商队的常例,没曾想……喉结滚了滚,竟半个字也说不出。 李世民放下茶盏,瓷碗与桌面相碰的脆响,在空旷的太极殿里荡开。“还记得武德九年吗?”他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落雪,“你揣着刀跟在我身后,玄武门的石板缝里,渗的可都是血。” 这话像根冰锥,直扎进长孙无忌心里。那年他三十出头,攥着刀柄的手被血泡得发白,看着李世民踏着李建成的尸体走上台阶,眼里的光比殿上的金灯还亮。他以为那是为了江山,为了让百姓不再遭兵戈,可如今…… “陛下,”长孙无忌“噗通”跪下,朝服的前襟沾了灰,“犬子荒唐,臣……” “辅机起来说话。”李世民没看他,手指摩挲着奏折上的字,“你是朕的大舅子,是凌烟阁上排第一的功臣。长安城里谁不知道,长孙家的门槛,比六部衙门还难进。”他顿了顿,抬眼时,目光像淬了冰,“可难进的门槛,挡得住外人,挡不住家里人作妖啊。” 长孙无忌的指甲掐进掌心,血珠顺着指缝滴在金砖上,洇出小小的红点。他想起女儿嫁给太子时,李世民拉着他的手说“咱们是一家人,要共守这天下”。那时他信了,以为亲缘加功勋,能让长孙家稳如泰山。却忘了,这宫里最薄的是情面,最狠的是皇权。 三日后,长孙冲被押进大理寺的消息传遍长安。没人敢去求情,连皇后长孙氏也只在宫里哭了半宿,第二天照旧带着宫女绣《女诫》。倒是长孙无忌,亲自带着家仆抄了商铺,把所有账本送到御史台,连长孙冲藏在床底的那箱宝石,都一并交了上去。 李世民在御花园召见他时,他正跪在牡丹花丛前,脊梁挺得笔直,像当年在玄武门时一样。“臣请辞司空之职,”他声音哑得厉害,“回并州老家,给先母守陵。” 李世民摘下朵半开的芍药,簪在他的朝冠上。花瓣的粉,映着他两鬓新添的白,竟有些刺眼。“你走了,谁替朕看住那些老狐狸?”他笑了笑,眼角的细纹里盛着些说不清的东西,“冲儿年轻,该受些教训,但国法之外,总还有些情分。” 后来长孙冲被判流放岭南,没到半年就遇赦回京,只是终身不得入仕。长孙无忌照旧在朝堂上站着,只是话少了许多,每次议事,总把目光落在阶下的石板上,像在找什么。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命人画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长孙无忌的画像挂在最中间,画师特意把他的腰画得挺直,眼神锐利如旧。可熟知他的人都知道,自那封奏折后,他再也没在朝堂上笑过。 史书里总说唐太宗如何知人善任,说长孙无忌如何忠谨。可那些藏在“君臣相得”背后的试探与权衡,那些被权力撕开的亲情裂痕,从来都比官修的史书更真实。就像玄武门的血迹,看着是干了,可每逢阴雨天,总会在石板缝里泛出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