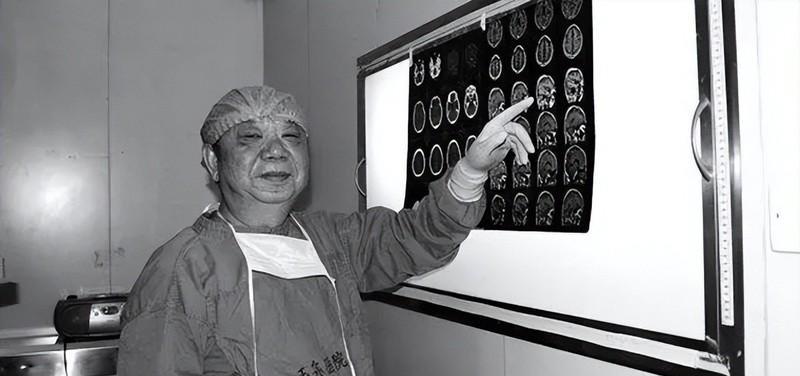1885年,74岁的左宗棠病故,众大臣定谥号却犯了难,连拟4个,慈禧仍不满。焦灼之际,一学者出了个主意,慈禧连赞:“就定这个,成全他往昔愿望!” “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当军机章京徐庚身在养心殿念出《周书·谥法》里的这句话时,殿内的烛火似乎都顿了顿。 这话像一道光,照进了僵持多日的困局——此前内阁拟的“文胆”“忠烈”“威毅”“恭勇”,要么偏于文治,要么仅显勇武,都被慈禧以“未协”二字驳回。 而“襄”字,像专为左宗棠量身打造,藏着他一生最沉甸甸的注脚。 这注脚刻在西域的戈壁里。1876年,64岁的左宗棠正对着地图咳嗽,案头堆着李鸿章“弃疆”的奏折:“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 他猛地将笔拍在案上,墨迹溅到“伊犁”二字上。那时清廷国库空虚,西征军费需他自筹,可他看着地图上被阿古柏侵占的百万疆土,连夜上书:“祖宗之地,寸土不能让!” 次年春天,他带着一口棺材出嘉峪关,军帐里的油灯夜夜亮到天明,从肃州到乌鲁木齐,每一步都踩着沙砾与决心。 两年后,新疆全境收复,捷报传到京师时,慈禧正在赏牡丹,闻言沉默片刻,说:“这老东西,倒真做成了。” 谁能想到,这个在西域扬威的老将,早年竟是个落第举子。1832年,20岁的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半工半读,父亲早逝,母亲新丧。 他白天给同窗抄书换米,夜里就着月光啃《农政全书》《读史方舆纪要》。 三度会试落第后,他撕碎答卷,在墙上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转身钻进农田研究水稻,跑到河道测量水势。旁人笑他“不务正业”,他却在这些“杂学”里,攒下了日后治疆、办洋务的底气。 后来太平天国军逼湖南,湖南巡抚骆秉章请他入幕,他凭着对地理的熟稔,三天拿出防务图,硬是守住了长沙城。 定谥的争论里,有人拿“规矩”说事:“按例,未竟钦差之责者不得谥‘襄’。”左宗棠临终前是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刚到任四个月就病逝,海防整顿尚未着手。 可徐庚身冷笑一声,翻出左宗棠西征时的奏稿:“臣年六十有四,岂敢妄贪天年?惟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这话掷地有声——当他带着棺材穿越沙漠时,早已把“差事”做成了“功业”,区区未竟的海防,怎掩得住收复新疆的万丈光芒? 慈禧心里有本账。她记得左宗棠办洋务时的倔强,福州船政局开工那天,他拒绝用洋匠的图纸,非要掺进中国工匠的巧思。 也记得他直谏时的硬气,甲午前他力主加强海军,奏折里直指“太后修园,国库虚空”,气得她将奏折摔在地上。 可她更记得,新疆收复后,英俄使节在朝堂上收敛的气焰,记得那份标着“中国领土”的新疆地图,如何让摇摇欲坠的清廷多了几分底气。 “文襄”二字,“文”能彰他通经史、办洋务的智,“襄”能显他复疆土、固塞防的功,恰如其分。 1885年深秋,左宗棠的灵柩从福州启程回乡,沿江百姓自发跪拜。 有人举着他当年督办的船政局造出的“扬武”舰模型,有人捧着新疆的沙土——那沙土里,混着湘军士兵的血与汗,也混着他“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誓言。 灵柩上还未刻字,但沿途百姓都知道,朝廷会给这个老人一个配得上他功绩的名分。 最终,“文襄”二字刻上墓志铭时,距离他病逝已过月余。这两个字里,藏着一个落第举子的逆袭,藏着百万疆土失而复得的艰难,更藏着一个民族在风雨飘摇中,从未熄灭的坚守。 就像徐庚身说的,“功业自在人心”,清廷的谥号或许会被岁月磨损,但左宗棠在西域种下的左公柳,早已成荫,替他把“襄”字的分量,刻进了历史的骨血里。 主要信源:岳阳市人民政府——绝口不谈和议事 千秋唯有左文襄;人民网——人民日报沧桑看云: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