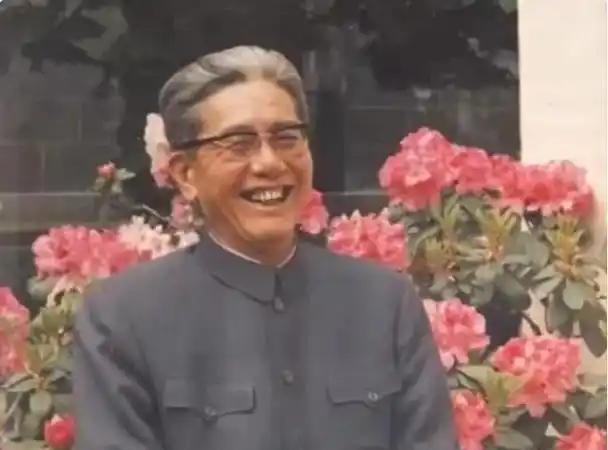1948年底,刘伯承和陈毅到达西柏坡。当晚,毛泽东就对陈毅说,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有什么要求嘛尽管可以提。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 1948年的西柏坡,冬夜的风带着土腥味,院子里烧柴的烟味混在一起,钻进屋子,呛得人直眯眼。 刘伯承和陈毅赶到的时候,鞋帮子沾着泥,外套的扣子半开着,像是一路上谈事谈得急。 那天晚上,毛泽东没多绕话,见了陈毅,点着烟就说:上海解放了,你去当市长吧,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 话是平平地说出来的,可屋子里的灯光摇了一下,谁都知道这句话有多重。 陈毅只是笑了笑,那种知道责任压到肩头的笑。 他明白,这“败仗”不仅是枪炮上的输赢,还关乎着一座城市的脸面。 上海,是银行和码头的城市,是电车叮当、霓虹闪烁的城市,破坏一次,就得用几倍的时间和力气去修补。 从那晚起,作战会议上就多了一条暗线——怎么打才能不毁这座城市。 讨论的时候,粟裕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圈,一遍遍提醒哪些地方不能用重炮。 陈毅加了一句,部队进城,不许随意进民宅,不许扰民。 这些话听着像家长里短,可真落实起来,比打仗还难。 几个月后,黄浦江两岸的枪声稀稀落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 那天的早晨,南京路的铺子照常开门,门口挂着刚擦过的玻璃;黄浦江上小轮还在摆渡,水面被划出一道道纹路。 解放军按计划推进,街上秩序没乱,像是这座城只是换了个主人。 可这种平静没能维持多久。 从舟山机场起飞的轰炸机,像不速之客,隔三差五就来“拜访”。 B-24、B-25、P-51、P-38……名字各异,目的相同——炸电厂、炸水厂。 杨树浦发电厂挨了重拳,一半设备报废,整座城市陷进黑暗。 商店里点起蜡烛,车站的广播停了,电车僵在轨道上不动,像一群失了魂的马。 陈毅在市政会议上说:“解放了上海的土地,还没解放天空。” 他敲着桌子,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荡。 那时候的防空部队,年轻得像刚上阵的学徒兵,没什么远程预警能力,只能等到敌机压下来才慌忙抬起炮口。 要改变,就得有人去造一双提前看到的眼睛。 安国路76号的楼顶,一台从国民党缴获的四式雷达被架了起来,天线像铁做的花架,朝着天转。 刚竖上去时,大家围着看,心里盘算着它能替上海撑起一片安稳的天。 可几次空袭,它像个聋子,什么都听不见,屏幕上一片死寂。 毛病出在年纪太大,零件不全,发射和接收的频率对不上。 1950年的冬末,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21个学生被叫了名字,还没等毕业典礼,就被送到安国路。 他们背着小包,住进楼下的宿舍,晚上铺的是木板床,白天爬上楼顶一根根查线路。 风大得能把人吹得脚底发飘,螺丝掉到地上顺着水沟滚远,他们就趴着去捡。 市无线电台的主任工程师钱尚平来了,没带什么行李,只拎着一个小包,包里是工具和几张图纸。 他和交大的讲师蒋大宗并肩蹲在设备前,拧开机壳,调频、测波,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新开始。 终于有一天,荧光屏上闪出一个模糊的亮点——近距离的固定回波。 有人笑出声,又赶紧压低了,怕惊动了什么。 3月10日,雷达正式能用了。那天值班的人眼睛都盯着屏幕,手心出了汗。 两个月后的5月11日深夜,两架B-24轰炸机贴着夜色往上海飞,保持无线电静默,以为没人发现。 屏幕上的波形先动了,报告传下去,探照灯亮起,炮声跟着撕开夜空,其中一架在半空炸成火球,火光映亮了半边天。 第二天,残骸落在郊外,成群结队的人赶去看,带着孩子,提着篮子,像赶集一样。 那21个学生里,有20个穿上了军装,从此成了雷达兵。 他们从上海出发,把设备搬到沿海、搬到北方的哨所,一路守着天空。 多年以后,有人回忆说,当时没想什么宏大的词,只盼着上海的灯别再灭,空袭来的时候能提前喊一声让人去躲。 安国路的楼顶早变了模样,雷达也进了博物馆,可想起那个亮点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的夜晚,心里还是热的。 夏天的黄昏,江边的风吹得旗子哗哗响,像那年夜空中探照灯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