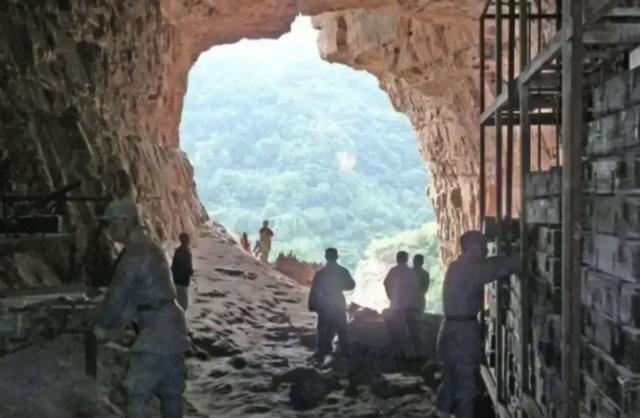1939年,日军少将中村正雄被击中腹部,身受重伤,军医为了取出子弹,只能切开他的肚皮,谁知一发炮弹正中屋顶,屋顶瞬间坍塌,碎石灰尘灌满了中村正雄的肚子! 1939年的冬天,昆仑关的风像刀子,能把人的耳根削得生疼。 天色暗得比往年更早,山道上积着前几天的冷雨,鞋底一踩,湿泥混着硝烟味往上蹿。 关口外的山谷里,埋着的是阵亡士兵的身骨,夜里风吹动草尖,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那时候南宁已经在日军手里,他们守得紧,就等着用昆仑关堵住中国和外界的咽喉。 第5师团是精锐中的精锐,硬得像一块铁板,中村正雄就是这块铁板上的一颗钉子。 老兵一个,日俄战争打出来的底子,脾气又硬又急。 按军阶,他该用镶铜军刀,可他腰间挂着一把镶银的,亮得像一片冰,走到哪儿都晃人眼。 那是赏赐,意思是他在战场上值这个面子。 那年冬天,他接到的任务是去救三木吉之助的联队。 三木困在昆仑关,兵力被打得稀烂,像被劈开的木柴,只能靠几根劣质绳子捆着。 中村从南宁带着部队连夜出发,天色阴沉得看不见月亮,只有几架军机掠过,轰鸣声在山谷里一阵阵地回。 七塘到九塘的路早被国军炸成了断线,桥墩倒在水里,河水翻着白沫。 队伍只能绕过残桥,在泥地里推着辎重前行。 五塘那一带,伏击来的太突然,像是有人在黑暗里猛地把桌子掀翻。 机枪声裹着火光,打在石板路上,溅起细碎的石屑。 日军的队形被撕开,伤员倒在路边,血沿着泥沟流下去,混成暗红的水。 中村吼着让人顶住,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催前线死守。 可走到九塘前,他自己也没能逃开命运。 那是个蒙蒙亮的早晨,雾气从山脚爬上来,把树梢都盖住了。 一声尖啸从远处刺破雾幕,迫击炮在不远处炸开,气浪像一巴掌把他拍倒。 他的腹部被撕开一道深口子,血从破口里涌出来,热乎乎地顺着军裤往下淌。 几个士兵抬着他跑到一处旧民宅,那是所被废弃的小学教室,课桌被拼成手术台,墙皮脱落,角落堆着几本被雨打湿的课本。 军医打开他的军装,看到嵌在腹腔深处的弹片时,脸色发紧。 刚要用镊子去夹,一声轰响顶在头顶,屋顶塌了半边。 瓦片、木梁、灰土像一场脏雪,从天而降,砸在地上,也砸进了他刚被切开的伤口。 军医本能地抬手去挡,指尖一碰到那片腹腔里的泥沙,整个人像被冰水泼了一下。 他们没法彻底清理,只能慌忙换了个地方继续。 外面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屋里的灯油烧到见底,灯罩被血雾染得发黄。 几个小时后,弹片被取出来,缝线拉紧,可感染已经像潮水一样漫上来。 到第二天凌晨,中村的呼吸断断续续,手边那把镶银的军刀被收进了帆布袋,再没出过鞘。 这事在日军中传开,像一根支柱突然倒了,士气一节一节地垮。 三木的残部撑不住,昆仑关的防线被撕开口子。 国军趁势压上去,血流得比雨还急。 几天后,关口重新被握在国军手里。 战场上散落着歪倒的铁盔、折断的刺刀,还有没人再去翻的背包。 统计数字像冰冷的石碑,日军几千人没能走下山,中国的阵亡数也逼近一万五千。 清理战场的人,在一堆破烂里捡到一本小册子,封面被血水浸透。 有人翻开来,看到里面有几行字——“昆仑关的中国军队,比俄国人更难对付。” 字迹歪斜,像是仓促中写下的,墨色在纸上晕开。 没人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也没人多问。 那本日记最后不知落到了谁的手里,也许压在某个木箱底,早就发黄。 多年以后,昆仑关成了旅游地。 山道两侧竖着石碑,碑脚的青草每年春天都长得很快。 风从隘口吹过,带着一点湿意,像是把远处杜鹃花的味道也送了过来。 山腰间有一块孤零零的墓碑,上面刻着中村正雄的名字,立在松树的阴影下,碑面上爬着细小的苔。 路过的人不多停,偶尔有孩子追着蝴蝶跑过去,踩得草叶一阵乱响。 天色将晚的时候,山里的雾又起来了,慢慢裹住关口。 那些石头、草木、碑刻在雾里若隐若现,像是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走来,又被藏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