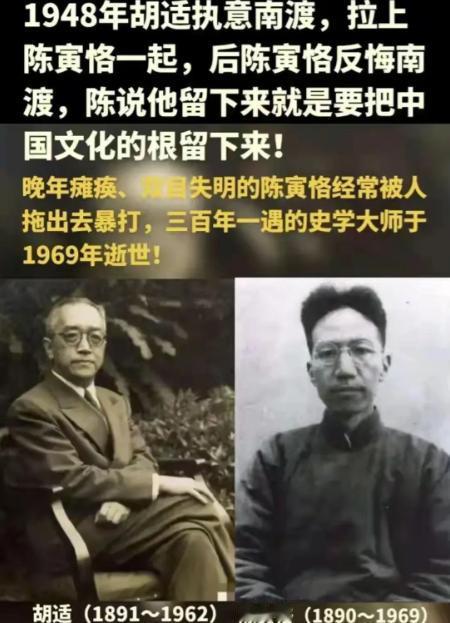1941年12月,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谁料,老人竟用流利的日语破口大骂,不成想,这群日本兵的首领站了出来,对着老人鞠了一躬,并用日语说: 1941年12月25日,香港彻底沦陷日军之手。 在“黑色圣诞节”之后,这座昔日繁华的都市,被侵略者的刺刀毁灭了一切。 而一桩发生在九龙半山寓所的事件,彻底成为震撼施暴者亦照亮黑暗中不屈的灵魂。 旅居香港的中国史学泰斗陈寅恪,用日语厉声斥责日军暴行,迫使凶徒低头退却。 陈寅恪的学问,早已跨越国界,有“教授的教授”之誉。 但能令暴戾的日军士兵瞬间失态的原因,或许藏在他学术脉络中。 早在1902年,年仅13岁的陈寅恪便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求学。 那时的他,在留日学生群体里,总是个不起眼的孩子。 他常常低头在图书馆看书,正是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不仅精通了日语,更深入钻研日本的历史典籍与古典文学。 他是同学眼中的“书呆子”,但实际上是“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体现。 此后,他游学欧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等十几种语言,但日语却始终未被遗忘。 这份深厚的学术积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化作了凛然的锋芒。 1941年,抗战烽火燃遍华夏,北平沦陷后,清华等校南迁。 陈寅恪当时右眼几近失明,身体状况堪忧,朋友曾劝他留居北平,因为他的地位,日军必会给予“礼遇”。 然而他断然拒绝:“我是中国人,死也不做亡国奴的学问!” 他选择颠沛流离,拖着病体追随学校,甚至将珍贵的研究手稿缝入棉衣内层。 几经辗转,他受聘于香港大学,一面教书育人,一面等待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机会。 然而,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彻底截断了海路,将他困在香港。 在日军飞机频繁的轰炸声中,他依旧在油灯下坚持著述,视文化传承高于个人安危。 香港沦陷后不久,一队日本士兵闯入陈寅恪的住所。 砸门声与呵斥打破了宁静,面对枪口,普通民众早已魂飞魄散。但眼前这位清瘦病弱、身着长衫的老者,却毫无惧色。 看着这些已经沉浸厮杀机器的士兵,他眼前或许闪过当年东京街巷中激烈辩论学问的日本学生身影。 激愤之下,陈寅恪竟用异常流利、地道且带着东京腔调的日语,厉声斥责。 他没有谩骂污言,而是直指日军暴行违背了他们文化中尊崇的儒家伦理与武士道标榜的“忠义”,字字诛心,句句戳在日军的文化根脉与道德软肋之上。 日语之纯熟,道理之透彻,史实之确凿,令原本气焰嚣张的士兵们瞬间惊愕。 领队军士惊疑之下试探询问陈寅恪的身份。 当得知眼前的老者竟是大名鼎鼎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且曾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具有声望的学者时,整个搜查队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日本文化中,对真正具有深厚学问的长者有着根深蒂固的尊敬,尤其在得知他曾与本国学术渊源匪浅。 领队士兵当即郑重地向陈寅恪鞠躬致歉。 他们此后甚至按上级指令派人“保护”陈家,试图表达“尊重”。 更令人惊诧的是,日军高层在事后亦得知此事,并指派一名高级军官携带丰厚礼品登门拜访,意图拉拢这位学术泰斗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理论涂脂抹粉。 然而,金钱利禄、虚假的礼遇,在陈寅恪傲然的民族气节面前,如同粪土。 他只接受来自自己劳动或同胞接济的饭食,“绝不沾侵略者的一粒米”。 日军对陈寅恪表面的“尊敬”,与其说是敬畏其学问,不如说是畏惧其那用任何强权都无法征服的独立精神和浩然正气。 日据下的香港,暗无天日,日军暴行肆虐,平民惨遭蹂躏。 陈寅恪在保护家人方面费尽心血,甚至让心爱的女儿剪去秀发,扮成男孩模样以避祸端。 尽管生活困顿,饥寒交迫,尽管右眼视力几近丧失,左眼亦严重受损,但这位双目不便的老人,始终未曾放弃一个学者的天职。 在昏黄的油灯下,他始终忍受病痛,坚持研究著述,完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凝结心血的重要著作。 1942年5月,在抗战爱国力量及民间组织的精心策划和艰难运作下,陈寅恪终于得以逃离香港魔窟。 离别之际,他将最珍重的手稿带回到自由的土地,继续耕耘杏坛,钻研故纸,即使后来双目完全失明,也以口述的方式坚持学术创作,直至生命终点。 陈寅恪在用不可征服的灵魂昭告世人,真正的力量,不仅在于武器,更在于精神的独立与文化的尊严。 在最为黑暗的时刻,文明的星火永不熄灭,一个民族的脊梁,终将由最硬的骨头撑起。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客户端——父亲陈寅恪早年的点滴旧事)(澎湃新闻客户端——陈寅恪家族的南京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