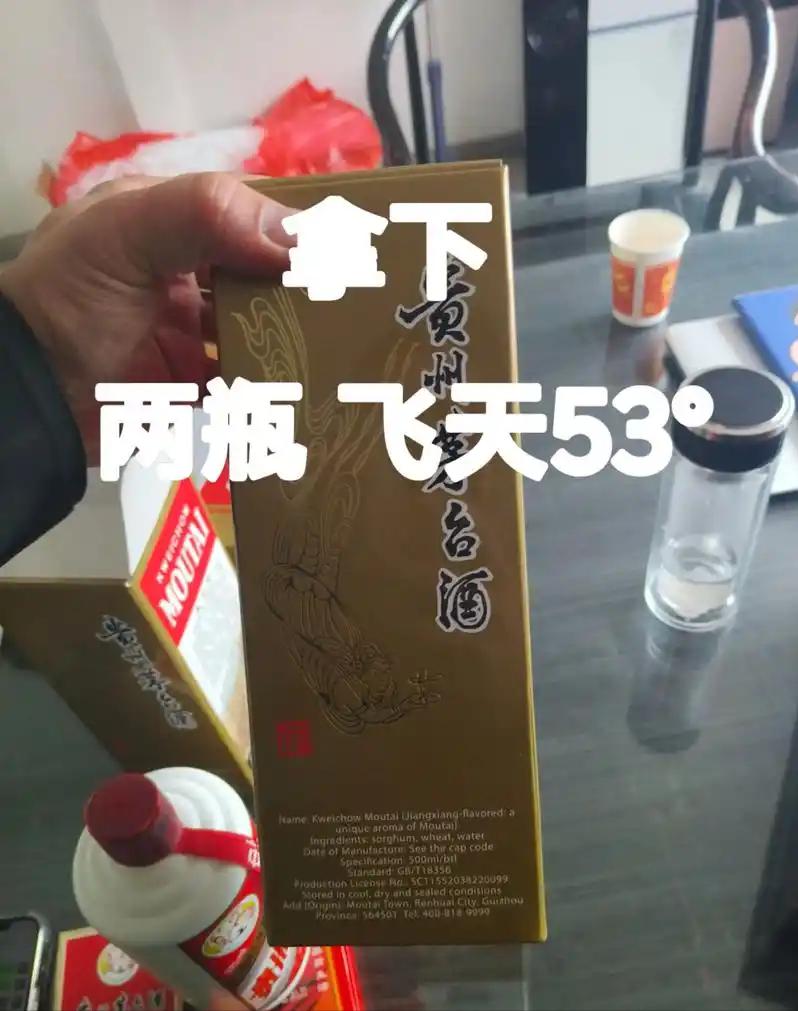2024年,新疆乌鲁木齐,男子到烟酒行买了2瓶飞天茅台酒准备宴请朋友,共花了5400元。可朋友喝了酒后,怀疑酒是假的,于是让男子去举报烟酒行,后经鉴定果然是假酒,于是男子将烟酒行告上法院,要求返还5400元购酒款并赔偿54000元。一审法院支持了退一赔十的请求,但二审法院却发现了重大问题。 (信源:手机光明网——一男子多次购买假茅台后索赔十倍赔偿,法院:退还酒款,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花费数千元购得一瓶假冒茅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寄望于法律,期望商家承担“假一赔十”的责任。这一期望看似合情合理,然而现实情况却常常令人大失所望。 最近,乌鲁木齐和上海的两起假茅台索赔案,就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两地的消费者都手握假货的铁证,但最终都只拿回了本金,他们所期望的十倍惩罚性赔偿,无一例外地被法院驳回。 乌鲁木齐的刘某,就倒在了第一道门槛上,一个关于他“身份”的拷问。2024年3月,刘某在一家商行,通过微信支付了5400元买下两瓶茅台。几个月后,他拿着假货鉴定报告,将店主郭某告上法庭,索赔十倍,也就是54000元。 起初,一审法院全额支持了刘某的诉求,认定商家销售假酒且未履行检查义务,理应受到处罚。然而,案件进入二审阶段后,形势骤然逆转。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刘某的行为模式存在异常。 他不仅多次购买同款酒并索赔,甚至在此次购买过程中,还进行了全程录像以获取证据。这些细节使得二审法院对其购买动机产生了质疑。法院认为,刘某购买茅台的主要目的,似乎并非出于个人品尝或招待亲友这类“生活消费需要”。 他的行为,更像是一种以索赔牟利为目标的系统性操作。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核心,是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打击不法经营,而非鼓励一种新的牟利方式。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的行为超出了法律意义上“消费者”的范畴,因此撤销了一审判决,只判令店主退还5400元货款。这道“身份之门”,将以诉讼营利为目的的购买者,挡在了惩罚性赔偿的大门之外。 即便索赔者的身份无可挑剔,也未必能笑到最后。上海的张先生就遇到了另一堵墙,这堵墙的名字叫“举证责任”。张先生在上海一家店铺花了8400元购买了三瓶茅台,回家品尝后发觉味道不对。 他将酒送到茅台公司鉴定,结果证实是假冒产品。于是,张先生信心满满地将商家告上法庭,同样要求十倍赔偿。与刘某不同,张先生的消费行为没有任何疑点,他就是一位普通的市民。 然而,法院的判决再次出乎意料,同样驳回了他的十倍赔偿请求。法院给出的理由很直接:酒是假的,没错,但张先生没能拿出证据,证明这假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也就是说,它可能对身体有害。 法院的逻辑,是将“假冒伪劣”和“不安全食品”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假冒”侵犯的是品牌方的知识产权和消费者的知情权,而只有“不安全”的食品,才能触发食品安全法中严厉的惩罚性赔偿条款。 从乌鲁木齐对购买动机的审视,到上海对假货性质的苛刻界定,这两起判决,看似都让消费者吃了亏,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消费维权法律背后的一套平衡逻辑。 法律既要像一把利剑,斩向那些危害我们“舌尖安全”的不法商家,也要像一面盾牌,防止维权规则本身被滥用,成为一些人敲诈勒索的工具。 这些高门槛的存在,也促使我们思考更有效的维权方式。当民事诉讼的路走不通时,或许可以换个思路。比如,第一时间选择刑事报案,让拥有侦查权的公权力介入,去追查假货的生产源头和销售链条。 一旦刑事案件成立,制假售假者面临的将是更严厉的法律制裁,消费者后续再提起民事赔偿,也会更有底气。法律的天平,总是在保护弱者和防止滥用之间来回校准。这些案件引发的讨论,本身就是推动它走向更优解的过程。